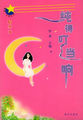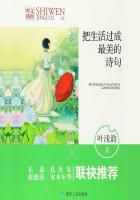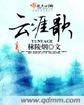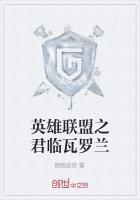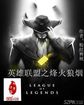我是踩着一地金黄潜入护国寺北岸那条老胡同的。树叶刚刚在秋雨中摇落,叶脉上仍然残存着生命的湿润,梗子在水露中浸泡过的沉香四下弥散。一只臃肿的老猫,在古旧的灰瓦上探出白色的头,眼皮同黄昏的阳光黏连在一起,显然对不速之客的踏访漠不关心。后来的日子里我多次看到那只猫,它迷离中带着几分清高的眼神和恭王府的门钉一样一成不变。
许多陌生的门,仪仗般一扇扇从眼侧掠过。疲惫的夕阳坠落在许多瓦制或陶制的花盆上,使我想起一生爱花如命的外祖母来。那洇湿的盆土里植着各样的花木,名字是大抵都叫不出的,能写清楚的怕只有喇叭花了,它们沿着藤蔓,架起在两户之间的半空中,袅袅娜娜,保持着攀爬的姿态。
房东引我一步深似一步地走着,过道愈发狭窄,树叶的清香却更浓了。当那间安卧于最深处的小平房穿越了无数门厅终于挺立在眼前时,气味的来源有了答案。
我确实看见了一棵很大的榆树。
仿佛要站班礼拜一般,同我未来的厨房并肩站在一起。
那实在是一棵很大的树,它的伟岸与粗壮,在这条低矮的胡同深处显得格格不入,两个男人都未必能把它的腰身围抱周全。腾地而起的根脉,宛若一条条突起在泥土之外的青筋,跳动在小屋斑驳的膝脚下。密布的枝枝杈杈,撑起天然的巨伞,使大地和天空产生了某种隐秘的通联。尽管榆树叶已落了许多,金灿灿地铺满了过道,铺得很厚,枝杈上仍然还有至少一半的叶群,掩护着间或休息的雀鸟。
我爱上了这棵树,在我爱上那所月租一千二的房子之前。
如许多作家所写那般,从此我卑微的窗前也有了树。
来北京之初,为了同广院离得近些,便合租在定福庄北街的一幢家属楼里。没毕业的时候,我曾把考取广院的研究生作为盛大的理想。这份亲昵一直在延续。
但每日到后海的编辑部上班,自然就有些远;我无论如何忍受不了在地铁里被各种肉质揉搓,呼吸比氨还难闻的生铁味道,以及在四惠东或建国门那站如闻防空警报般的狂奔。于是我租了一辆贝科蓝图单车,擦得锃明瓦亮。清晨从东五环外一路听着德德玛濮存昕骑到后海,晚间又碾着茫茫夜色融化在宽阔的长安街。那些闪耀的霓虹,明晃晃地映着我的镜片,使我沉醉不知归路。那些沿街的行者,那些异域的来客,那些高可摘星辰的广厦高楼,那些古旧的墙,渐渐地叫我熟稔,并萌生爱意。
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沾满了漉湿的叛逆,但这样坚持了三个月以后,我突然找寻不到叛逆的理由了。秋风中,我感到了一种荒凉。我终于骑不动了。
残奥会闭幕那天,是房租期满的最后一天。透了小窗的纱网望出去,低天的月,别了中秋才几日,就一下子瘦削许多,仿佛咬了一口便被丢弃的月饼。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落幕,而我追梦的春华秋实也终于同它一起散了场。
离别广院,不只是距离的需要,更是一种立场的隐喻:做一个清贫的文学编辑,不再是收入丰盈并光芒万丈的编剧或导演,这是一条被颠覆的道路。我须在更辽阔的原野里疾奔,同更丰厚的土壤接吻,更懂得民众的贵重,更明晓生命的湿度。
只为奔赴文学的后海,与茅盾、郭沫若、丁玲为邻,我终于背叛广院薄情而去。在那核桃树林阴湿的土里,有我埋下的一颗心,未尽之梦,且由它向远方赶来的后人传说罢了。
巷陌深处,很是清净幽僻,住的尽是老北京布衣。大抵一墙之隔便是梅兰芳故居的缘故,这院落的众生也仿佛添了几分雅气。
一走一过,总会与许多脸孔不期而遇。打声招呼,寒暄几句,比之钢筋水泥中的木偶人,显然生动许多。炊烟袅袅升起时,巷道里总有京剧广播隐隐传来。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大概是吃好了,拄着手杖稳健地踱出门去。一位妇人怀抱婴孩从外归来,路过我窗前,不拘小节地打了一个粗嗝,那婴孩仿佛听到了一种召唤,立即以嗝和之。这种生存体验让我第一次感知到了群落的存在。在先前,城关楼群中长起来的一代人,是绝无这种意识的。
我渐渐熟悉了每一位街坊。
比如,对门的老何。
在我敞着门扫地或搬东西的时候,他总是树叶一样悄无声息地飘洒进来,点上一颗雪茄烟,四下里寻望一番。他对我的一架书籍颇感兴趣,最后终于忍不住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个文学工作者,也写点东西。
他说太好了,你是作家,我是画家,都是搞创作的。
他高兴的时候眼睛总是像蜻蜓一样瞪得很大。
原来我这间房子空了两年,一直很静。老何生怕房东把它租给后海酒吧的伙计,或者市场卖东西的小贩,扰了他的创作。
我应邀观赏了他的雅室。那是他的老母亲留下的一座祖宅,三进屋,内室还套着一方天井,植了一株通天的仙人掌。壁柜上收藏着不少好茶,墙上自然也少不了字画。老何说他新购了一套楼房,任其闲着,后海这边是文人雅士的福地,他只爱在这老宅子里品茗作画,仙人般的生活。他喜欢一边望着他的画,一边吐着肥硕的烟圈说话,并不一定看我。
如此爱这地方,与之为邻,地价也似乎抬高了几分。一句“都是搞创作的”,颇使我受了鼓舞,夜静时分,还真就趴在电脑前咣咣砸起键盘,创作创作。
在我刚刚习惯了北京秋天的干燥时,一夜雷电交加的大雨不期而至。
电火般的闪电仿佛直接透了玻璃抛进来,使屋舍俨然白昼。轰鸣的雷声,低沉地压满了老榆树的枝头,每一声都炸在耳根。我听到风雨中树叶飘摇的吼声,每一扇叶面都像一张弹动的簧片,惶恐不安地战栗着。
我硬用鼾声压过了雷声,姑且安然地沉沉睡了,却在天明时被窗外的吵嚷惊醒。三五个街坊,围在大榆树下,列举着它的原罪。
都是这树造的孽!斜对门的妇人吼道。就在前一夜,她家的电器烧坏了。这不招待见的老树精!
就是,你看这叶子,老得扫,你不扫吧满地都是。有人附和道。
这时我听到鞋底踩在厚厚的叶子上的沙沙声,似乎还有露水弹飞的声音。
妇人又说,这树根不能再长了,再长就把他家(她指的当然就是我家)的小厨房拱塌了,到时候咱们都得遭殃。
于是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合计,要把这树锯掉。
有人说以前就反映过,但上边说这树太老了,属于古树名木,不给锯。又有人说,他们不锯,我们挨家挨户集份子锯。这时我听清是老何那个慢条斯理的声音,他说这树可不好锯,要锯也得一段一段地锯。
那个清晨,我开始为一棵树的命运认真地忧伤。
我确认没有听到九十多岁的老奶奶的女低音。突然间,从未与之交谈过的她,仿佛成了这胡同深处唯一可以护佑我的人。再见她时我终于忍不住问起:奶奶,这树有多少年了?
老人的眼神在秋光中疲惫地黏连着,仰头望了望已秃掉的树冠,摇摇头道:
说不清啊,我小的时候它就已经这么高了。
日渐熟稔的胡同和日渐深邃的秋天一起变得冰冷和凄凉。
有一次,我居然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那夜去人艺看《雷雨》,出了首都剧场,骑了贝科蓝图,不知不觉驶进一条胡同。本是想抄个近路的,却越走越迷糊,光色渐暗,居然转不出去了。老北京的死胡同在夜色中是有些怕人的,人们睡得早,灯火熄灭了,只能听见猫在瓦楞上疾走或从一片屋瓦跳上另一面墙垛的重重的扑通声。三个鲜活生命刚刚消逝,沉郁的悲伤与黑夜一起逼近。我认准一个方向,铁定地骑,隐约发现一块指示牌。定睛辨识那斑驳的字迹,认出是“沙滩北街”,心头一惊——这正是我的北京户口的驻地。先前它只打印在一张轻飘飘的集体户口单子上,我煞有介事地找过,现在竟顾自横在眼前,黛色的墙体上晃动着鬼魅的月影。
我揣摩着这个谜语的暗喻,不觉间骑回到德内大街。我钻进门洞,在凸凹不平的青石板上惝恍不安地硌了一阵儿,直到望见那棵黑暗中肃立不语的老树,才确信自己真的到了家。
原来我在北京还是有一个家的。
是这样的,我还花了一千二的租钱呢。可是,为何我总是常常忘却了这一点,常常觉得无家可归呢!
秋天疾驰在旷远的虚无中,说去就去。
我把编辑这份活儿做得有滋有味,团结了一批热爱文学的回族青年,信誓旦旦地要为回族文学的复兴贡献力量了。我还组建了一个QQ群,没事就在网上和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谈谈文学,聊聊创作。工作半年都不到的我,已开始习惯以专业自居,指点完这个又启发那个。
转眼已近岁末。
我盘算着,是时候组织一次网络聚会了。
许多写作者都如约来参加讨论。大家互道着赛俩目,谈着耳熟能详的回族作家和作品,分享着创作上的困顿与经验。发言很踊跃。
我一直遗憾素来活跃的安然为什么没来,突然,字行间蹦出他退出该群的消息,紧接着,我收到一条被他请出他的“回风”群的通知。显然,安然一直在隐身观察着我们的发言;更显然,他用无言的退遁,表达了强悍的蔑视与愤怒。
如坠寒窖!
我与安然早相识了,是七年网龄、两面之交的挚友。他是一个有血性的民间作家,那济南西关回民独有的桀骜之美,沉潜于逐字逐行,抖一抖亮出来,会让许多吃作家饭的人脊背发冷。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好兄弟,在灵魂深处有着难能可贵的默契,也能包容彼此的不周。但他的愤然诀别,显然在向我昭示:这一次,他要与我们划清界限。
慌忙去找他,见QQ签名里唯有一句:
请发声,阻止轰炸!
我明白了全部的因由。
那时节,在古老的巴勒斯坦,一场文明纪元里最灭绝人性的屠戮正在激演。许多长着长长睫毛的儿童来不及啼哭就死了,许多把美丽掩映在面纱中的母亲都埋葬在废墟里,许多虽然骨瘦如柴但仍然捡起石块准备投向坦克的父亲都被白磷弹烧得一块骨殖都不剩。
而我们,曾与他们跪向一座城堡的中国青年,在遥远的范仲淹的国度,如新年茶话会一般聊着文学,叙着家常。
人类的尊严和正义,正在受难;生命与人道,正在消弭;曾因种族屠杀而向全世界告状祈求怜悯的民族,正在从乞丐变成强盗,导演着更加令人发指的人类的灾难!而标榜着信仰文学的我们,在冗长的聊天记录里,竟没有留下一句人道主义的支援,没有送出一滴眼泪,甚至没有在聊天之前的一次默哀,一双捧起的手掌。
西边的星星已经暗淡,浓黑的夜幕笼盖了冰封的后海。我木然关掉了微笑的企鹅,决意作一次冷静的清算。
是的,文学的奔赴,在我已必须重新启程。
新年几日,冷僻、昏暗的小家,迎进了远来探望的父母。
元旦的清晨,我们仍在沉眠,却听到屋顶上扑通扑通蹿上蹿下的动静。母亲吓得坐起来,父亲也睁开了眼。我说,没事,是猫。可是那扑通声愈发地明目张胆和富有节奏,分明不是动物。
来不及推门去看,吱吱的巨响已经从天坠落。
父亲说,谁家的摩托声这么大!
我缄默着,悲伤得不发一声。
不用去看,也知道三五个屠夫已经蹿上我们的房顶,已经抱着滚圆的电锯,从枝到干,一截一截肢解着那棵至少二百岁的老树。
如果伊布里斯①真的与人类同存,如果魔鬼也会显形,我想它的声音一定和电锯一样。没有比那更可怖、更令人坐卧不安的声音了。那圆锯空转时,至多只还是狰狞的吼叫,凡啃咬在质感的树骨上,那渐强的割裂、决绝的凌辱,却分明掺杂了破碎的笑喊。
一棵树的倒掉,对于一条胡同平常得如同流浪猫的失踪。
绞痛与窃喜同样深藏不露。
父亲提议去苏宁电器给我买个电磁炉,他说我必须学会独立生存。
我便试着推门,却被一地的残枝堵住。
老榆树高贵的头颅仍还在,仍还不曲不折地张向高天。朝霞升腾了起来,红色的光染向这片待伐的枝头,天光一派血腥。到了次日清晨,枝已伐尽,只剩了粗壮的树干。到了黄昏,那干也不见了,留在原地的只有一截磨盘大的树桩了。
一个屠夫在清理现场。
我怯怯地问他:这些根还会再长么?
长就给它憋死,长就给它憋死。憋几次,就把树气死了,树是怕气的。他拍拍沾满秽土的手掌,操着一口畸形的汉语说道。
见门外有动静,画家老何照例钻出门来。
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家窗前的大树桩,眼睛一瞪,显得很兴奋:我说作家,我看这树桩改成茶几最合适,你和房东说说,到时候咱找朋友来喝茶!
父母回东北以后,小屋空荡荡,大成了一个世界。
突然意识到,太久没有做求祈了。
于是换了水,负重地捧起掌心,端庄地缅怀——为一棵不复生长的灵魂,也为一切轰然倒地的梦想,永远坎坷的理解,还有遭遇屠戮迟迟不归的痛感。
原载《长城》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