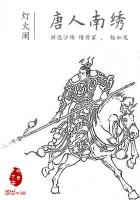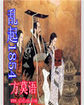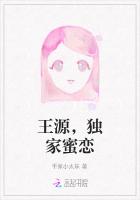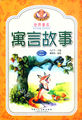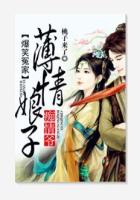5.初识“地球村”
1993年的夏天,受犹他大学Albrechtson教授的邀请,我以宁夏农学院副院长的身份率赴美考察团(一行三人)代表学校与犹他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进行第一次学术交流,同时考察美国作物育种和栽培技术等。
我们一到美国,我的学生(Albrechtson教授的助手)由犹他州驱车1600余千米已在旧金山机场迎候。为了帮助我们的考察,也节省我们的旅费,他牺牲了自己集中起来的一年的假期,租用了一辆汽车,全程陪同了我们的访问。得益于他的鼎力相助,我们的考察进展顺利,并具事半功倍之效。
Albrechtson教授对我们的访问行程安排得十分周密,费时少行程短而到访的地方多。在访问犹他大学之前,先由旧金山北上,沿途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俄勒冈州的俄勒冈大学,华盛顿州的华盛顿大学,以及美国农业部设在爱得华州的小谷物研究中心。我们到访每地,都细心考察了那里的实验设备、实验室研究和田间试验,与专家们进行科技交流,受到了深刻的启迪,获得颇大的教益,还收集到不少的文献资料和作物种子等。从每一个单位出来,汽车载重都增加不少。
另外,自驾车考察比坐飞机“天马行空”既节省了时间,又脚踏实地地领略了美国从乡村小镇到中小城市的自然风貌。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很短,我们驱车飞跨的这片土地,在200年前还是荒蛮之地。大自然和人类的创造力是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沿途饱览了自然天成和人类耕耘所成就的诗画美景。那一片片平整而望不到边的农田,就像是用机器裁出来的翠绿的地毯,庄稼和蔬菜种得那样的整齐,纵、横、侧看皆成行,像整齐列队的队伍一样;草场无垠,羊群犹如绿茵之上的点点白玉;低头吃草的肉牛在阳光的抚照下背上反射着油亮的光。我们也驻足欣赏那起伏秀美的山峦,瞭望那无边无际的森林,从拱桥上俯视那清澈湍急的河流,在山下仰望那激越咆哮的瀑布。有一次,我们驱车沿崎岖的山路蜿蜒而上,想在半山腰处停车远眺山色,顺便上洗手间。让我惊奇的是,在这孤零零的洗手间里居然也有热水洗手,有肥皂液、擦手纸等,洗手间的清洁与城里的别无二致。这让我纳闷,如此高耸而孤远的山上,这热水是从哪里来的?
结束了对美国西部的访问,在到访主访单位犹他大学之前,我们先乘飞机去访问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我的一位老朋友(我们的友谊开始于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时)全程陪同我们在这里的访问。他的夫人热情地天天为我们准备饭菜。我们先后访问了美国农业部所属的农业科学研究院,美国农业图书馆,马里兰大学等单位;参观了美国国会山、白宫等,登上了位于市中心的华盛顿纪念塔。
在犹他大学的访问,占全程一半的时间。我们一到,就开始了双方的交流活动。首先,Albrechtson教授以东道主身份介绍了犹他大学的情况,陪同我们考察了有关学院、研究室和田间试验等。我在这里作了“Seminar”(专题讲座,专家讨论会)。这是来美之前应Albrechtson教授和我的学生的邀请已作了准备的,会上交流了我写的两篇论文、一些幻灯片和荧屏投影胶片等。未曾料到的是,我到达Seminar会场时,到会者竟全是犹他大学的教授们,没有学生。我面临的是真正的“专家讨论会”。我看到各位与会教授所持的单子上,把我作的Seminar题目写得很大很正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小麦生产和发展》。但在我讲述之后,他们提出的问题多是与宁夏这块沙漠中的绿洲有关。最让他们难以理解的是,用以灌溉小麦的水来自黄河,而麦田的排水却又直接回到黄河。对此我只好临时在黑板上绘图予以解释,然后用幻灯片展示了从黄河引水的闸门,密如蛛网的农田灌排系统;以及金色的麦浪,平展的稻田,葡萄架上紫红的葡萄,把枝条压得弯弯的玛瑙般的枸杞等。这些影像激起了教授们的兴趣。一位教授问:“为什么在那茫茫戈壁中间竟有宁夏这片绿洲?”我脱口而出:“黄河!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
美国犹他州与中国宁夏在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诸方面很相似,都属于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农田盐渍化和种植作物的种类也相似。两校间经初次交流和进一步商谈,合作关系建立了起来。内容包括教授互访,互派研究生,科技文献和科研信息交流诸项。
合作关系最容易办到的是文献和科技资料的交流,通过双方互寄就行。商定的科技信息交流是通过计算机荧屏定期用英语对讲来实现的。对讲时可看到对方的影像,这在当时还感到新奇。犹他大学刚与另一国家建立起这一信息交流渠道,与我们是建立这种渠道的第二家。我看了用于这种交流的设备,觉得回去置办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其实,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信息时代,美国是进入信息时代的领先者。信息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到21世纪初,计算机荧屏对讲技术已失去其神秘色彩,进入普通家庭。这样,双方信息交流之路愈益宽广,就像铺满阳光的康庄大道。
但是,在合作关系展开之后,我们发现,横在双方之间的语言问题成为交流的障碍。我们国家落后,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首先要学习西方的语言,这让我们在学习效率上吃了大亏,因为学会一门语言要费多年的工夫。信息交流对讲用英语,派遣赴美的研究生要先考过托福或GRE;相反,美方则很简单,只使用他们的母语。访问中国的教授,中方要为他们配翻译(除非这教授是华裔),只能讲一句,翻一句,事倍功半。我们访美一年之后的盛夏,邀请Albrechtson教授回访宁夏时,就是这样的。
与犹他大学合作项目中由于语言问题我方两头吃亏。英语能达到对讲和出国要求的教授寥寥无几;我们下大气力从英语和专业诸方面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能选派出去的也是凤毛麟角。但无论如何,建立了这种合作关系是好事,是大进步。
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世界“变小”了,变成了“地球村”。当人们进入被称之为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不应只操一种语言,首先要能运用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最好能会多种语言,否则就寸步难行。写到这里,我忽然彻悟:国学大师季羡林精通五六种语言,陈寅恪精通14种文字,马寅初(曾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72岁时开始学习并能运用俄语。大师和院士们能运用各种语言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才有他们视野的开阔和学术造诣的博大精深。
我们在犹他大学待了10天,中间有一个周末,我的学生全家,带我们去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看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摩门教堂。这座教堂用不同色彩的花岗岩、大理石建成,高耸入云,气势雄伟,内部宽敞明亮。与西方一般的教堂不同的是,四壁布满了一幅幅象征着教义的壁画和艺术品。我的学生为我们讲述了摩门教的历史。
在美国历史上,摩门教曾被视为邪教。教徒们惨遭杀戮和驱赶,不得不在一位杰出领袖的率领下西迁,最后定居在盐碱漫布、满目荒凉的现犹他州一带。他们开山劈岭,披荆斩棘,搭建茅棚,治理碱滩,以勤劳勇敢、以血和汗、以不知多少代的生命为代价,使不毛之地变为良田,使其后代得以繁衍(该教曾实行的一夫多妻制也与繁衍后代有关),并建成恢弘壮丽的新盐湖城。耸立在盐湖城中心雄伟无比的摩门教堂,似乎证实着他们为生存而抗争的胜利,但为这前无古人的建筑奠基的,却有数不清的摩门教徒前仆后继的尸骨!
我是头一次知道世界上有摩门教及该教的悲惨历史。这与自称为世界上最优秀人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国早期移民,曾把非洲黑人当做牛马贩卖来加以奴役虐待,以及把土著印第安人惨绝人寰地疯狂杀害、驱赶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不毛之地而几近灭绝的历史融汇在一起,使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当今美国广阔富饶的土地上,曾浸透了多少被奴役者的汗水和鲜血,埋葬着多少世世代代拓荒的奴隶们的尸骨!这广袤土地上的农作物和牛羊群代代丰茂茁壮,概因为它们从这血汗和尸骨中汲取了营养!
结束对犹他大学的访问,接下来是取道内华达州回旧金山的顺路考察,显得很轻松了。我们从犹他大学驱车南行,在美国西南部又转了半圈,加上前面美国西北部的半圈,算是在美国西部转了整一个圈。
美国是一个无奇不有的国度。我们在内华达州驱车飞驰,在那看不到庄稼、看不到牛羊、看不到树木、赤地千里的沙原上竟矗立着一座白日里金碧辉煌、夜间霓虹灯万紫千红的拉斯维加斯大赌城。而且,似乎由这座赌城把荒漠无边、寸草不生的内华达州盘活了。我们驱车飞驰在这片土地上,一边又好奇地谈论着美国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沿革。
原来,我们这次访美,汽车轮子所碾过的美国西部的所有国土,都是历史上通过扩张而得来的。且不说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是如何并入美国的,只说美国沿西海岸的内华达山脉与中部的落基山脉之间的大片土地,是1846~1847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中得来的。这大约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今日美国版图上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部分犹他州。
现在墨西哥人偷渡到美国打工的人每年有数百万,屡禁不止。这些墨西哥人理直气壮,没有负罪感,认为越过国境就像跨进自家的后院一样。一个墨西哥男人到美国作苦力所得的微薄收入,除了自己用,可以寄回去养活一家人。“他们咀嚼着美国甘蔗最干涩的一段,却依然觉着比在母国的生活更多一些甜味。”
世界的发展真是令人费解,令人沉思。按说美国当年不应以武力割占墨西哥的领土,可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原墨西哥人很愿意摆脱墨西哥政权的统治到美国来得到自由民主。当时的美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侵略战争”,是保护这里人民自由的战争。虽难摆脱“侵略”的罪名,却认为以人心背向决定人们脚下土地的归属是合理的。时至今日,被割占的这片领土和它所承载的人民,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如果它不被割占的话,却会仍处于“发展中国家”。
当今世界,“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口头上,包括上小学的孩子。据研究者的论证,全球化其实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就开始了,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风靡世界。难道上面说的事情也都印证了全球化的历史轨迹?难道现今的世界,真如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第29届奥运会主题歌所唱的“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永远一家人”吗?
6.再上台阶
我领导的农学系荣获自治区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以及我个人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里程碑。这既是荣誉,更是对自己的鼓舞和鞭策。我暗自制订了下一步的目标:使农学系再上一个台阶;使自己在教学与科研上再有所成就。可是,在当时的国内,似有这样的“潜规则”:凡在业务领域里有所造诣者,都要在行政上委以重任。由此,我在1991年秋被任命为农学院副院长兼小麦研究室主任。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来宣布对我任命的会议之前,农学院的院长特地向我打招呼:“宣布对你任命时,你要服从,不能说不干。”
我服从了组织部任命,在全院主管教学、成人教育、学报、图书馆和实验农场等部门的工作。
我淡漠官场,为同事们皆知。何况,当时学校的第一把手曾在背地里冠我“难以驾驭”的帽子,所以从未想过升迁之事。这便是宣布对我任命之前院长(第二把手)向我打招呼的原因。
我并没有感到这官位的荣耀,只感到肩上的责任重了,只觉得这是国家对自己的信任。我要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学生,我没有道理不好好干。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既然我要不负重托,就要烧起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主持修订全院的教学计划。
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划时代的大转折,使全国高教也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十四大对高等教育提出新要求,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高校要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克服学校不同程度存在的脱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现象,要按照现代化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结构。
根据《纲要》的精神,我带领工作班子首先从“需要”和“现状”方面进行调研,包括下到县、市考察地方上对于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状况;在校内通过期中教学检查和期末总结进一步摸底;召开全院教学工作会议研究修订教学计划的方向、目标和具体措施;还深入到马列德育课部和计算机课程组等单位,与教师座谈讨论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等。
学校成立了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班子。这个班子不乏高教事业上的老手,又有中青年人的活力,很团结,对教改兴趣浓厚,想法多,工作起来还有些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