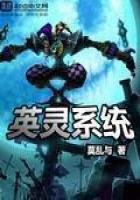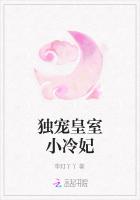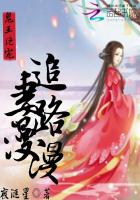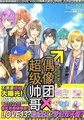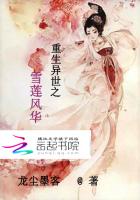老实说,知道《中华儿女》设立了“我的母亲”栏目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在读这个栏目里的文章时曾经几次都产生过写作的冲动,但是,我却始终没有拿起笔来。是没东西可写吗?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是考虑到该不该写和应当怎么写。这次编辑部又来向我正式约稿,而且,态度十分诚恳。盛情难却,我不能不答应下来。
我心里很清楚,我的母亲是有些特殊性的,我和母亲之间的感情也是有些特殊性的。把这一切如实地写出来,不是没有困难的,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然而,现在既然已经答应下来了,那就只有把一个真实的母亲和一个真实的我,统统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作者与母亲合影大约在近八十年以前,父亲作为一个书生,孤身一人从广东省南海县来到北方做事谋生。当时,他已经结过婚,而且妻子病故了。在他于山西省一家煤矿当经理的时候,与母亲结了婚。母亲是北京人,还是满族人。据说,我的姥爷是蒙古族人,曾经在清朝的“旗”里当过一个小军官。后来,随着清朝的覆灭,母亲娘家的家境也就败落下来。所以,父亲是花了一笔钱才把刚刚只有十三岁的母亲娶过门来的。
后来,父亲辞职离开了山西煤矿,回到北京在一家印刷公司当文牍科长。这时我们的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仍旧雇用着用人,其中包括“老妈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保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始终过着相当清闲舒适的日子,当着令人瞩目的、有钱人家的“太太”。
哥哥和我就生在这样一个富裕家庭的最后阶段。
人们传说,我小的时候,大奔儿头,深眼窝儿,长得有些像外国的小孩儿,既好看又好玩儿,为此大家都比较喜欢我,叫我“小外国孩儿”。母亲更是喜欢我,经常要带着我出门去买东西、看朋友。其实,我只不过是母亲向着亲友们显示和夸耀的“小玩艺儿”而已。我的吃饭、穿衣以及其它的许多口罗嗦事全部都由“老妈子”——“老王妈”来承担,母亲对此是从来不管的。在我很小的时候,脑子里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母亲,而是“老王妈”。因为她从我生下来不几天喂羊奶起,一直照顾我长到上小学之前。“老王妈”是京东三河县人,在我们家差不多呆了一辈子,是在我们给不出工钱以后又继续白干了两年才回农村去的。一句话,是“老王妈”整天形影不离地照顾着我,所以我那时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母亲的爱。
后来,父亲由于年老体衰,也许还有别的原因,被印刷公司给辞退了。从此开始,我们的家境就以很快的速度向下跌落着。原来一大家十来口人住在西单附近闹市区独门独院的宅门里,后来全家只剩下本家四口人便搬到靠近西直门的一条胡同的杂院里,住进了一间不满十平米的小平房。父亲失业以后,经济收入分文皆无,只有靠着当、卖衣物过日子。可是曾几何时,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一件件地消失了。实在没有办法,父亲才提出来他可以做中医应诊病人。父亲年轻的时候,确实学习过中医,而且成绩不差,是一个医术尚可却无名气的医生。因此,在挂牌行医以后,来看病的人也是寥寥无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不得不开始过着“有上顿没有下顿”的贫困生活。
虽然那时候我的年纪还小,懂事也不多,但是有一件事却一直留在了自己的记忆里。
那是一个深冬的夜晚,是一年当中北京最冷的天气。
天空堆满了厚厚的灰色云层,鹅毛大雪在随着西北风呼啸着上下飞舞。
那一天,由于没有前来就诊的病人,父亲连一个钱都挣不到手。早晨全家人就放弃了吃东西,中午也只是喝了稀溜溜的棒子面粥,到了晚上干脆断粮揭不开锅了。天黑以后,我们都围坐在小煤球炉旁边烤着火,也不知道是谁的肚子里在不时“咕咕”叫着。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对无言。只有父亲在欲说又止之后,摇摇头长叹上一口气。
小煤球炉里,只有少半边的煤球是红的,没有一点点火苗。炉子上坐着一把生铁的水壶,已经好半天了,壶顶的口上也看不见冒出一点儿热气来。人越饿就越冷,而越冷也就越饿。这大约就是所谓“饥寒交迫”吧。母亲看了一眼窗外,又看了一眼座钟,说:“别急,再等一会儿吧。他准能来。不管怎么样,他一来咱们就能有吃的了。”
突然,从胡同里传来了一声很熟悉的卖萝卜的吆喝声。母亲的眼睛里一下子闪现出惊喜的目光,并且,急不可待地跑出屋去。
功夫不大,母亲手里拿回来两个赊来的大水萝卜,一边笑着一边掰给我们吃。我们大口大口地吃着,水萝卜又甜又香又脆又水多,好像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萝卜。
大家很快就把水萝卜吃完了,连萝卜皮也没有剩,只留下了再也无法啃下去的小萝卜尾巴。而且,哥哥还要把萝卜的小尾巴也吃掉,被母亲一把抢过去扔在地上了。
母亲让我们赶快洗脸、洗脚早点儿睡觉。可是躺下以后,谁也睡不着。肚子还是“咕咕”地叫个不停,而且,好像声音更大了。躺在我身旁的母亲,帮我掩好被子,搂着我说:“快闭上眼,再不睡肚子又得饿了。”我点点头,只好闭上了眼。
是的,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把母亲和我一下子拉得很近很近。
父亲的中医诊所基本上是没有病人来光顾的,偶尔来了一个半个病人又赶上父亲血压高的毛病犯了,只好让人家另外去投医。Et子越来越难熬了,可以说已经到了再不想办法就要饿死人的地步。万般无奈,母亲这位长年使用过“老妈子”的人,也不得不给人家去当“老妈子”。
记得,母亲第一家是给一个韩国人当“老妈子”。我们是同住在一条胡同,只隔着两个门的邻居。大约正是由于比较近便,所以,母亲可以一方面在外边做“老妈子”,一方面还可以照顾我们父子三口。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母亲常常在晚上八九点钟,或者再晚一点,等到主人用过饭休息以后,就把一大包带着煳锅巴的剩大米饭,偷偷地送到家里,然后,再立刻跑回去。这对于经常吃不上大米、白面的人来说,自然是高级的食品。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三个人用水疙瘩咸菜就剩大米饭,一边吃,一边说,一边笑,真有点像过年似的。
老实说,当时每天的三顿饭里主要是要靠这顿晚饭填饱肚子。为此,我们从一大早就盼着这顿晚饭。我常常是在天快黑的时候,就一动也不动地坐在窗户前面,瞪着两只眼睛,透过玻璃盯着院子里那扇红色的旧街门。而只要一看见母亲的身影,我就会高兴地回过头来大声叫着:“娘来了!娘来了!?’然后,跳下凳子,冲出屋去,抢着把剩大米饭接过来。这几乎成了每晚家里一个不可缺少的精彩“节目”,也是我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刻。
当时,一个“老妈子”每月挣的工钱是很有限的。家里要靠母亲的工钱、父亲行医的收入和偷来的剩大米饭,才能勉强地度日。大约正是因为这样,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哥哥和我到她的主人家里去吃顿“蹭饭”。
有一次,母亲刚刚换了一个主人,就叫我们晚上去吃“蹭饭”。
新主人是在新街口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住。下了学以后,哥哥和我便来到了那里。因为从来也没有来过,胆子特别小,谁都不敢走过去按一下门上的电铃。哥哥让我按,我让哥哥按。最后,只好用“石头、剪子、布”划拳的方法来决定。哥哥输了,由他去按电铃。不知道为什么,哥哥按了老半天也没有人应声开门。眼看着天就要黑下来了,我们都有点着急。哥哥说:“干脆,咱们推门试试,要是没关着就溜进去。”我当然赞成。于是,哥哥在前,我在后,用手一推就把门给推开了。我们笑着走了进去。可是再也没有想到,刚走出门洞没几步,一条黄毛的大狼狗就从院子里影壁旁窜出来,向着哥哥的身上猛扑。哥哥大叫了一声,回头拉着我的手赶快往外跑。跑出门去以后,哥哥又转身把门关上,并且用手紧紧地拉住了门上的大铁环不放。当时,把我们的脸都吓白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哥哥和我再也不敢进门去了,甚至连门铃也不敢按了。
哥哥问:“怎么办哪?”
我摇摇头,不知道怎么好,哥哥说:“这样吧,咱俩就在外边儿等,说不准娘能出来看看呐。”
我们坐在不远的大槐树底下,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了下来。这时候,又肚子饿,又进不去,又实在不想走。怎么办呢?哥哥出了个主意——干脆大声喊母亲出来。我一听当然也同意了。
我们俩就站在槐树底下,向着灰色的高墙里边,用嘶哑的嗓子一声接着一声地喊:“娘——娘啊——!”“娘——娘啊——!”……喊了有十多声以后,母亲果然出来了。母亲来到我们的面前,不由分说便打了哥哥一巴掌,埋怨哥哥太不懂事。母亲说:“你不知道,我正给老爷开饭呐,哪儿有时间出来接你们?再说,这事儿得尽量不让老爷他们知道。你们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啊?”
哥哥听了当然不大服气,就把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我也直给补充着。
母亲听了以后,特别知道了哥哥和我差一点让大狼狗咬伤,眼圈儿马上就红了,走过来一下子把我们俩抱住,哭着说对不起哥哥和我,哥哥和我听着也直掉眼泪。
时间太晚了,怕惊动了主人,那天的“蹭饭”也没有吃成。临走的时候,母亲拿出钱来,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一个人买一个芝麻烧饼吃。母亲一直送我们到胡同,然后就赶快回去给主人洗衣服去了。
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母亲为我们,为我们的家可真是不容易。
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病故了。
老实说,父亲的高血压病不光他自己知道,我们大家也知道。因此,如果能够得到及时治疗的话,这一关是完全应当也可以闯过去的。然而,家里实在是太穷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哪能有钱治病呢?于是,父亲的病既不能请医生来出诊,也不能到医院去就诊。在这种情况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由父亲自己给自己开处方抓药治疗。天晓得,父亲到底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处方。反正,只吃下一剂药去,人就再也不能说话了。
那是一个早春的夜晚,天气乍暖还寒。
由于父亲的病,家里冷清极了,没有一点点生气。
父亲得的是脑溢血,也叫中风不语,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你和他说什么,他只能点点头,或者摇摇头,有时嘴角上还能露出一丝惨淡的笑,显然心里什么都是清楚的,就是已经失去了任何语言表达的能力。
母亲坐在床前照顾着父亲,用热毛巾轻轻地帮他擦着脸上的汗水。
虽然晚上没有吃饭,可是因为一个星期以来基本上没有睡觉,哥哥和我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突然,父亲用手指指着哥哥和我,想让我们到他的身边去。
母亲赶快把我们叫醒,让我们来到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