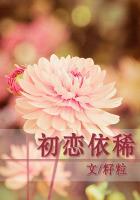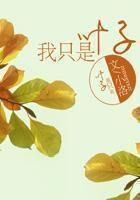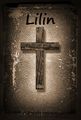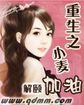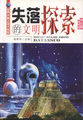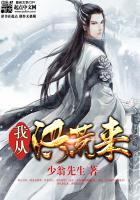“花儿”于20世纪20年代由地质学家袁复礼首先引入文化界,其后逐渐引起越来越多文化人的注意,进行搜集整理。关于“花儿”的渊源,《西北花儿学》从音乐、文学、民族、社会历史等方面作出了比较科学的推论:认为河州型“花儿”所受音乐的影响,主要是古羌族音乐、中亚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音乐和汉族音乐,前两者都是经过同汉族音乐相融合而成为中国音乐,并最后形成“花儿”音乐,因此,河州型“花儿”的音乐应当说形成于隋唐或元代以后。
河州“花儿”产生于古河州。河州是古地名,始于十六国前凉时期,终于民国初年。历史上它的地理外延很大,包括现在甘肃省的黄河、大营川以西,乌鞘岭以南,西倾山以北,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全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临潭、陇西、定西、武威部分,青海省的民和、循化、化隆、同仁(保安族原居住地)及贵德等地,其辖区延续至清朝末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回族、藏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各民族用他们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花儿”这一艺术珍品。
从文学因素来看,河州型“花儿”形体上的单双字尾同存于一诗的特点,在产生于唐代的曲子词中开始出现;而元散曲在语言的通俗化上则更接近于河州型的“花儿”;元明民歌中以爱情内容为主,这一情况无疑对河州型“花儿”作为情歌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这些情况,河州型“花儿”的文学形态只能产生于唐代以后,而以元明之际较为可靠;从创造这种民歌的民族看,河州型“花儿”主要是回族、东乡族、撒拉族、汉族等共同创造的,而这里的民族主要是在元末及明代以后形成的,因此,河州型“花儿”的产生年代不可能早于元代;从社会历史条件看,河州型“花儿”流行区所经历的历史是一个由以牧业经济为主向以农业经济为主演变的漫长历史时期。这一转变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反复,充满着动荡不安,直到元明基本上得以实现。因此,河州型“花儿”是一种产生在从牧业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时期的民间情歌,它的产生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明代为这种民歌的产生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有利的条件。所以,就这种民歌的某些因素来看,它的渊源是相当早的,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但就一种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具体艺术样式来说以及它是由几个民族所创造和传唱,并具有独特形式的、音乐和文学相结合的民间情歌,它的最后形成时间应当确定在明代。
从前面关于保安族族源的介绍中我们知道,保安族大约是在元朝末年经过动乱,到明朝中叶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当时的青海同仁一带是藏族居住区,并不是“花儿”盛传区。由于同仁在地域上属于汉、藏地区的接合部,回族中的商人、脚夫以及士兵把“花儿”带到同仁地区,在那里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保安族中较广泛地传唱并产生适合他们的审美要求的“花儿”。但是,保安族中大量创作“花儿”应当是清末迁居到大河家以后的事。我们从保安族“花儿”中可以领略到藏族民歌与“花儿”融合的现象。
“花儿”分为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保安族的“花儿”属河州型“花儿”。河州“花儿”是产生和流传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广大农业区的一种地域性的民间歌谣。随着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花儿”也广泛地流行于甘、青、宁、新等广大西北地区。生活在这里的汉、回、东乡、撒拉、保安、裕固、土、藏等各族群众,喜欢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保安族所在的积石山自治县形成了许多“花儿”会,有位于安集乡与胡林家乡交界处的五眼泉“花儿”会,寨子沟乡东平寺“花儿”会,刘集乡盖新坪“花儿”会等,自治县政府每年在盖新坪、积石民俗村举办“花儿”大赛。“花儿”的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积石山自治县成立之初,文化馆油印了内部资料本《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民歌集成》,2001年由董克义主编出版了《积石山爱情“花儿”精选2000首》。保安族“花儿”所属的河州“花儿”,主要以河州方言演唱,其格式奇特,句型、旋律简短固定,主要表达爱情内容。它有四句体、三句体、两句体,形成“花儿”圈。人们称其为大西北民族情歌。其音调高昂、辽阔、苍凉、婉转,十分动听。
在所有积石山的“花儿”唱词中,有的反映并展示着保安族的历史和发展轨迹,有的反映并展示着保安族居住地的风貌和民俗,有的反映着保安族的社会生活和爱情生活等。可见,保安族的“花儿”具有印证民族发展的历史的史诗性质。因此,马少青先生在《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中将“花儿”称做是保安族的“百科全书”。“花儿”在抒发感情上的浓烈性,具体表现为感情的真挚、方式的直露,对此,西北民族大学郗慧民教授在《西北花儿学》中曾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说:“似乎整个爱情生活都是在一种极其险恶的情势下进行的,面对着深刻而尖锐的矛盾,充满激情地和不顾一切地去爱、去思念,充分体现出生活在西北高原的少数民族的共同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它是一种雄奇、剽悍、粗犷和带有悲壮气氛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在西北高原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政治形势和文化传统的汤水里浸泡出来的,反映了这样的精神,也就反映了这样的社会面貌。”可见,保安族的“花儿”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感情,它们总表现得那么大胆、直截了当和撼人心魄。他们在抒发感情的浓烈性,主要表现在感情的真挚、方式的直露、格调的粗犷、气势的宏大和色彩的浓烈。所以说保安族人们扯着嗓子喊出的“花儿”,是内心的坦露和真情的表白。
保安族花儿属临夏“花儿”,亦称河州“花儿”,是保安族民歌的主要形式,在保安族民间文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保安族人人爱唱“花儿”,他们往往是触景生情,即兴编词,随口而唱。通过精练的语词、比喻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也常被青年男女在倾吐爱情时采用。
保安族“花儿”的基本形式是四句,前两句为比兴,也称引向、陪衬句,后两句为本义。其中一三句结构相同,每句三顿或四顿;二四句结构一致,每句三顿。四句工花儿的特点是单句单字尾。至于单句、双句的字数、停顿数,则因歌手的语言驾驭能力、文化修养、演唱技巧不同而有所差异。
保安族传统“花儿”的主要内容多为反抗压迫、歌颂爱情,尤以情歌数量多,艺术性更强。保安族人唱花儿有个规矩,即只能在山中、野外唱,不准在家里或村里唱,更不许在长辈面前唱。
2.宴席曲。保安族的歌谣中,有名的还有宴席曲。宴席曲是河湟地区各民族人民在婚庆宴席场中演唱的一种民歌,也是保安族说唱艺术中的主要形式之一。保安族的宴席曲融汇吸收了各族人民在婚庆宴席场中演唱的精华,集歌舞说唱为一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且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它是从结婚宴席上吟唱的婚礼小调衍变而来,不同于“花儿”,“花儿”一般被称为“野曲”,而宴席曲一般被称为“家歌”。
保安族宴席曲吸收融汇了河湟地区回族宴席曲的精髓,集歌舞说唱为一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内容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反映一般家庭生活的,有反映婚姻恋情的,也有反映生产场景的。其中《大马上备的是好鞍子》是一首在保安族婚宴上赞美新郎的小调,由前来道喜的年轻小伙子单独表演。它通过流畅、连贯、紧凑的词句道出客人们对新郎相貌、气质等诸多方面的欣赏。
(1)宴席曲的产生。宴席曲的产生除受当时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外,还有比较深厚的文学传统源流,其年代尚无定论。马克勋编着的《保安族文学》认为宴席曲是一种产生于宋末元初的少数民族民间“散曲”,它同元曲流行的时代和回族的形成历史基本上是一致的。回族形成的时代正是词和元曲兴盛的时期,当时的民歌对词、曲的产生和发展影响十分重大。早在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文化大交流中已有许多少数民族民歌传入中原,并很快与中原民歌合流,成为一种崭新的音乐体系,后来这种民歌传入宫廷,主要用于宴饮间的歌舞,故称“宴乐”。宋末明初,各种民间曲调和部分外来民族的乐曲,逐渐形成一种崭新的诗歌形式,这就是当时流传在北方的散曲。由于散曲是在“俗谣俚曲”的基础上产生成长起来的,因此它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间风格。再加上当时民族杂居区社会生活的影响,它必然吸收不同民族的曲调和声腔,这就构成了散曲不同于诗歌的特色。明代,民间文学得到了繁荣发展,民间产生了大量的民谣和歌曲,在城乡人民口头广泛流传,形成了民歌兴盛的局面。在当时统治阶级的正统文学一般表现为内容贫乏、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民歌的新鲜活泼引起了文人的重视。明代的民歌,大致分为传统的民间歌谣和当时新兴的民间“俗曲”两部分。
宴席曲在临夏地区成为几个少数民族的一种传统喜庆仪式曲,与回族的经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明代中期,社会经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空前发达,这给善经商而大分散小聚集的回族商贩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同时从元代留居河州的先民和戍边军士中就有传承的西域民间歌舞在一部分人中得到保留,在“宴席场”三天无大小的宽容场合,他们载歌载舞,创造热闹高兴的氛围,从而使之成为宴席场的喜庆活动仪式保留至今。宴席曲的曲调、歌词、舞蹈动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先民原来的文化影响,不仅是回族婚嫁喜庆节日里的一种娱乐活动,而且还是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民族的娱乐活动。
保安族宴席曲的内容有庆贺喜事的赞歌、倾诉社会生活的苦歌和欢歌,还有讽趣兼备的贬歌。赞歌是宴席曲的主曲,是在保安族青年男女举行婚礼的晚上,邻里亲友和村上的青年们同唱把式前来祝贺时唱的,它由门曲和院曲两大部分组成,一般进门前先唱门曲,到院内,燃起篝火,大家围成圆圈,边喝茶边唱起夸赞曲,进而赞至父母、兄嫂和亲友。有名的保安族宴席曲有《恭喜曲》《十劝人心》《没奈何》《出嫁歌》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出嫁歌》:
啊!我的父母哟!
从今日起我在人家的门上活尘土式的人哩,
我祝愿你们活得舒服,
每晚睡个好瞌睡!
感谢你们对我一生的抚育和操心,
从今日起,放下了你们的一片心。
你们受了人家的白银子,
受了人家的肉份子,
卸下了对女儿的重担子。
我生长在家里,
厨房里跑了千千遍,
为你二老侍候了万万遍!
今日我朦打胡涂地出门哩,
我的心就不安稳啊!
我心里害怕得很,
难过得很啊!
我的父母哟!
啊!媒人,我的媒人啊,
你凭着你的麻雀嘴,
当了我的催命鬼!
你当媒人想穿鞋,
花言巧语能把鸦鹊哄得来。
你当媒人想吃油馍馍,
你就把两家的大人哄得团乐乐。
你当媒人想吃肉,
山上的野兔你也能哄上了走。
我的媒人哟,
你就像枯树上的黑乌鸦,
搅得我颇烦不安稳呀,
哎,坏了良心的媒人哟!
啊,我的媒人,
你千万不要坏良心了!
《出嫁歌》是用保安语演唱的歌谣,表达了保安族妇女出嫁时的哀怨之情。在封建时代,青年男女婚嫁都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婚姻自由,这对夫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妇女来说,自己的婚姻美满与否,实在难以预卜,所以有的姑娘就又哭又说又骂,哭说的特别新颖别致,有心人听后再添枝加叶并进行传播。久而久之,演唱者们便把它们东拼西凑,创作成完整的作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制度的变化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这种以哭腔说唱的曲调逐渐消失,偶尔在宴席中由宴席曲的表演者所演唱,其目的也是为了娱乐而已。保安族宴席曲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其伦理道德方面。前面刚刚说过,保安族的宴席曲是在婚庆宴席场上所演唱的民歌,保安族的婚礼分为娶亲、送亲、闹宴席场等程序,整个婚礼过程充满喜庆色彩,男女老幼同乐,有“三天无大小”的习俗,即结婚后的三天内,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都可以尽情地欢乐,不必拘谨于平时的礼节和长辈晚辈之间的“规矩”,从而增加婚礼的热闹气氛。
从保安族欢乐喜庆的婚礼中,我们可以看出保安族青年男女追求恋爱婚姻自由、追求忠贞爱情的美好情感。尤其在“撒五色粮”的送亲仪式上,用抛撒五色粮的方式来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深深眷恋与报答,显示出保安族青年尊敬老人、孝敬长辈的美好品德以及当地淳朴、美好的社会风俗。一首《出嫁歌》,唱出了保安族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心声,以及忠于爱情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