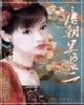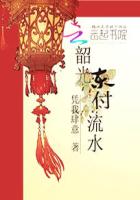第一节传统社会组织
我国少数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与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传统社会组织。尽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各不相同,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均具有血缘宗族组织向社会地域组织过渡的共同特点,带有明显的宗法性特征。保安族的传统社会组织也有着自身的特点。
一、乡约(寺约、回约)制度
清朝统治者利用伊斯兰教推行乡约制度,规定凡是有清真寺的地方“都由地方官择立该教公正之人充当寺约,责令束约回教”,“其无寺者,按其乡里人数择其老成者为回约”,进行“分段管理,各给印签,予限三年,期满更换,不须再立掌教名目,彼族其有不法之徒滋事行凶以及私立邪教等,即由该寺约、回约妥为禀官提究”。
这种以政权巩固宗教、以宗教维护政权的宗教封建特权曾经长时期地控制着保安地区,直至国民党统治时期,保安地区的官僚地主、族长、教主“三位一体”的统治形式愈演愈烈。马步芳统治临夏时,从青海派来了新兴教(即伊赫瓦尼)教长,掌握着大河家大寺所属各寺的教权。“八大家”地主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衣钵,自封为大河家四十二坊清真寺的“总管”。各小寺举行重要仪式时,必须得到“八大家”的许可。
二、谢乃
在保安族的聚居区,实际上每一个“村”都是一个“措娃”(藏语,部落),内部有若干“谢乃”(当地土族用藏语仍称措娃,具体含义不清)之分,各个“谢乃”都各有其名,在部落内部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似乎有等级之分。马家“谢乃”称做“马吉么合”,意为“马家军队”,迁走了六个。
“谢乃”对所属的每个家庭的重要家务和生产活动有很大的支配权,“措娃”对公共事务有很大的决定权。“谢乃”这种社会组织似乎有别于安多地区的藏族社会,据菅志翔的调查,年都乎、郭麻日、尕撒尔、下庄四个行政村的土族中现在还有30个“谢乃”。一位保安族老人说:“四十家一个马吉,原来分下的,大墩有两个马吉,甘河滩有四个马吉。”如果老人说的是对的,“谢乃”也许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组织方式有关,但这只是菅志翔的推测。李克郁教授证实,“谢乃”这种组织在互助土族中普遍存在,不同于藏族的措娃和汉族的宗族,但至今尚未有人做过研究。不论“谢乃”是不是四寨子蒙古人中间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方式,后来的移民全部被组织进“谢乃”中去了。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内地移民入门完全被吸收到蒙古人后裔的社会中去了,这种现象可以看做是结构同化。20世纪50年代调查的口碑资料里记录四寨子“土人”与移民通婚比较普遍。
从14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20年代的三个半世纪中,内地的移民实际上至少已经在语言、结构、婚姻、认同四个方面同化到蒙古人后裔中去了。虽然由于迁移的时间不同,人口的族群背景不同,四寨子人中间还有一定差异,但人们一致认为“我们是朝廷的人”,而区别于当地的原住民族。据《循化志》记载,“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多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为番民矣”,“保安四屯实内地民人,久居番地,染其习俗,竟指为番人,似误矣”。《西宁府续志》载,道光年间,保安营部将在上奏中将保安四屯全部统计为番民。
到清雍正六年(1728年)土千总王喇夫丹被杀、四寨子人的军籍被取消之前,这里发生的是一种后来移民同化到地位等级较高的早期移民中去,而与当地的其他居民隔离的族群现象。移民融合而形成的“四寨子人”自己并不认为他们与周围的吐蕃部落一样,而是认为自己是“朝廷的人”。当地的吐蕃认同也没有把他们认同为自己人,称他们是“汉四寨子”。但汉文文献反映出,汉人并没有将他们与番人区别开来。对于“四寨子人”身份的认定,自我认同与其他两个方向的社会一开始就不一致。这个时期,由中央朝廷的委托统治而造就的地方权力关系,也可以说是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和职业构成,决定了四寨子人的族群归属——既不属于“番”,也不属于“汉”,而是“朝廷的人”。由于当地吐蕃人的农业技术也有所发展,并逐渐出现了吐蕃农庄,这种情况下,社会阶层和权力关系就成为族群归属的首要的决定力量。
在保安族社会内部,目前仍有“谢乃”这一群体,总体上“谢乃”是一个大家务的分支,家务分亲方和“谢乃”,是一个爷爷的后代称之为亲方,爷爷兄弟的后代或者较远的后代称为“谢乃”。保安族内部“谢乃”从来没有发挥治理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它只是在婚丧嫁娶和重大节日时,凡是一个“谢乃”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平时它的凝聚力也是非常之小的。
目前,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面临着如何改善农村社会的传统治理模式,推进村民自治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村落里推行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尊重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发挥民族特有制度和文化的治理功能。
第二节家庭礼仪
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的家庭多为家长制的大家庭。家庭内父母、丈夫的权力很大,妻子的地位较低。长辈是家庭最高权力的支配者,任何人都得服从。在日常生活中,保安族的父权(家长权)主要体现在其尊老爱幼的传统习俗中。保安族非常尊重长者,忌子女不孝,长幼无序,“吃饭要端给长辈先吃;见到长辈要先道‘色俩目’,家庭中翁媳之间、兄与弟媳之间有回避之俗,以示对长者的尊重”。节日里,村里的孤寡老人受到无偿和应有的照顾。有这样一首歌谣:你一碗,他一碗,隔壁的大娜(婶婶)送一碗。你一元,他一元,大娜她一年不受寒。
保安族人就餐时要先洗手,让年长者先入座上席、动筷,然后其他人才能吃。饼子、馍馍、油香要用手掰开吃,不可啃咬或大口嚼咽。放饼时,注意将面子放在上面,掰开后没吃完的,不勉强塞让同席者吃。忌讳进食时出声音、喝茶用口吹或吸出声音,向客人倒水加茶时,要向内倒,忌讳反手向外倒,也不可用左手向客人递东西。
夫妻之间以丈夫的意志为主。舅父的权力在保安族家庭中占有一定位置,特别是对外甥的婚姻有决定权。在保安人家里,年轻妇女不能和男子同坐一席吃饭,而是让男子先吃,等他们吃完自己才吃,或者在厨房单独吃。做饭、倒茶、端饭在保安人来讲是做儿媳妇份内的事,婆婆至多是在人比较多、人手不够的时候帮一下忙。儿媳妇端饭进屋时腰要微躬,出门时略退几步再转身走出去。
第三节交往礼仪
保安族在社会交往中恪守“行善”“真诚”的伦理道德准则。在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要讨得有关人的同意方可行事,否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外族人认为保安族是“直杠子”,意思是他们对待朋友真诚、友善、直率、讲信用。
保安族是一个讲文明礼貌的民族,见面都要互致“色俩目”,年轻人见到长辈还要鞠躬。在日常交往中不仅用汉语互致问候,也常用阿拉伯语互致问候。“他们见面相互问候时,通用一种见面语,也叫祝安词,其问词全称是‘安色俩目阿来库木’(音译),意为‘求真主赐你平安’,答词全称是‘吾阿来库木色俩目’,意为‘也求真主赐平安予你’。保安族与回族一样把祝安词称为‘色俩目’,致者说‘色俩目’(平安,您好),回答者则说‘安色俩目’(平安,您也好)。如年轻人应向年长者道‘色俩目’;客人见了主人先道‘色俩目’;教民与阿訇相见,教民先致‘色俩目’;出门在外回来者应向当地留住者先道‘色俩目’;男对女先致‘色俩目’;少数人对多数人先致‘色俩目’等。穆斯林认为道‘色俩目’是圣行,是庄重之事,必恭敬为之,故在遇到对方赤体沐浴,或在厕所,或正在礼拜时,不说‘色俩目’。”
保安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当有客人来时,要迎于门外,然后请到炕上,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好茶饭款待客人,要把家中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招待,这是保安人最为重视的待客之道,客人满意了,主人才高兴。在与客人谈话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玩弄胡须、抠鼻吐痰,更不能伸懒腰、打哈欠。保安族还有“转客”的习俗,即如果有一家来了客人,这一家的亲戚和邻居也要请客人到自己家里做客,以尽地主之宜,以示这家亲戚的团结和睦。
保安族在待客时还有一些别具特色的饮食风俗。有客自远方来,都会受到热情款待。客人到家,首先要把客人让到上座,然后,先端茶,再上食物。用餐前,按照保安族的规矩,必须由一名年长的老人或家庭主人念诵一段《古兰经》,意思是感谢真主赐给了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动手就餐,如果是馍、饼之类的主食,必须由主人先掰开,然后客人才能取食。否则,被认为是不懂规矩。一般是一顿饭上三道饭菜,第一道是大饼或馒头,第二道是手抓羊肉或鸡肉,最后一道才是正餐精制的细丝面条。保安族在招待客人的时候,主人是不能和客人同坐在一起用餐的,主人只能站在地上不断地给客人倒水上菜劝客人多多用餐,这一习俗和东乡族是一样的,这一待客的方式充分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尊重。凡来保安族人家做客的人们被主人的这种感情所感动不已。待客风俗中还有,若来客是男的,中青年妇女是不能在男客面前随便露面的,要一直在厨房里为客人忙碌做饭菜或休息,待客人走后才能出来。
保安族还注重邻里友善,视和睦团结为民族生存的根本,祖祖辈辈同周围的汉、回、撒拉等民族相亲相爱、和睦友好。
第四节称谓习俗
亲属称谓是民间亲属制度的一部分。民间亲属制度,是关于民众的亲属关系、亲属观念和亲属称谓的社会规范。而“一个地方的称谓语系统可以鲜明地反映出此地的社会文化,包括传统习俗、伦理观、价值观、政治背景等。而称谓语的变化,又能及时地体现社会的变革与习俗的演变”。一般来说,称谓语可以分为亲属称谓和人名称谓两种,亲属称谓是所有社会所共有的语言现象,但是组成称谓系统的要素会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保安族的亲属称谓和人名称谓也代表了一定的保安族文化特色,反映出保安族的亲属制度及规范。
一、亲属称谓
保安人的亲族由父母、兄弟姐妹、叔伯、舅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儿孙等亲戚构成,保安人的亲族亲疏关系和教派门宦有很大关系,亲戚之间往往会因为不是同一个教派而疏远。保安族的家庭结构通常由夫妻儿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或直系家庭,也有三四代同堂的联合家庭。家庭中父母唯大,其次是丈夫在家庭中的支配权利很大,妻子的地位相对较低,父母是家里最高权利的支配者,任何人都得服从。在保安族中有“天是一大天,父母是一小天”的说法。同时舅父的权利也很大,保安人认为“阿舅是骨头的主”,所以外甥对舅舅是比较敬畏的。过去对外甥的婚姻大事必须征得舅舅的同意方可进行,就是在现在舅舅仍然有一定的权威性。
保安族的亲属称谓一般如下:爷爷——阿爷,奶奶——奶奶,外公——阿爷,外婆——奶奶,爸爸——阿保(保安语),妈妈——阿姆(保安语),舅舅——阿舅,叔叔——伯布(保安语),姑妈——阿嘎(保安语),姨妈——尕姨(保安语),岳父——丈人,儿子——尕孔(保安语),女儿——阿勾(保安语)。
二、人名称谓
保安族人在元明时期是没有姓的,只有一个伊斯兰教经名或称本民族名。以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采取了汉姓汉名。保安族十分重视给婴儿娶经名,婴儿出生后的几天内,请阿訇或年老者到家中,对着婴儿耳朵小声念经。所念经典章节中第一次出现的圣人之名就是婴儿的经名。男孩一般命名为“尔撒”“努哈”“易卜拉欣”“尤素福”“穆萨”“穆罕默德”“阿里”等,女孩一般起名为“海蒂彻”“阿依莎”“法图买”“阿米娜”等。婴儿长大后,在家中家人习惯称其经名。
保安族除了以伊斯兰教经典上的圣贤的名字命名外,还有以下命名法:有的以婴儿的生日命名,如出生在斋月的,就命名为“莱麦丹”;出生在古尔邦节的就叫“尔德”;出生在星期四,命名为“杜什儿”;出生在星期五,则命名为“主麻”等。有的以次序或排行命名,如女孩称为二姐儿、三姐儿、四姐儿,男孩称为老娃子、老疙瘩、老大、老二、老三等。还有的以动物命名,如牛娃子、虎子、羊羊、黑猫儿等。有的在经名前冠以汉姓,使汉姓与经名相结合,如马穆撒、王尤拜、黑牧杜尔,也有终身用经名的。
上学后取学名。学名由学校的老师取名,因而,不注重排行,只问其父有无学名,如有则避其父学名起名。学名中最具典型的有:占林、占龙、福贵、福寿、如虎、如龙、腾龙、腾云、成祥、福祥等。学名也有时代特色,明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生的孩子,起名多为文革、文红、东风、红卫、卫东等。
第五节生育习俗
保安族喜多子多福,早生早富贵。保安族没有固定的求子仪式,如果久不得子,父母会到拱北去施敬财物或请阿訇念经,祈求真主赐予男孩。保安族在过去提倡早婚,认为早生儿女早得福,并以生男孩为荣,认为若生了女孩而未生男孩,就是断了家中的根,是人生中的不幸。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