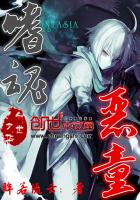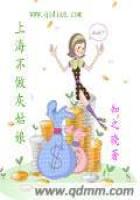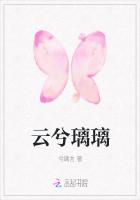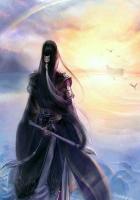第一节商贸往来
保安人早年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少量的牧业;有的人家自养少量的山羊、牛、驴等牲畜,生产水平十分低下。早年在保安城内有各种手工业匠人,这些匠人中除少部分汉人外,主要是保安人。他们有制作土枪、弓箭的,有铁匠、木匠、鞋匠和金银匠等。四寨子一带也有制作妇女头饰的,如银盾、耳环、笛子之类的金银制品。他们的手工艺很好,经常为寺院雕像作画,深受当地土族、藏族人民的欢迎,收入较高,又受人们的尊敬。在保安族的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商业活动占有重要的地位。
经营小本生意是保安人经常的商业活动。有钱人做大生意,贫苦百姓做小买卖,商业几乎与农业一样成为保安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保安人经商的特点是行商,他们的足迹遍布西北各地。早年的行商中最有名的是“藏客”和“松潘客”。保安人在定居大河家以后,商业更加活跃,他们的足迹遍布西北地区、西藏乃至印度。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按其资本和活动范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称为藏客,他们的活动范围广,经商的路途遥远,但是资本多。第二种类型称为松潘客,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甘肃、青海两省的藏区,资本相对来说比较少。第三类是小商小贩,就在附近的一些地方进行交换。保安族人进行大量商品交换的集镇就是大河家和刘家集。据《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刘家集,县西一百里,居民二百户,三六九为市,产核桃,年出市斗八百余石,花椒万余斤;大河家集,县西一百二十里,居民三百余户,双日为市。”
一、保安族早期的商贸活动
商贸活动在保安族群众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保安人定居大河家后,商贸活动日趋活跃。
清末的保安地方,随着保安站、堡等行政建制的加强与扩大,不仅成为一条通往西宁和内地的交通要道,而且随着贸易往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贸易区。当时,保安堡已有“番”“回”商贾百余家,保安四屯居民共千户以上。村寨相连,各族自成街坊,人来人往,已呈现相当繁荣的景象。
四寨子一带,除资本较大的几家富户既经商又放高利贷外,大多数的商业资本仅有几百元。他们从河州、循化或隆务镇集市等地购得一些盐、茶、烟、糖或壶、碗、布匹等,去藏区换得一点酥油、皮毛等畜产品,来往辛苦,本小利微。虽然这些收入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一些补助,但是终年长途跋涉,生活极不稳定。
民国17年(1928年),保安族马三十六、马全成、马胡录等10多人第一次经西藏去印度做生意,自此,到印度做生意的保安族人逐年增加,形成了一支经商马队,人数累计前后有500多人次。据“保安三庄”的老人回忆说,过去我们保安人有个讲究,“备好一马三件,不愁走南闯北”,即一匹好马,一件好皮袄,一杆好枪。自1928年到1949年的20年间,每年有20至30人从大河家来往于西藏或印度之间。
当时有本钱的人走西藏、印度,本钱小的人走柴达木、宁夏、内蒙古和四川阿坝、松潘做生意,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人,开始在内地城市如上海、北京与西藏和印度之间做生意。保安商队走的主要线路是藏区和蒙区,因此,被称之为“藏客”和“松潘客”。当时交通工具只有骡马,往返十分艰辛。商队出发前备好食物,约定在一个地点集中,统一出发。每个人要赶上20匹左右的骡马,每4人至5人带一顶帐篷,也有10多人带一顶帐篷的。从4月开始离家,8月到达西藏,到西藏后除留自己的乘骑以外,把其余的骡马卖掉,把银子和白洋换成“印币”,然后骑马越过喜马拉雅山,艰难行走20多天,到达印度边境嘎伦堡地方,把自己乘骑的骡马也卖掉,坐汽车到火车站,又乘火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当地买上水獭皮、漆皮、布匹、珊瑚、藏红花、铝制品、琥珀手饰、手表、颜料等货物,于同年腊月返回西藏,把部分货物在西藏售出,又在西藏买些毛毡、耗牛等物品,途经青海藏区时出售一部分货物。因路途遥远,加之牲畜走得又慢,第二年11月才能回家。回到家后把牦牛和剩余的货物在当地全部销售。商队经过青海时,按所赶骡马的多少,给马步芳一定数目的税钱。为防备路途土匪抢劫,商队中的每人都有一支好枪,是从青海官方那里买来的,他们有时同青海官方商队一同走。因保安商队凝聚力很强,具有团结协作和特别能吃苦的精神,个个机智勇敢,擅长做生意,官方商队称赞为:“保安人一匹马、一杆枪、一件皮袄,西藏印度跑趟子,真厉害。”马步芳还会见过商队代表马六十五等人员,欲聘几位副经理,因他们厌恶马家官僚而婉言谢绝。
193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进藏时,保安商队一直护送他到日喀则,因此,西藏僧俗中有很多保安族的好朋友,他们在路途客栈给保安族商队提供过诸多方便。商队中每年有人结伴而行去麦加朝觐。在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中有一批去过印度的“藏客”和走过四川、内蒙古的“松潘客”,以及来往于上海、北京等内地的“中原客”。保安族商客对促进西北地区的商贸发展,增加经济收入,繁荣经济和推动保安族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保安三庄”所处的大河家镇地处于甘青两省和永靖、民和、循化三县交界处,又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在民国初年,大河家镇已初具规模,店铺、饭馆、大小商贩近百户,在大河家经营棉布、杂货的有“永盛茂”“兴盛福”“全盛祥”“永盛祥”四家商号,在刘集经营布匹、杂货、副食的有“积顺昌”“渊发明”“敬信义”三家商号。
二、集市贸易和民间商贸
集市,是积石山县民间物资交流和民族贸易的场所和商品集散中心,也是保安族商贸活动的主要途径。积石山的集市贸易历史悠久,早在清初,已形成若干集市。据《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在民国初年就有居家集、吹麻滩集、刘家集、大河家集。新中国成立后,上述四个集市贸易一度十分活跃。“文化大革命”中取缔了集市,将各集商户、摊贩和居民遣送山区务农,使本来落后的经济更加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放宽了经济政策,恢复了集市贸易,集市又成为各族人民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经营工商业、交流信息的中心。集市增添了农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短短几年间,商业、服务业、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迅速发展,市场扩大,买卖兴旺,成为农工商经济联系的纽带。集市贸易交流的商品除各种棉、麻、丝绸、化纤等纺织品、针织品外,还有日用百货、各类家禽、粮食、油料以及瓜果、药材、皮毛、山货、保安腰刀、小农具等;理发、照相、油漆、木工、缝纫、饮食等各类服务行业也相继出现。癿藏、居集、吹麻滩、刘集、大河家五个集市从临夏至大河家公路沿线,各相距10公里左右,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其中居集和刘家集是原临夏县有名的五大集市(另三个是韩集、马集、尹集)中的两个集市。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家集、大河家集仍然十分繁荣,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两个地方成为连结青海、甘肃等地的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个体经济十分活跃,如今的保安人做生意大部分都坐着飞机、火车往来于全国各地,并将其他城市的商品带到大河家、刘家集。
大河家集临近黄河渡口,赶集的除保安、撒拉、回、汉等族之外,还有黄河对岸青海省民和县的土族、藏族,以及积石关外的循化撒拉族、藏族,是两省三县物资商贸交流的中心。操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民族在这里开展各种交易,传递各种信息,交流生产经验,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繁荣了保安族聚居地的经济。
第二节族际往来
保安族人民世世代代居住在隆务河边,与周围的汉、藏、回、土等各兄弟民族,朝夕相处,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开发了这片土地,同时也建立了亲如兄弟般的民族友情。然而,直到清咸丰末年和同治初年,保安族的聚居区仍是土司、头人、边官武吏交叉统治的地区。由于当地土司头人和寺院上层喇嘛等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展,且清朝统治者采用扶此抑彼“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同仁地区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如保安族与当地藏族因水渠问题引起纠纷,矛盾激化;同仁地区的统治者为扩张势力,强迫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族人民改信喇嘛教等。可以说,这些是迫使保安族举族东迁的直接原因。
尽管由于各种矛盾及清朝统治者的处理不善,与有的民族部落发生摩擦甚至械斗和流血事件,迫使保安人离开故土,迁到今甘肃省积石山县,但他们与故地各族人民建立了宝贵的世代友好关系。
一、与汉族人的关系
和其他民族和谐相处、互敬互爱是保安人民世代相传的美好传统习俗。今天,在保安人民中间,还流传着“三邻居”的传说,这个传说反映了保安族人民渴望民族团结、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保安族人民深深懂得民族团结的重要和民族友谊的珍贵。
由于保安族世代传承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传统,所以,早在清朝同治年间,保安人从青海逃命的时候,就得到附近朗加藏族部落的保护。从此,保安人迁徙到大河家后,十分珍惜民族间的友谊,祖祖辈辈同周围的汉、回、撒拉等族和睦相处,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佳话。
保安族聚居的大河家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历代反动统治者一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造成了许多惨痛的仇杀事件。从清乾隆年间到1949年前后,曾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民族斗争,虽然如此,各民族人民之间不乏友好相处、团结和睦的动人事例;每当民族矛盾爆发,各族人民互相掩护、互相解救的事比比皆是。
1949年,当地残匪猖狂地枪杀大河家一带的汉民时,大墩村的几十名保安人拿着刀枪日夜守护着邻近的汉民郭家村。据该村郭殿成回忆说:“由于保安人的保护,新中国成立前夕最乱的时候我们村没伤亡一个人。”
尽管反动地主、军阀百般地挑拨和破坏,但是保安族和汉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团结互助不仅没被切断,反而愈加亲密了。
马结邦(1860~1931年),保安族。积石山大河家乡大墩人。1928年,因驻守河州的国民军将领赵席聘故意挑起回、汉民族间的矛盾,大墩尹家山村的汉族农民张五月保便成为附近起事回族追捕的目标。马结邦得知后,冒着生命危险把张五月保接至自己家中,藏在家中的地窖10多天,使其躲过了这场灾难。马结邦救出张姓汉族的事迹,是积石山一带保安族与汉族之间和睦团结的典型事例。
据梅坡村的一位保安族老人回忆:“梅坡村新中国成立前约有100户保安人,附近有个15户的汉民村庄。民国18年(1929年),国民军来了,要枪杀穆斯林,是这15户汉民保住了我们的命。1949年反动的回族头人煽动我们杀汉民,我们梅坡村的保安人又保护了15户汉民。旧社会,我们保安族和汉民就是这样,一家保一家,一家护一家,团结得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保安族同其他民族的团结又揭开了新篇章。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在分配胜利果实时,各民族、各乡互让互选友爱倍增。大河家地区因是“马家王朝”历代居住之地,土豪官僚较多,没收的财产也多,而居住在积石山关外的循化孟达乡的撒拉族、藏族人民生活困难,保安族群众提议,孟达是大河家通往循化的交通要道,长期以来大河家各族人民同这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应该让他们也分享胜利的果实。于是,大河家地区在1952年4月20日,派了7名代表送胜利果实至积石关时,循化县派7名代表前来迎接;21日循化县召开大会,将大河家送的毡、毯、衣服、家具、现金等分送给孟达乡的群众。撒拉族农民马四力高兴地说:“今天分配的东西我们老五辈的人没见过,关内的弟兄对我们太好了。”
高赵家村气候较热,耕作比沿山一带早,但是缺牲口。汉民居住的河崖村靠近积石山,气候凉、耕作迟、耕地多而劳力缺。因此,每年在春耕时,河崖村的汉民便赶着牲口下山帮高赵家村保安人春播;夏收时高赵家村的保安人上山帮助河崖汉民收麦子。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更为团结,逢年过节都互相拜见问候,像亲戚一样地来往。30多年来保安族同周围汉族、回族群众一起,对有损于民族团结互助的行为都严肃批评。老人们经常用过去互相团结友爱的事例教育后代珍惜民族感情,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这种世代相好的传统影响下,各民族之间互相关心、解囊相助的事情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