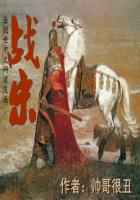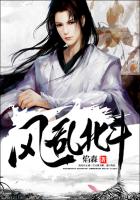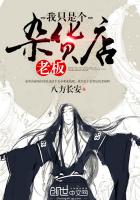1981年春节有个汉族村的汉族群众准备扭秧歌、闹社火,梅坡的保安族群众捐助资金,支持他们置办道具。落实宗教政策后,修复了清真寺,汉族群众自动筹集小麦、现金以及花茶、被面等礼品前去祝贺。保安族群众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相处得真像亲兄弟一样啊!梅坡村第十合作社只有马世祥家一户保安族,其余全为汉族。30多年来汉族群众对马世祥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马世祥的弟弟参军,汉族群众像欢送自己的亲人一样给他披红戴花;马世祥结婚,汉族老乡送礼放炮、热烈贺喜。马世祥曾多次被人劝说搬到保安人多的庄子落户,他总是说:我实在舍不下汉族乡亲们。像这样民族团结友爱的事例,在保安族、汉族杂居的村庄举不胜举。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强迫保安族养猪,不允许保安族妇女带盖头,周围的汉族群众对这种违反民族风俗习惯的做法非常不满,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有一部分汉族悄悄把保安人养的猪赶到自己家里。“文化大革命”中揪斗保安族干部,多数汉族都采取明斗暗保的方法,汉族干部挨斗时保安族群众也没有一个上台去斗的。各民族之间结成的这种凝聚力是很强大的,任何人都破坏不了这种民族间的神圣友谊。
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各族人民也表现了团结互助的高尚风格。在1981年8月的抗洪中,充分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非险区的大墩村保安族群众调配农机具和劳力,帮助险区的汉族、回族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共出工215人,帮助抢碾小麦21000斤。近几年来,在保安族中涌现了一大批维护民族团结、积极投身“四化”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1983年9月,有7名保安族代表光荣出席了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保安族社员马麻乃还被树立为全州民族团结的典型。进入21世纪后,当地汉族同胞和保安族同胞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年64岁的汉族医生何世英44年来坚持如一日,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用自己的医术帮助保安族群众,经她接生的保安族新生儿就有600多名,许多家庭两代人都是她接生的,成为保安群众爱戴的“白衣天使”和“好妈妈”,同时她还负责了5500多名保安村民的医疗保健工作。多年来,每逢过年过节,经她治疗帮助过的保安族同胞都会结伴去看望何医生,不仅把她当成了一名医生,更当成了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亲人。2010年,新华网、《甘肃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何世英的先进事迹,在她的精神感召下,先后有22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加入到了服务积石山、服务保安族同胞的行列,极大地改善了保安族群众的医疗卫生水平。
保安族历史上虽然也务农,但耕作是粗放型的,施肥播种都是“乱肥乱子”。到大河家定居后,在汉族群众的帮助下,保安人逐渐掌握了调茬种地的耕作方式。如去年种豆子或杂合(大麦、豆子)的地,今年种麦子最适宜;去年种麦子的地,今年种豆子或杂合最好。夏天作物地种洋芋最好,老麦、佛手麦不可种在洋芋秋田里。开花田(指种荞麦、豆子等的地)种大小麦最适宜,如果第二年和第三年种麦子,第四年再种豆子,以后结得很好。糜子地里种豆子也很好,故当地有这样的谚语:“糜茬里的豆,一镰割不透。”
此外,种地还要看时令,清明前后适宜种胡麻,谷雨时节种大谷、小谷最适宜。以前每年开春下种时,保安人民总习惯“九”完了才种,可是汉民在“七”“八”“九”里就下种,“九”尽了,庄稼也种完了。这样早种早收,可使庄稼在成熟季节少受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现在的保安族人接受了这样的经验,提早了播种时间。以前保安族定居的大墩、梅坡、甘河滩等村因大部分是旱地,所以不种冬麦,而今因为政府投资引来了山峡水,每个村水浇地面积增多了,所以种冬麦的农户多了起来。
保安人在来大河家之前,所种的粮食作物只有青稞、麦子、荞麦、豆子、胡麻等;来到大河家之后,通过向汉族人民学习,又增加了白麦、蓝麦、佛手麦、老麦、大燕麦、豆子、大黄糜、黑糜、黑谷、白谷等许多作物品种。原来的保安人没有种菜和吃菜的习惯,在汉族的影响下,现在常种的蔬菜有白菜、青菜、莲花菜、韭菜、菠菜、萝卜、葱、蒜、辣子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保安人的物质生活。
以前种地时,保安人不重视选种,往往在地边或场上随便选一些作物种子,没等晒干就堆砌起来,因此,每年总有一些种子霉烂,庄稼总有不少黑穗(即空穗),特别影响产量。后来,在汉族农民的帮助下,保安族人民重视选种,并学会了拌种技术,如麦种用清油混上些房檐上的尘土拌,洋芋种用炕洞的小灰拌,大麦种拌上牛羊粪等,这对苗全苗旺很有好处。
在犁地上,保安人原先只是每年一次,学习汉族人民的经验后,现在已是三犁三耙,当地有谚语“庄稼三犁三耙哩,买卖要照本做哩”。第一次犁耙地是在庄稼收割后立即进行,犁过后让太阳晒上五六天,最为理想,如果地刚犁过就下了雨,还须补犁;第二次犁耙地是在第一次犁耙地的10天后;一个月后再犁耙第三次。庄稼经过三犁三耙后,产量可显着提高。
在锄草上保安人原先使用的是较笨重的铲子,铲草时要弯腰,很费力。同时由于锄草、刨土是向后的,很容易压坏幼苗。汉人的锄子小巧灵活,适宜坐在地上锄草,这样又快又省力。同时由于是向前锄的,可以避免刨出的土压坏禾苗。现在保安族人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过去保安人民施肥不掺土,直接就薄薄地乱撒在田里。迁徙大河家后,学会了汉民的办法,天天垫换牲口厩房和粪坑的土,将这些粪土堆起来经太阳照晒发酵,快到春耕时,把粪土砸细,均匀地摊在田地里。
在农具上,保安族原先用二牛抬杠,杠很长,并为直形的,很不灵活,转弯不便,地边的四角犁不到。后改用了汉族短小灵活的杠犁,地边四角也能犁到了。
保安族原先不用耙子,犁过地只用榔头随便将地拨平一下。到大河家后,他们也使用耙子磨地了。连枷也是保安人来到大河家以后才使用的,原先保安族在打场脱粒时,使用的是一种长长的皮条,既费力又危险。现在使用连枷,又方便又省力。保安人原先用的木铣把子很短,用起来弯腰费力,现在也已改用汉族的长把木铣了。在青海同仁时,保安族用来碾场的碌碡较小,现在也改用了汉族的十二个齿棱的大碌碡。
在收割庄稼的时候,过去保安族人总是要等地里的庄稼黄透熟透才收割,而且时间也抓得不紧。这样,若遇雷雨或冰雹,庄稼损失很大。现在,他们接受了汉族农民的“田黄一时,龙口里夺舌”“黄田不能等,随黄随收”的收割经验,也采用了早收快收的办法。
保安人以前是刚割完庄稼就碾场。后来,他们学习了汉族的碾场方法:庄稼收割后,先整齐地堆起来,让太阳晒几天后再碾,这样可使粮食的颗粒更加饱满。
在汉族的热情帮助下,保安人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很快的提高,现在他们所种的庄稼和汉族相比,毫不逊色,并且在保安人当中也出现了不少种庄稼的能手。
二、与藏族、土族、撒拉族的关系
在明末清初之际,保安族居住的今青海省同仁县已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大杂居的“四寨子”(又称“四屯”,即尕撒尔、年都乎、吴屯、保安)。在保安城内杂居着保安、回、汉等民族,多为历代“守边防番”的“营伍人”和他们的后代。城外有上、下两庄,上庄住有土族,称为“五坊头”,下庄由保安族居住,俗称“四坊头”,又称“四坊马家”(意为下庄的四个马姓家族)。尕撒尔住有保安族、土族等民族。年都乎主要居住着土族,也有少数回、汉、撒拉等族杂居。
保安族聚居的尕撒尔、保安(妥加)、下庄三地被称为“保安三庄”。四周邻庄均为藏族、土族部落,即称之为“同仁十二族”(意为同仁地方的十二个以藏族、土族居民为主的大部落)。
清咸丰末年和同治初年间,保安族响应西北回民起义,反抗清朝的反动统治,同仁地区的统治者怕回民起义的烽火燃烧到他们统治的辖区内,于是挑动部分藏族部落头人鼓动不明真相的牧民群众迫使保安族迁走。
据说在民族纠纷发生后,部分藏族部落集兵,要侵袭保安人,藏族另一部落“吴屯”的头人“吴屯王爷”速传讯给保安人。朗加部落群众接应了由保安城北水洞逃脱的部分保安人,并与下庄出逃的保安人一同护送,使他们顺利到达今青海省循化地区。从此保安族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流落到循化街子一带。
居住在隆务河西岸尕撒尔村庄的保安人,听到保安城和下庄的保安人被迫东迁的消息,感到势孤力单,难以继续在此居住,于是他们在马牙拉、马三哥、马六十(一说马三十)等老人的率领下,在附近藏族、土族部落“浩仑那卡”的护送下,舍弃家园,随后也来到了循化地区。
传说保安族迁到循化地区后,受到当地撒拉族人民的热情款待,被安置在循化城西韩姓“上四工”(街子工、查家工、苏只工、查汗大寺工)的许多群众家中。后因当地人多地少等原因,两年后保安族再次东迁,于清朝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1863年)过积石关,来到了今甘肃省大河家地区。
保安人初到大河家地区时,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地、人口稀少,且主要是汉族居住。他们被安置在回族较多的癿藏地方居住。后因癿藏地方经济生活条件差、人多地少,当时又因清朝对太平天国用兵,西北地区苛捐杂税繁重,各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同时,整个河州地区又卷入西北回民起义的巨浪,造成刚到此地的保安族人民深受社会动荡之苦,生活极不安定,于是他们重返大河家。原尕撒尔的保安人住在大河家的大墩村,保安城的保安人(妥加入)落户梅坡,下庄的保安人一部分到了甘河滩居住,另一部分再回到癿藏的甘藏沟、麻巴、旧城落脚。这部分人不久又被安置在柳沟乡的尕集、斜套和刘集乡的高李定居。至此,保安族离开青海同仁地区辗转迁徙5年左右,最后定居大河家等地,形成了新的保安族聚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