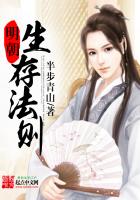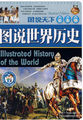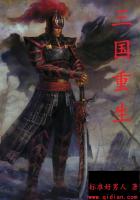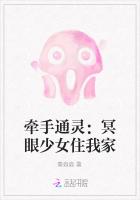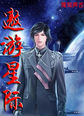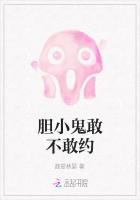打牙仡佬:这一支仡佬族有一种特殊的习俗——打牙。打牙是古代僚人的一种显着习俗特征,原本是生活习俗和葬俗。据史书记载,女子在十五六岁时,便打掉右边的一颗牙齿,做成耳饰,称为“筒环”。又有史书记载,父母去世之时,子女和媳妇要打下两颗牙齿放入棺材中,随棺入葬,以示永诀。后来,这种打牙的习俗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婚俗。女子在出嫁之时为了防止对夫家造成危害,要先打掉两颗门牙,成为结婚礼仪中的一部分,并将额前的头发沿眉处剪齐,取齐眉之意。在《职贡图》《苗蛮图册》和《番苗画册》中都描绘了新娘出嫁时被打牙的生动场景,或者被打牙后疼痛的样子。打牙习俗带有一定的强迫性,这也说明这一习俗发展到了晚期,走向衰亡。有诗云:“桶裙无褶织青羊,最爱夫家不忍伤。新妇一齐龋齿笑,打牙风俗太荒唐。”打牙仡佬性情比较剽悍,好斗,主要分布在黔西、织金、普定、黄平、清镇等地,如今打牙的陋习已经不复存在。
锅圈仡佬:最早见于《黔书》,这一支仡佬族得名于女子的发式。女子多用青色帕子将头发拢成锅圈状,穿青布衣服和短裙,男子穿斜纹布织成的衣服。锅圈仡佬人受彝族的影响较大,人生病了不求医问药,而是用面做成虎头的形状,再装饰一些彩色的线绳,然后放入簸箕内,请鬼师来作法事祈祷,这种祛病仪式来源于仡佬族对生病原因的宗教理解,认为人生病是妖魔作祟的结果,用虎头来禳灾除病是因为虎乃百兽之王,威武雄壮,能够吓走妖魔。锅圈仡佬嗜酒,懒于从事农业劳动,主要分布在平远、安平、大定等地,今天这一支系已经消失。
打铁仡佬:明清时期,仡佬族地区的手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制铁技艺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这时,出现了专门的铁器工匠,专门打制铁质农具。他们不但铸铁犁铧、大刀、锄头,还会制造鸟枪,所造的鸟枪质地优良,受到附近各民族的欢迎。人们称他们为“打铁仡佬”,主要分布在黄平州、黎平府、平远州和大定府境内。
披袍仡佬:这一支系的名称也十分形象,突出了族人服饰上的特点,披袍仡佬男女都穿只有一尺多长的短衣,外面披上一件袍子,前短后长,没有衣领和袖子,从头上笼下,女子喜欢将羊毛染上各种色彩织成裙子穿。《职贡图》中说披袍仡佬属于苗族或布依族中的一类,宋代时并为乌撒蛮部,元明时期归土司统辖,康熙时改土归流。《苗蛮图册》和《番苗画册》中都描绘了他们冶炼铁器的场景,记载说披袍仡佬性情淳朴,严谨勤劳,善于农耕,并赋诗云:“冶炼炉边种又分,铸犁为业最殷勤。妇人无事披袍坐,细染羊毛织彩裙”,介绍了披袍仡佬的主要特征。该支系主要分布在平远、施秉、安平等地。
水仡佬:该支系是因居住在山涧盆地或江河岸边,擅长捕鱼而得名。《职贡图》和《苗蛮图册》中都描绘了族人在溪流中捕捞鱼虾的劳动场景,说水仡佬擅捕鱼,即使是隆冬时节也能入渊捕捞。男子一般穿青布衣服,女子爱穿细褶长裙,族人敬畏官府,遵纪守法。婚丧嫁娶仪式和苗族很相似。曾分布在余庆、镇远、施秉等地,如今这一支系也已经消失。
土仡佬:这一名称在前代的典籍中没有见过,在《百苗图》中首次出现,并把他们归入苗族的一支,而非仡佬族。这一支系的人生活的地方山高天寒,土地贫瘠,没有成片的森林,靠旱地粗放耕作为生,较为原始,男子通常身披草编织成的蓑衣,用热油搽脚,以防脚底被荆棘和石头划破,结伴出行,为别人做雇工。各种抄本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都和这种记载相吻合,他们主要居住在威宁地区,但今天已经消失。
猪尿仡佬:又称为“猪屎仡佬”。很明显这是一种侮辱性称呼,体现了别的支系或民族对这一部分仡佬族人的蔑视。这一支仡佬人长期与土家族、苗族及部分侗族人杂居,是受土司控制的半自由民。明初罢废思州、思南土司后,土家族、苗族和侗族被编入户籍,仡佬族人周边各族的土地私有化不断扩大,他们流动生活的区域日趋缩小,加上人口稀少,社会凝聚力不高,难以与其他民族抗衡。为了防止家中牲畜被盗,只好将牲畜关入房屋里,这就是图录中说的他们与猪狗等家畜住在一起的真实情况。这一支系的仡佬族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粗野蛮横的。据说他们长年不洗脸不洗澡,以打猎为生。男子性情粗野,有仇必报,并随身带刀,经常发生争斗,喜欢与人拼命,打死人者只需赔偿对方一头牛。这一支系主要分布在黎平、石阡、沿河等地,而居住在清平地区的一部分形象稍好一些,比较遵纪守法,通晓汉语。图录中有诗云:“食兽如狼喜自雄,往来佩剑且弯弓。清平约束形稍改,守法还教汉语通。”
雅意仡佬:他们自称“咪达”,习俗与仡佬族其他支系有所不同,雅意仡佬老人死时,亲人就在其床上为死者洗净身体,换上寿衣,用十二种家禽野兽的爪、角串好,挂在小锄上放在棺材前卜卦,再念经埋葬,然后在其墓前各栽一棵梧桐河松树。雅意仡佬大致分布在黔西一带。
第二节历史沿革
一、远古时期
我们把仡佬族称为贵州这片土地上的地盘业主,可以从考古中寻找到一些踪迹。近年来,在黔西北的赫章、威宁地区先后发掘了一大批具有浓厚地方民族色彩的古代墓葬,当地的彝族群众把这些古代墓葬称为“濮素坟”。其中在赫章县可乐发掘了近二十座墓葬,发现有人类头盖骨和牙齿以及铜发钗、鎏金铜柄木梳等装饰品,这些墓葬的葬俗在国内十分少见。从墓中出土的发钗和木梳等陪葬物的情况看,应当是被称为“魋结”之民的夜郎地区濮人的遗迹,也就是今天仡佬族的先民。
从黔西北地区的墓葬中,发现有水稻和大豆的遗存以及麻布的残片、陶纺轮等物品,可推断仡佬族先民很早就进入了定居的农耕生活,妇女们已掌握了一定的纺织技术;出土的辫状立耳铜釜上能够找到合铸或者焊接的痕迹,许多生活用品都施以鎏金,说明当时仡佬族先民已掌握了一定水平的手工铸造技术,社会分工也有一定的发展。此外,在兴仁、兴义、安龙、普定、平坝、清镇等地,分别发掘和收集了一批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历史文物,这些考古发现让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想象,来描绘一幅仡佬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情景图。他们斩断荆棘、拔除荒草,然后用青铜锄或铁锸整土播种,所收获的粮食用铜釜炊煮。妇女们四处采集野生纤维,或者种植麻类植物,再纺线织布以供衣着,还有专门的手工业技能人员为大家铸造铜器等生活用品。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始出现了部分剩余产品,贫富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时,仡佬族先民早期社会中产生的血缘组织——寨老制逐渐演变为以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农村公社组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掠夺战争的日益频繁,农村公社组织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统治者奴役和剥削广大群众的机构,原来的氏族、部落首领也随之由社会的公仆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君主。
二、濮人与奴隶制国家
殷商时期,仡佬族先民濮人进入了部落联盟阶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自春秋以来,遍布于今天西南和中南广大地区。春秋初年,濮人在西南地区建立了牂牁国以及鄨、鳛等小国。战国初,牂牁国衰落,其南部为南越国所占,北部的另一支濮人兴起,建立了夜郎国及其邻近的地方邦国。夜郎国建立起了作为国家支柱的军队,并通过武力扩张,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国,称霸一方。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夜郎国拥有十万精兵,奴隶制国家机器得到了一定发展,最强盛时所统辖地区包括今天贵州省全部、云南省东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一小部分以及四川省南部的部分地区。
西汉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经营西南地区,“募豪民田西南夷”,将大批中原劳动人民和豪强地主迁入夜郎地区进行屯垦,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濮人地区的社会经济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铁农具已广泛用于生产领域,但制作还十分粗糙。而仡佬族先民正是使用这些简陋的工具“开荒辟草”,垦殖出大片的耕地和农田,为西南地区的开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时期,夜郎地区的畜牧业和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制陶和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拥有了自己的酿酒业。商业活动也逐渐繁荣起来,尤其与巴蜀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贸易来往,商人阶层开始出现,带动了夜郎国地区交通的发展,并出现了一些人口相对集中的“邑聚”(即城镇),成为商品货物集散地以及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汉武帝派大将唐蒙出使夜郎,唐蒙以绫罗绸缎等厚赐夜郎王,并喻以威德,双方达成了协议。汉王朝开始在夜郎境内设立县治,委任多同之子为县令,王位世袭制在濮人地区得以确立,逐渐产生了封建关系的萌芽。夜郎国及其周边的各个小邦都纷纷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统治。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年~前25年),夜郎王兴、句町王禹以及漏卧侯俞互相争夺而战事频繁,汉王朝派出使臣前往“持节和解”,夜郎王兴拒绝调解而遭斩杀。这样,群龙无首的众邑君慑于汉王朝的威力也都纷纷归降。至此,统治濮人地区四百余年的夜郎国覆灭了。
三、汉魏时期的大姓势力
汉魏时期,战乱频仍,为了解决粮饷供应等问题,一些封建地主和豪商纷纷招纳农民,到广大的西南夷地区屯垦。而这时,中央王朝对当地土着上层推行“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政策,使他们逐步演变成为夷、汉“大姓”集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独统一方的强大势力。
据汉文献记载,当时仡佬族先民地区的夷、汉大姓主要有龙、傅、尹、董、谢等家族。除谢氏以外,都是从“三蜀”(即蜀郡、广汉、犍为三郡的合称)迁来的。其中龙氏居于今贵州平坝、清镇一带,傅氏居于今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尹氏居于今黔南的都匀、独山、荔波等地,董氏则居于今黔西南的兴仁、兴义一带。而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暹,在两汉之交时曾为牂牁郡功曹。这些大姓不但在经济上拥有雄厚实力,在政治上也享有权势,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
东汉王朝将西南地区的居民分为汉户、夷户,分别进行管理。汉户指西汉以来迁入的汉族;夷户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一方面,地方官吏利用汉、夷上层共同对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汉、夷大姓之间又常常通过联姻结成“遑耶”(指亲家),与中央王朝派来的地方官吏争夺权力。在仡佬族先民地区以谢氏的发展最为突出。汉魏六朝以来,谢氏历任牂牁太守,控制仡佬族先民地区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直到隋唐时期,还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汉魏六朝时期是全国政局动荡、混战不休的分裂割据时期,因此仡佬族先民所在地区的政治归属时南时北变动不已。然而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看,西南地区受战乱的破坏并不大,反而进一步吸收了外来传入的先进技术,使仡佬族先民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在农业生产中,铁器和牛耕得到广泛普及,并有了初步的水利灌溉设施。手工业方面,青铜的铸造和制陶技艺突出,技术更加熟练,造型更为精美。
四、唐宋时期的羁縻统治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各地内附或已征服的少数民族,根据其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设置经制州或者羁縻州县,实行两种方式并行的管理办法。在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设置经制州,由吏部正式派官治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则设立羁縻州县,由带有军事性质的邻近都督府指派当地土着首领为刺史、县令,代替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当地各族人民。这种官吏名义上出自王朝封授,但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力,并且由子孙世袭,他们对中央王朝只有朝贡和出兵助战的义务。羁縻州县的设立客观上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全面交往,促进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发展。
随着社会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仡佬族已由“僚”人中的一部分发展为单一的民族。隋朝时的《武陵记》中便正式出现了“仡僚”(即仡佬)的称谓。
两宋时期,中央王朝统治者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与北方诸少数民族的抗争之中,无暇顾及包括仡佬族在内的西南各族地区,仍然保持了唐朝后期以来的羁縻统治局面。在仡佬族分布地区,先后设立若干羁縻州,由于当时统治者把少数民族都看做是尚未开化的民族,因此又称为“化外州”。所辖居民仍不为“编户齐民”,不征收赋税,仡佬族按期向朝廷进贡朱砂、水银、马匹、葛布等地方土特产。朝廷则以金银、袍戴等赏赐地方首领,以此维持着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关系。
这一时期,大部分仡佬族已直接受治于中央王朝,但仍有部分仡佬族中的封建势力割据一方。他们在政治上是世袭的土官,在经济上是封建领主,享有种种特权,将辖境内全部土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强迫广大仡佬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充当田丁。田丁平时要为封建领主耕田种地,服各种无偿的劳役,战时还须无条件地为土官作战。不但要承受各种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对封建领主还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