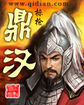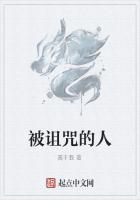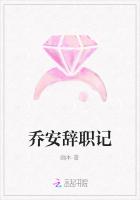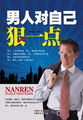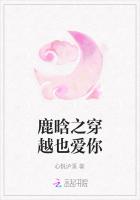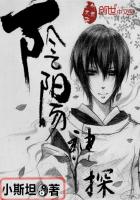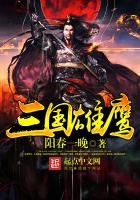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仡佬族婚姻具有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当时的“东谢蛮”“西谢蛮”“南谢蛮”和“西赵蛮”都是指仡佬族,其首领谢氏高居统治地位,自视血统高贵,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然而统治者毕竟是少数,即使找不到门当户对的人家,也不愿将女儿下嫁普通人户,于是统治者曾一度采取控制养育女孩的措施,以维护其等级的尊严。这一时期,无论处于上层还是底层的仡佬族男女青年,都没有恋爱婚姻自由,他们的青春和命运,完全被等级和财富两条铁链牢牢锁住。
明清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历及民族关系的影响下,仡佬族内部各支系明显形成。不同支系之间联系极少,习俗有别,并且互不通婚。许多地区仡佬族男女婚配只在同一支系内不同宗族之间进行,联姻范围只在十里至数十里之间,婚姻关系几乎都在亲戚之间相互展开,形成“亲上加亲”的婚姻体制。其中最为普遍的便是姑舅表婚制,其中不同地区又有不同的取向,如安顺、平坝、贞丰等地严格实行“姑之女定为舅媳”,如果亲舅家无子,须嫁堂舅之子,否则这位姑娘便终身不得嫁,他人亦不得娶;而普定、关岭、六枝、金沙等地则相反,即“舅之女当为姑之媳”,姑之女绝不能嫁归舅家为媳,否则会遭人耻笑;而大方一带的仡佬族则姑表婚、舅表婚并存,还有一些地区姑舅表婚和姨表婚并存。
从总体上说,仡佬族男女的婚姻属于封建性的包办婚姻,男女双方不能自己做主,亦无权选择,在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前提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男女青年在婚前有恋爱的自由,可以在各种社交场合中认识、了解,并建立爱情关系,然后再求得父母的允许,请媒人出面促成婚姻,这一类婚姻总体上看是比较人性化的;还有一种是连婚前的恋爱权利也被剥夺,许多青年在结婚以前连自己的配偶长什么模样、性格如何都完全不知,他们甚至不能与同宗以外的其他同龄异性见面来往,完全被封建礼教所束缚。
一、传统婚俗
(一)恋爱
南宋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对仡佬族的婚姻有一定的描述,这一时期,仡佬族是崇尚恋爱自由的。明清时期的一些地方志中也记载有仡佬族男女青年在节日聚会或者喜庆的重大场合“相会于野”,私订终身的情况。《遵义县志》中记载:“清代以前,仡佬族每年春节,男女玩山,在耍房中情歌互答,自由恋爱,情投意合,互相‘丢准成’后,男方便可委托媒人说亲。”说明仡佬族在恋爱婚姻习俗上是比较自由开放的。
所谓“耍房”,是一个为仡佬族青年男女聚会而搭建的草棚子,通常建在离村寨不远的山上,或半封闭,或不封闭,能够遮风挡雨。每逢春节或者农闲时候,村中的青年男女常常三五成群,相约到耍房对歌玩耍,无论是否认识,都能在对歌过程中玩得十分尽兴愉快。大家你一首我一首,你唱我和,你问我答,人多时,会男女分开在相隔不远的两个耍房互相对答。有时,远村的青年也会在熟人的引带下来耍房对歌。在贵州西部的一些地区,仡佬族青年也在“石峒”中互表衷情。
在遵义一带,唱山歌一般都要小伙子带头唱:
好久没有唱山歌,喉咙长起蜘蛛窝。
跟妹借把铁扫帚,扫扫喉咙唱山歌。
姑娘回唱道:
好久没有唱歌来,哥的喉咙长青苔。
妹把扫帚借给你,哥把山歌唱起来。
小伙子再唱:
唱首山歌给妹听,看妹知音不知音。
点灯要点双灯草,唱歌还要妹连声。
姑娘对唱:
哥唱山歌妹来还,四句歌儿不算难。
哥唱天上七姊妹,妹唱地上九连环。
此句之意是你放心,我完全可以和你对下去。
小伙子继续唱:
叫我唱歌我就来,披起衣裳穿起鞋。
随身带着几百首,后头还有马驮来。
姑娘也不甘示弱:
你歌没有我歌多,我的山歌用马驮。
前头到了大定府,后头还在乌江河。
男女双方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有些比歌打擂台的挑战意味。这些山歌大多数是现成的,这些男女青年从小跟着长辈、哥哥、姐姐学来的,记忆力好的仡佬族青年男女歌手可以一口气唱几十甚至几百首山歌,所唱的内容大都是朴实的日常生活生产,信手拈来,有时候歌手也会临场发挥,创作新歌。当然,还会唱出自己的择侣条件或者打听对方的人品情况,以寻找意中人。
小伙子唱:
这山没有那山高,那边山上我的娇。
我的娇来我认得,盘子脸来弯眉毛。
姑娘对唱:
这山没有那山长,那边山上我的郎。
我的郎来我认识,大眼睛来高鼻梁。
小伙子继续唱:
鸡嘴没有鸭嘴圆,不说苦来不说甜。
只要哥哥仁义在,仁义在来水都甜。
这时,通常会有第三人出来撮合:
郎也乖来妹也乖,郎提簸箕妹提筛。
郎提簸箕簸出去,妹提筛子团拢来。
因此,耍房对歌实际上也是仡佬族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主要方式,通过一次或者几次耍房活动,彼此唱歌、对话,了解对方情况,如果双方情投意合,会“丢准成”(或叫“丢把凭”),就是互赠信物,立下誓言。接下来,便由小伙子托媒人向姑娘提亲。
赶场也是青年男女结交的好机会,通常在赶场的场坝或者来回的途中,男女青年会以对歌来互相结识或加深感情。
通常也是小伙子主动开口搭腔:
来到场坝赶场玩,撞见阿妹在路边。
唱首歌来问阿妹,但愿成双不成单。
姑娘若是有意,便含蓄地唱:
油菜开花黄又黄,蜜蜂采花忙又忙。
土边一株花油菜,只等蜂儿采来尝。
小伙子再表情意:
出门得见映山红,花多叶茂开得浓。
哥想伸手摘一朵,不知妹心同不同。
然后双方会对歌互相试探:
姑娘唱道:
一朵鲜花鲜又鲜,单单生在悬岩边。
花鲜本是为哥采,不怕岩垮就攀岩。
小伙子唱:
豌豆开花明对明,蚕豆开花像灯笼。
心想搭腔称情妹,妹家华贵哥家穷。
(二)提亲
小伙子和姑娘在耍房对歌的过程中相爱了,但是要走进婚姻的殿堂,彼此组合成为一个家庭,还得遵循一套固定的程序仪式。有些地区的仡佬族婚姻也由父母包办,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三媒六证,更要严格按照固定的婚礼仪式来进行。首先,小伙子要请媒人到姑娘家提亲,也称讨口风、取同意,仡佬语叫“补海”。媒人大多是亲戚或者熟悉、信得过的人。有时,也有好心的媒人看到某两家男女青年般配,主动为男女双方提亲做媒。这种婚俗如今仍然广泛流行于仡佬族村寨当中。提亲后,男女两家同宗三代,经过“远亲访一访,近亲想一想”,认为门当户对,便放话同意,也叫“取同意”。
在一些地区,“取同意”这一过程十分有趣,如安顺一带,媒人带着礼品来到姑娘家中“取同意”,姑娘家人会做饭做菜招待媒人吃饭,还会邀请家中有威望者或者寨老陪同,媒人可以从所上的菜会意姑娘家是否同意这门亲事。如果同意,就会把媒人带去的公鸡杀掉做来吃,如果不同意,则杀自己家的母鸡。如果姑娘家把自己家的母鸡端上桌,媒人心中已经明白了几分,这也是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媒人得想办法让姑娘家的人多喝酒。酒过三巡,找机会把鸡头夹给姑娘的父亲,这时正值酒酣耳热,他会不小心把鸡头吃掉,这一来,媒人就会咬定女方家长同意了亲事。因为鸡头吃掉以后,是公鸡还是母鸡就说不清楚了,即使拿出媒人抱来的公鸡也无济于事,他会说“公鸡家家有,天下公鸡都一样”,请来的寨老和陪客也只得按吃了鸡头为准来撮合这门亲事。但是通常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仡佬族提亲前,两家人都会提前有所了解,才会请媒人上门说亲,媒人通常都会受到尊重和热情接待。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仡佬族,“取同意”的过程进行得比较含蓄,小伙子将礼品送到姑娘家后,姑娘家如果同意,便会接受,如果不同意则拒绝收礼,并礼貌地婉言谢绝。在礼节比较隆重的仡佬族人家,提亲会进行两三次,第一、二次提亲时,姑娘家长都不作明确的答复,还要经过第三次提亲,这一次,姑娘家才向媒人明确表示答应了这桩婚事,并立即设宴款待媒人。通常姑娘家接受以后也会回赠一些礼物,通常是一双布鞋或者袜垫,但是很少当面送出,而是悄悄放入小伙子的口袋中。这样,姑娘算是“放了人户”,小伙子也算是“定了亲家”。
(三)定亲
婚姻大事不仅仅是男女小青年自己的事情,往往也关系到两个家族之间的结合,因此绝不能草率。提亲之后,两家人还要经过一段时期的相互来往加深对彼此的了解,直到双方都满意,婚事才能定下来。
两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和情感磨合后,小伙子家要选好日子,备上厚礼,通常是衣料、酒、面、禽蛋、粮食果品等物,请媒人带到姑娘家,称为“交小礼”。姑娘会回赠自己亲手锥缝的鞋袜,以不失礼节,并且可以展示姑娘精良的针线活。然后是“装香”,小伙子备好八色或十色布料、荤素人情、糖果糕点及香烛火炮、袱纸等,盛入12个茶盘,在媒人带领下前往姑娘家,将礼品摆在堂屋神龛前,点上一对红烛,姑娘的父母也坐在神龛前,小伙子要面向香烛向姑娘的祖先和父母行跪拜礼。“装香”仪式虽不大摆筵席,但周围的亲朋好友也会前来祝贺、捧场,“装香”后,这桩婚事才算是正式确定了下来,不得随意更改。
(四)烧香与开庚
婚事确定下来以后,两家人来往就更加频繁,也都要开始为婚事做准备了。首先,小伙子要备好聘书以及鞭炮、香烛、肉蛋、酒糖、衣料、手镯、戒指、耳环、项链等彩礼,分成若干竹筐,请人挑到姑娘家“烧香”,也称“纳聘”或“插香”。双方家庭对这一礼仪都十分看重。在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把嫁女儿的人家常常称为“输家”,俗话说:“输家输到底,贵的不过是两回烧香礼”,意思是姑娘家在场面上的光彩与人格的尊贵,必得通过厚重的礼品才有望展示出来。在举行此项礼节之前,双方家庭总是要通过媒人进行辗转反复的谈判,彩礼究竟应有多少。若双方达不成共识,则难免产生不愉快,影响这桩婚事。通常对于男方家庭来说这是添人进口的喜事,自然会表现出应有的爽快和大方。“烧香”之日,姑娘家的亲戚朋友也会前来道贺,姑娘家人会把小伙子送来的食物分给众亲,称“烧香人亲”。
“烧香”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男女双方要出具庚书选定婚期,称“开庚”。庚者,生辰也,这是择定合婚吉日的重要依据,亦叫“开年庚”。小伙子先将生辰写在大红纸上,随着“烧香”的礼品一同送到姑娘家开年庚。姑娘家也要将女儿的生辰(坤命)写入庚书,称“发庚”。两庚齐备,便请八字先生根据男女双方的年庚生月,推算“八字”,选定迎娶的吉日,写入庚帖。另具“报期书”,由媒人递交女方家,女方家开回三亲六戚的“书单”、姓名和轿夫人数。男女双方便按上述事项筹办婚事。
“烧香”仪式结束后,姻亲关系就更加牢固,就是俗话说的“三炷香,两棒磐,敲了就当铁水凝”。
(五)接亲
仡佬族称结婚为“配刁”。结婚在人们看来是一生只有一次的头等大事,所以迎娶的礼仪显得尤为重要,男女双方家庭往往要用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来筹备,家中的一切事务都围着这一件大事来安排。比如,种植多少花生、葵花、芝麻和苏麻,喂几头猪、几只羊,腌几坛酸菜,泡几坛酒,晒多少洋芋片,熬几锅包谷糖,请哪些亲戚朋友,办多少桌酒席,都要一一纳入考虑范围。男方家还要考虑修整房屋,面请轿夫、唢呐匠、押礼先生等。女方家则考虑置办衣柜、桌椅板凳、锅碗瓢盏、铺笼帐被等。
姑娘在婚前一两个月便放下农活,在家中缝衣制鞋赶嫁妆,并把之前姊妹间秘密传抄的哭嫁歌本拿出来温习和研究。
仡佬族婚礼,普遍是“男不迎亲”,即新郎不去迎亲,而是请媒人和至亲前往迎娶。婚期吉日这一天,男方家中备上厚礼、轿子和迎亲彩旗、唢呐、锣鼓等,由媒人和押礼、书班领队,一路吹吹打打前往姑娘家中迎亲。接亲人员一般有六人,中年男女各一人,青年男女各两人,据说是祖先流传下来的规矩。一人提礼,两人打灯笼,三人抬物品,到了以后,先由书班和媒人依次点交礼物,称为“过礼”,姑娘家向男方交点嫁妆。新娘离家之前,要哭嫁,表达离开娘家和父母的不舍之情。哭罢,新娘便要离开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家,去开创另一段新生活了。她穿过门前的红布毯,踩过燃有7根灯草桐油灯的筛子,寓意姑娘心灵手巧,筛子摆有12个或24个铜钱,代表每年12个月大吉大利,这叫做行“开光仪式”。仪式完后,新娘从媒人或至亲手中接过一丈二尺红布,拴在轮子内部(以固定轿子,防颠簸),再戴上铜镜以避邪,由人牵扶着走进轿子。新娘家中要组织男女青年组成专门的送亲队伍,一般8~12人。男的护轿,保护姑娘,女的随轿,热热闹闹。送亲客护送新娘一直到新郎家中,会受到新郎家的盛情款待,然后带上男方家准备好的回亲礼品返回。
新娘到了婆婆家后,由人牵着下轿走进堂屋。堂屋中装扮得喜气洋洋,香龛红红朗朗,烧纸点烛,新郎新娘一起向祖先、父母行跪拜之礼,父母拿出红包给这对新人,封赠婚姻美满,大吉大利。接着,家中其他的长辈也都到堂前受礼,并送上红包以及祝福的话。“礼”过之后,便把新娘牵进新房,新郎家的弟妹们也前来道贺,给过门的嫂嫂打洗手水,新娘也会发给他们红包,称为“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