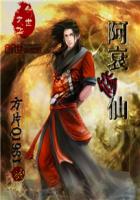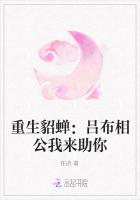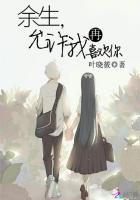现在我已近不惑之龄。生活中许多华丽的东西无缘可求,我的青春在飞流的时光中正悄然逝去。从前我那白杨般挺拔健壮的身姿如今萎缩成弯曲变形的枯柳;从前飞奔于足球场,惯于早起晨练的阳光青年,如今菊花一样绽放的笑纹里蕴藏着对苦难命运的抗争。我头戴回族白帽,心怀感恩,为母亲和所有善良的好心人捧接一个长长的都哇尔(捧起双手向主祈祷)。阿米纳(允许吧)!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笛音
春天的村庄像被春风催开的柳芽,又像小麻雀的黄嘴角,嫩黄的色泽挟裹在暖风里绿成地毯似的麦浪。大地潮湿得如同受屈的孩子哭肿了眼,软遢遢的,有踩上母亲肚腹的亲切感。老柳树上的喜鹊被摇晃惊吓飞出巢窝,喳喳喳地喊叫之际忙向爬树的屁孩拉下一泡稀屎,算是恐吓警告,为了她的鹊蛋能安然无损,她飞到不远处扇翅叫骂,做着扑飞的战斗准备。好在孩子们只折下几根柳条便急切地溜下了树干。
那些直圆的柳条踩在脚下反复搓揉,抽骨蜕皮后,再用小刀切好空心皮口,用力一吹,呜哩哇啦地响起来,粗细不同,音色各异的柳笛就做成了。这种柳笛齐发共鸣的壮观须在驴背牛脊水草边才有趣。牲畜们甩尾擞毛弹蹄驱赶着蚊蝇,从爽口的草香咀嚼声里抬起头,张望间被那笛声迷醉得春心萌动。叫驴们(公驴)哇嗷哇嗷地撒蹄直奔草驴(母驴)身边,一副交颈搔耳状,胯下直挺着一杆枪,跃跃欲试;牛哞声也是声声震耳,青草的气息招惹着一股欲望的爱意。这个孕育生命的春天啊!让孩子们厚裹了一冬的棉衣脱得单薄,我们这些孩子们还不懂得,其实笛音就是春天的爱情曲。
孩子们都一起拥向了张二爷,那团红胶泥在他手里反复搓揉着,比面团还有韧性。他的粗糙手掌纹路里嵌进了红泥,指甲缝里和指头裂纹里全是胶泥的红色。只需一会儿,先前没形没态的一团软泥竟有了“哇呜”(一种流传乡间的土制乐器,学名为“埙”)的雏形。可以捏成小鸟状,可以塑成水壶形,旁凿吹口,气孔通连,上口有眼孔,滴几滴香油润孔,阴干后,紫红光亮,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托掌把玩,深得孩子们的喜爱。孩儿们也就“二爷给我捏一个”地央求个不停。张二爷笑眯了眼,抬起鞋帮磕了烟锅的烟灰,别进裤腰带,应承着动起手来。
村庄的哇呜声此起彼伏,夹杂着鸟鸣,掺混于鸡鸣狗吠声中。劳累的大人们,被吵闹得忽地起身坐在炕头,臭骂一句:“吹你妈的丧调!滚远点!吵得老子不得安生!”急过头了,跑出屋子,抬腿脱了鞋子,朝一堆孩子扔将过去,再吼一声:“滚远点耍去!”孩儿们惊鸟展翅地飞开了,又到不远处,恶作剧地呜哩哇啦比先前吹得更响。“日”的一声,一块土坷垃飞砸过来,又是一阵惊叫。这就没了吹哇呜的兴趣,变为小渠边洗澡,打中美之战了。孩子追逐嬉闹的声音覆盖在夏日的绿树浓阴中,还有蛙声的重叠,孩子就是一只只活脱脱行走的人蛙。
真正意义上的笛音是我最早从三叔那里听到的。三叔的竹笛对我是个神秘有趣的诱惑。竹管中通,椭圆的笛孔,三叔抬臂横笛,撮起嘴唇,芦苇薄膜粘贴住第二个孔口,手指弹跳间有序地吹出高低音符。奶奶家老房子后面有一棵歪脖子老柳,像是卧爬房上顺势而长的梯子,三叔坐于树杈中如卧躺椅,柳叶婆娑,那笛音便加了一层露水的湿边儿,变得润滑嘹亮。加上民歌的音调,在寂静的村庄里穿透饥饿无聊的耳朵,抚慰了姑娘小伙好奇的目光。那是三叔从青海参军回家探亲时的一段精彩表演。我那时五岁大点,嚷着向三叔要笛子,笛子递给我,我不会吹,摸几下,又让三叔吹给我听。笛子是三叔从部队里学的,那时三叔去兰州医院,巧遇上山下乡的女知青——我现在的三婶,真是所谓的千里姻缘笛音牵,笛声成了相爱的语言。兰州大城市的漂亮三婶,等着宁夏川区的三叔从部队复员后,在兰州分配了工作,结婚成家了。
三叔的笛音隐含了对三婶的恋爱,思念的笛音在村庄的歪脖子老柳树上婉转悠扬,我幼小的心灵仿佛飞进了一只欢快的百灵鸟。
三叔在宁夏老家结婚后又返回兰州。我随奶奶走了有生以来最远的一趟火车路程。我通过转瞬即逝的车窗观望外面的风景,民房、黄河、远山、绿洲、戈壁、荒漠……远山起伏连绵。到了兰州城,高大的楼房夹杂着拐弯抹角的巷道、民房、四合院。宽阔的马路上车流人涌,商店林立,还有满眼新鲜的公园的花和树……目不暇接的城市风光,使我的眼眸里好奇百生。这是一九七四年的兰州城。
这也是我第一次走出村庄,第一次坐火车走进大城市,第一次看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与繁华(尽管兰州还不是西部之最,尽管我还幼小不谙世事)。奶奶抚摸着我黑亮的头发说,娃呀,你要好好念书,将来也像你三爸一样当个城里人。
一九八五年七月,高一暑假,我到父亲所在的内蒙古左旗一个牧区建筑工地上打短工。那里的天气早晚温差大,风吹沙子跑,牛羊满山腰。建筑工程队要在一个叫宗别立的乡建一座电影院和农机监理站,那里四面环山,有个自然湖泊,水清草茂,是灌溉汲水的天然水库,顺山势而流汇的雨水成为湖泊的水源补给。当地的脊字型房屋依山坡而建,每家相距不远,皆为青砖瓦房,坐落于湖岸坡地。各家敞院里,有牛羊圈舍围栏,畜禽朝夕叫声不绝于耳。
那是个月圆之夜,我走出工棚独自散步,晚风送着胡麻和苜蓿的花香,倍感神清气爽。我见过家乡平原的月色,在山塬上观月,还是平生头一次。踏着湖光月色,人像泊在水银上。月儿满如银盘,亮灿灿的,伸手如触白幕。忽而前边传来笛声,悠扬的《春江花月夜》让人顿觉沉醉于江南水乡美景里。走一段陡坡,月光更显清新。那边草地上,席地坐着一位白衣少女,笛音随月光洒满山坡,那是一幅蒙眬的画卷。月圆笛润,碧草幽香。为了不惊扰画中人,我特意放轻脚步,又驻足远听,不敢惊醒她的痴迷。月色佳人,笛音弄香。不知何时,阿妈来寻唤女儿,再三催促劝拉下,她才下山回家。
后来我得知,那是位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疯姑娘,几年前,她在大学里和一位音乐学院的蒙古小伙相恋,两年后,小伙另择女友甩了她,因她太痴情迷恋,脑子受了巨大的刺激而痴疯。我看见她犯病时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笛不离手,误认为我是她的情哥哥萨尔乐,直追我过来,口中喊着,萨尔乐,你怎么不理我?我给你吹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听着她不断重复的疯言疯语,尽力躲避她的纠缠。她嬉笑着,吹奏着,追逐着,我在一群人眼里倍感羞涩地躲闪……直到现在,我的脑海还依稀闪现那疯姑娘一抹痴狂的笑容,不知她病况如何?
内蒙一行,回来后,我就买了支笛子,拜师学笛了。从此,小屋里,溪水边,树林中,沙枣树下,表演晚会上,月色屋檐下,一笛在手,笛音绕梁,如影随从。苦乐年华,流水青春,尽在鸣笛中。
然而,世事难料,我不幸意外伤残。笛挂墙壁,空对寂寥,蒙尘难鸣,笛缘难续。手残不能抚笛,心浮不能吹音。只好作罢,望笛兴叹。每闻笛音,定要静听欣赏。
花竹篮儿
我四岁出麻疹,高烧昏迷了一个星期。半年后,体质依然虚弱,一副病怏怏的样子。
六月初,麦田绿波荡漾,正是蚕豆开花的季节。小妹月红三岁,眼眸黑亮,头发油黑,口齿伶俐,白里透红的脸蛋上分布着一对小酒窝。月红踮着脚尖跑,我总追不上她。遇见小伙伴和我打架,她拾起地上的土坷垃扔过去,连推带搡地说不许打我哥哥!我家新庄的房屋离奶奶隔着稻田,要五六百米的路,其中夹杂着水渠、水沟和小木桥。沿着田埂的一条土路寂静得只有夏季的虫鸣蛙声,胆小的孩子不敢独自走路,冷不丁会碰上狐狸、野鸡、野鸭、野獾等野物出没。家家没有院墙,环绕的树木是唯一的屏障。
夜半人静时,常有鸡鸭被野物偷吃。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拿大灰狼吓人,听见屋外风刮树叶沙沙响,也吓得蒙住头脸。
那时妈妈上工总是手拿肩扛着干活的农具,送我和妹妹到奶奶家去。我走路总是牵着妈妈的衣襟,腿软得走不了几步路就赖着让妈妈背,小妹月红很懂事,从不和我这个哥哥争。妈妈下工接我们回家,小妹说,妈妈,哥哥腿软走不动路,你背哥哥走。说着,她脚尖点地,一溜风儿似的跑在前面,黑亮的头发忽闪着,宛如草地上一只奔跳的小鹿。妈妈每次烙好锅饼用刀切好放在盘子里,小妹挑最大块的给我这个争嘴的哥哥吃,又急忙拿一块递到妈妈手里说,妈妈,你也吃。
爸爸下班回来给我们买了一个黄绿套色的小竹篮,我和妹妹爱不释手,睡觉都放在枕边。醒了,就用它装些打碎的瓷碗片,摘些野花、小树叶、蚕豆花儿等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过家家。这个小竹篮是多么稀罕啊!只有远在工厂上班的爸爸才能从很远的镇商店里买回这么漂亮的小花篮。其他孩子的父母都在生产队里劳动,出不了远门,根本买不到这样的东西。小孩子总有炫耀的心理与天性,所以我们只把小竹篮让那些好朋友玩,和我们不友好的就不让他们碰一下。
记得那次玩泥巴,我不小心将小竹篮用泥手摸脏了。小妹月红说:“哎呀哥哥,看你把花篮篮糊脏了呀!我到渠边洗干净。”还没等我说啥,小妹就提起竹篮一路小跑消失在蚕豆花丛中。
我只顾和伙伴们玩泥巴,猛然想起小妹已经去了好一会儿还没有回来。我对伙伴说,不玩了,我要找我妹妹去。我甩着两手未干的泥巴,沿着那条小路边走边喊小妹月红的名字。
在那座小桥涵洞口的一汪水湾里,小妹面水而浮,像睡在水波的缎面上,花衬衣和花格裤子泡在水中,手里还紧紧握着花竹篮不放。我当时吓坏了,拉了一把小妹没拉动,就哭着向奶奶家跑。正好爸爸也下班了,正在奶奶屋里说话。我说,奶奶,妹妹掉……掉到水渠哩!爸爸听见后和奶奶拔腿就跑。爸爸抱起水中的小妹时,她口眼紧闭着不省人事。爸爸把妹妹放在地上,奶奶哭喊着孙女月红的名字,很多人围了上来。爸爸按了两下小妹的胸口,没吐水,也没了心跳呼吸。正好有人赶着黄牛经过,那人说,快把娃娃放到牛背上驮着让吐水!小妹驮在牛背上也没吐一口水,眼睛再没有睁开看看我。母亲闻讯从远处的稻田里跑来,抱着心爱的女儿哭得死去活来,女儿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看看妈妈。乡亲们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说,唉,这娃人爱真主爱,没一点挽救呀。小妹的生命,犹如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在我以后的睡梦里,常出现一大片田野里开放着各色艳丽的花朵,我和小妹摘了满满一篮花儿,身边有无数蝴蝶翩翩起舞……这是一幅奇特的画,在我的梦境里忽隐忽现。花竹篮儿,连同那个久远的故事,早已逝水东流。我聪明懂事的小妹,如果能活到现在,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