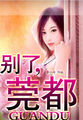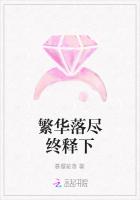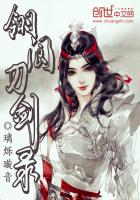别看我们是山村里的人,但我和于强都有共同的业余爱好。在学校里,我们都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于强喜欢唱歌,我喜欢跳舞,我们那个体育老师不但舞跳得好,人也长得帅,他是我的偶像,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还曾经对他产生过另一层意思。我们是在县中学读的高中,勉强读到毕业,不要说考不上大学,就是考上了,也上不起。
回乡几年,这是我和于强第二次出来打工了。
我们做过很多行当,于强做过小工,做过瓦匠,也给人刮过腻子,擦洗抽油烟机,我做过保洁员,也做过饭馆服务员,不是他们故意不给你发工资,是他们实在发不出来,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有关门散伙的,也每天都有开张大吉的,所以我们无论哪样都做不长久。今年,我们不打算给别人干了,想自己做点小生意。我们置了两个锅,铁的炸油条用,铝的煮馄饨,又买了一个微型打浆机,用来制作豆浆,好在这花不了多少钱,加起来不过二百元。炸油条,包馄饨并不难,我和于强以前每天早晨吃,看也看会了。我们就这样出了早点摊儿。
我们的生意一般,除了房租剩不下几个钱,因为在这条街上有四、五个早点摊儿,大同小异。如果说不同,也有不同,那就是我们用的是从超市上买来的正经八百的色拉油,而别人,据我们所知,用的大都是“口水油”,也就是本地人说的地沟油。比如,在我们出摊两、三天以后就有蹬三轮的来找我们了,三轮车上面装着一个黑糊糊的大汽油桶;拧开大汽油桶的盖子,紫红色的油便倒了出来,每桶四十元,一桶四十斤,才合一元钱一斤。另外还捎带有三、两只方形的黄色薄铁通,如果你没有,三元钱便卖你一个。如果你用好油,这四十斤一桶岂不要好几百元?我和于强都拒绝使用。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因为本地人一般是不出来吃早点的,他们都是在家里自己做。他们特别不肯吃馄饨,害怕馄饨里面的馅儿,只有外地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了便行。当然,同行本来就是冤家,我们也不好戳穿那用地沟油的,不便说人家的坏话。
我们清晨四点就起床,把发好面反复地揉,再拌馅儿包馄饨,还有把打好的豆浆用塑料袋封好,因为有许多外地人要急匆匆一手拿油条一手拿豆浆边吃边赶公共汽车。十点钟左右我们收摊,然后必须休息一会儿,下午还要为第二天做准备。
我叫迟雅丽,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以为很“雅丽”,长大了,才知道俗而又俗。
别误会,我和于强还没有结婚,当然也算不上是同居,我们只是住在一间屋子里,中间挂了一块布帐,我睡在里面,于强睡在外面,和锅碗盆勺睡在一起。我们互相约束,彼此恪守着底线,都想把那最隆重、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留在我们结婚以后。当然,亲热的举动平时是难免的。
我们这家房东也是怪,院子里又加盖了一排房子,原本豁豁亮亮的五间上房也出租了,中间打了不少隔断,一共出租了十多家。他们一家三口却挤在一间西屋里。我到过他们屋里,比我们还要脏、乱。但是他们真闲在,一家人什么也不做。他们的女儿十七、八岁了,胳膊和后背都刺着青,个子不高,却留着蓝黄相间的头发,像鸡窝,也像我们山里打回来垛起的秋草。女房东玩牌,男房东腆着大肚囊,整天坐在台阶上忽达忽达搧扇子。
只有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才是我和于强最轻松、最自由的时光。这个村子叫东坞村,村子很大,村子的正中心位置有一块圆形的空地,于强说那大约得有二十多亩,人家都铺了地面砖,四周还种有树木和花草,转圈还有灯。到了晚上,那里聚集了好多好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年龄大的扭秧歌,年纪轻些的跳舞。他们还有一个小乐队,能奏不少曲子。他们跳交谊舞,也有少数在跳迪斯科和街舞。我和于强每每到那里去看,我们站在边上,望着他们,我心理真是羡慕死了。其实,迪斯科和街舞我早就会跳,别看我们是小县城上的中学,但我们那个学校也有衬钱的,他们从外面学了时髦,便迅速传播,我虽然和他们学的,但我跳得却比他们好。我想,我的家乡什么时候也能像这里一样呢?我们的乡亲每到晚上也如本地人那样娱乐、那样跳舞?
有时我和于强也到马路上闲逛,在路灯下映出我们时短时长的影子。我们看着路两边的风景,也不知道八九点钟了为什么马路上还有那么多车,他们都干什么去?或是从哪儿来?似我们这样,并不新奇,人行道上常有一对一对的,但年纪都比我们小,最多也就十八九岁,我敢保证他们都和我们一样是外地人,然而他们就那么公然地在路灯下拥抱、亲吻,像蛇一样拧在一起。也有个别的一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抵着头专心一意地摆弄着手机,那肯定是新买的手机,在练习发短信。
我们走着,忽然我对于强说:“揹揹。”
“你都多大了,还揹揹?还学人家。”于强说。
“不嘛,就让你揹。你还没揹过我呢。”我撒娇地说,于是蹿上了于强的背。于强身体真壮,而且一米七八的个头,把我揹起来毫不费力;如果我不叫停,他肯定要揹出三四里地。
“我该背你了。”我说。
“算了吧。我一百四十多斤,你没迈步恐怕就把你压躺下。”于强说。
但我还是背了他一段儿。
我们没有电视,又不甘心憋在那间小屋里,有时去看跳舞,有时就在这路边,度过一个又一个晚上。
然而,三个月之后,我和于强吵架了,起因是他要回家。头年的这个时候他就坚持回去,我依从了他。
我说:“要回去你一个人回去,这次绝对不再跟你回去!”
于强说:“雅丽,听我的,还是得回去。好歹也算是我们老家的一个收获季节,你说,除此之外家里一年四季哪儿挣个活钱儿?”
我喊道:“我受够了!”
于强说:“够什么够?不就是半月二十天的吗?收完了杏,咱们再回来。”
我说:“你就是把满山的野杏全掳光,能卖几个钱?来回够路费吗?”
于强说:“你不能光考虑咱们俩,你家里需要你,我家里也需要我……”
我打断他说:“麻烦你,两家的事你就全代劳吧!”
于强直愣愣地看着我,他是老实人,即使急了,也说不出特别的话。然后他想了想说:“那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
我说:“照样炸油条,卖豆浆!”
于强说“得了吧,你发不好面。再说,一天几十斤面,你怎么合得动?怎么受得了那么大的累?”
我不吱声了。的确,发面需要技术,也的确是个力气活儿。但是我说:“那我就坐在屋子里等,什么也不干,等你回来!”
那一天我们谁也没有和谁说话。等第二天把剩下的东西卖光以后,于强缓和了口气,说:“那好吧,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屋里等,别到处去。我很快就回来。”
我把于强送到车站,这时候,我的鼻子发酸了。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俩从来没有分开过,一同走过崎岖的山路,一同走过石子河滩,上小学也要走十多里,上中学还要乘去县里的长途车;即使回到村里,也是今日不见、明日见,现在猛然要分别几十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强抱了我,抱了很长时间,我不松开手,但公共汽车来了,他还是上了车。
我在路边的地摊上买了一本闲书回来看。我真的什么也不做,只把自己闷在小屋里,但那本书我只看了一天就看不下去,小屋里闷热,没有电扇,孤独而且烦躁。我想,即使半月、二十天,自己还是应该找点活儿干,否则怎么熬得过去!
我锁上门,走出去。这条街上忽然少了一个早点摊,人们有些奇怪,房东问我,我说于强家里有事,临时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