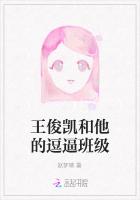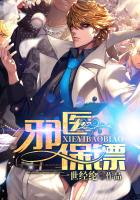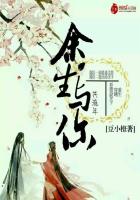玩的就是雾里看花——《大玩家》
都说雅好古玩忒能烧钱,真的“雅好”起来可要做足功课。刚好一本新鲜出炉的《大玩家》,号称是“国内唯一可以代言中国古玩界的长篇小说”,便洋洋洒洒构架了一个惊险悬疑的鉴宝传奇,门外汉也可一窥玄奥了。
康熙五彩将军罐、乾隆粉彩大瓶、万历五彩大罐……这些瓷器若是官窑真品,便身价数百万甚至千万,若是新货仿品,再手工精湛,也免不了挨一重锤,粉身碎骨。电视上的鉴宝节目是引起肾上腺素激烈分泌的收视招牌,古董街鬼市也永远淘腾着“捡漏”和“打眼”的主题。古玩界,玩的是古意眼力,更是心跳感觉。
暗箱之旅
坊间早有人抖搂出来,《大玩家》这部小说影射了马未都的发家史。马未都在业界和民间都是一块金字招牌。而书里的反派boss黄立德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级鉴宝专家,平日里品茗听戏闲雅清正虚怀若谷,俨然宗师。他同一位能仿制历代官窑重器的高手朱伯勤引为知己,可惜在伯牙子期的惺惺相惜之外,子期黄立德却动了栽培摇钱树的念头,把一批“朱仿”瓷器包装成海外流失名品,留洋获得传承资历再回国拍卖,价钱便一本万利。为此,黄立德不惜做了一个又一个局:稳住消失已久的仿制高手好友,挤掉只拍真品的拍卖行老总,让业内另一大佬给他当烟幕弹……虽然最终得偿所愿赚得盆满钵满,却永远失去了内心的宁静。
随着环环相扣的情节推进,一个个稀世之宝横空出世,搅动乍看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的古玩界。那些国宝在视线里流转,本该各自承载着丰厚的文化信息,却往往便消弭在尔虞我诈中,令人扼腕。
寻父之旅
在对一系列古玩掌眼和打眼的拉锯战中,还穿插着一正一邪两个男人的寻父之旅。
主角郑岩本是市博物馆专家的高徒,安蒂克拍卖行的业务主管,出场时还是个孤儿。自从一件高仿中的高仿“朱仿”搅乱一池春水,离奇命案和错乱情感便接踵而至。郑岩为此深恨朱仿的制作者朱伯勤,希望揭开“朱仿”秘密澄清古玩界。待他顺藤摸瓜按图索骥,却惊悉自己正是朱伯勤的儿子。而他也得到口碑,父亲并非只是传说中的造假高手,而是赤诚一片技高艺精的天才。至此,郑岩心目中的父亲拼图终于完整。也许这个父亲并不完美,却最独步天下。隐身在重重迷雾之后的朱伯勤,其实一直指点着郑岩的术业和人生。
郑岩同事夏海生的父亲倒是一位纯粹的收藏家,却被儿子认为食古不化冥顽不灵守着金山当乞丐。在与郑岩的明争暗斗中,夏海生的欲望越来越膨胀,内心越来越狭隘,对郑岩的忌恨和对物欲的贪婪使他完全丧失了良知。他弃父如敝屣,转而投到黄立德的麾下甘为鹰犬,沆瀣一气,可谓认贼作父。而且,在谋财害命霸占了别人的藏品之后,夏海生要挟黄大师为他出货,倒打一耙,彻底蜕变成“眼红心黑”的不齿败类。
《大玩家》中两个父亲的形象,一个由仁厚而腹黑,一个由狰狞而狷介,一明一暗,相辅相成,自然也提携出大智若愚和心怀叵测的迥异后辈出来。中国太极八卦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哲学,在此也能窥斑知豹。
点醒之旅
识古不穷,迷古必穷。
一本《大玩家》翻下来,便是对古玩一窍不通的“麻瓜”也能对业内行话掌握个七七八八了。而且,有些角色醍醐灌顶的话语,读来真如当头棒喝。
某专家说:古玩吃的就是眼力饭,捡漏是它,打眼也是它,眼力就是一把刀!……在这个江湖里滚,宰人防身都靠它。
某大佬说:古玩的魅力和价值其实就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间。古玩行的买卖,吃的就是眼力饭,就算上当,也只能自认倒霉。随便一件东西,如果大家都没看穿,假的也是真的。除了故宫里的藏品,谁敢保证市场上的古玩都是真的呢?
某野心家说:看货、收货、鉴定、拍卖,有人买,有人卖,就跟击鼓传花一样,在不同的人手里倒来倒去……有时会突然产生幻觉,感觉这纯粹就是一个游戏,所谓的古玩不过就是个道具,无所谓真假,只要大家愿意玩下去,遵守游戏规则,就没有任何问题。这就像炒股,并不是每一只股票都价值相符,可不妨碍人们追捧爆炒!其实古玩跟股票是一码事,买股票不是为了当股东,买古玩也不是想做收藏家!股票无所谓价值,古玩无所谓真假,只不过是游戏的道具而已。重要的是差价,只要有差价就能赚大钱。
……
这大概都是大玩家们的肺腑之言。
所以啊,古玩果然不是什么人都能玩的,有钱有闲有眼力,缺一不可。能在地摊上捡个大漏摇身变为富豪,也可能一夜间灰头土脸身败名裂。当个看客,做个读者,看别人惊心动魄,自己安然无恙,也挺惬意。
如果,《大玩家》更偏重于古玩的品鉴和流派传承,而非圈子里的厚黑权谋和白烂三角恋,就纯粹了。
2009年9月21日
新浪读书用稿
惟有铭记——《1944:松山战役笔记》
于松山战役结束之纪念日,九月七日夜,拜读完余戈兄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
对于这样一部潜心四年拾掇而成的力作,从治史的态度到文风的稳健,我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份。这次是一鼓作气读完《笔记》,且做了重点标记,把深以为然也的句子都摘出来,较之以往的阅读习惯真是大有长进。尽管作者一再谦虚,不过是个“菜团子”,但我想说,这个菜团子太有营养了,对于如今三聚氰胺苏丹红二恶英喂养大的我辈读者来说,是最养人的粮食。啃着这个菜团子,得以逐渐拨开迷雾,看着历史一帧一帧的在眼前定格,最后“别无他想,只有铭记”。读这样的书,是幸福的。
朱增泉中将在序言里,当头便道:不要以为只要穿上军装,都自然成了军事迷。
……穿上军装,并且懂得军事的人,也不一定全都对军事潜心钻研到入迷的程度。
……余戈写的这本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
……面对共同的民族敌人——日本侵略军,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都曾为捍卫自己亲爱的祖国浴血奋战、流血牺牲。
我最喜欢引用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那段话。希腊人对历史也有着一种谦恭的态度,那是阿波罗的历史女神教会他们运用一种澄明的目光。用修昔底德比照司马迁,不敢说孰优孰劣,只能说,在《史记》中徜徉久了,就会渴望平淡的最贴近于真相的探究。有时候,距离越近,反而看不清楚,所以,幸而能够等上“七十年”(余戈语),某些真相不会自己浮出水面,但总该有一些使命感的勇士,敢于校正谬误弥补遗缺。
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争。
在松山战役中,中国远征军阵亡四千名将士。树立在昆明市圆通山的中国远征军第八军松山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时至今日仍只有折断残存的基座,原先的碑身早已不可寻觅。
想起余戈在新书发布会上,脱口而出的一句,“这个国家是没有良心的”,这种出于怨愤的宣泄,其实淋漓地表达了后人对先辈曾经浴血却无以为继曝尸荒野之现状的所有痛心疾首。今人之成熟,是否就该踩在先辈的尸骨上,仰之弥高?
也许,上天是这么安排的:中国种族太庞大,如果文化太优秀,个体太出色,那还让世界上其他民族怎么活?好,就让它毛病多一些,改起来慢一些,交学费多一些(人命和效率)吧。我们的国歌一语成谶:中华民族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上帝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吗?
以上是余戈私下里的一段文字,深以为然。
读《松山战役笔记》,令我心有戚戚和茅塞顿开的语句段落俯拾即是。囿于能力和水平,我的这篇读后感,只能避重就轻地谈谈自己的理解。
《松山战役笔记》中的“超链接十五:第八军松山战役中的指挥者”,余戈兄的结论是“松山战役全程指挥之首功,仍然要归于何绍周,李弥应排在第二位(其率荣一师解救龙陵之功可另算),王景渊、熊绶春两位大概可以并列其后”。
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余戈兄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陆军第八军第一〇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及《陆军第八军一〇三师在滇西整训日记》这样的第一手资料,而得出的。
我也是年中在翻阅资料时,发现网络上和相当多的书面资料对松山的实际指挥者模陵两可。说到军长何绍周时,便说何是甩手掌柜,说到李弥时,便突出李弥的神机妙算。
一个重大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怎么会各执一词?
邓贤的《大国之魂》影响甚广,可谓初次向国人揭开了中国远征军的那段烽火岁月,但所谓纪实文学中,也颇有些妙手乾坤的笔法。一味贬低何绍周作为的军长的实际指挥,而刻意抬高副军长李弥的作用。即使是《军事世界》杂志在今年八月号做“红蓝同学会”专题时,仍然把攻克松山的功绩完全归到李弥名下。可见,“李弥指挥了松山战役”这一说法,《大国之魂》为其滥觞。
方知今的《血战滇缅印》,用了一个半篇幅来写何绍周的指挥之艰辛,初还以为是文学化的描写,但其后见了几篇亲历老兵的回忆文章,对何的表现亦颇肯定,可见何的亲率亲为绝非捕风捉影。当然,我之考校松山战役实际指挥者,并非抹杀李弥身先士卒的先锋精神。可喜,费了一番工夫,结论仍然是确凿的,与余戈兄同。其实,史家及战报也早都是如此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