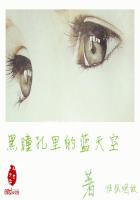郁荩轩依言拿起,揣了一个在裤兜里,用随身带着的威戈牌瑞士军刀起开另一听,刀尖挑了一块,送至章汉骞面前,“师座请。”
章汉骞推开,“给贺幼麟留一个?”
“是。辎重连这两天任务重,小贺直嚷嚷掉秤了。”
章汉骞嗯了一声,终是不耐烦道,“郁营长,你吃。这是命令。”
郁荩轩顺从地吞了。
“师座,您最近清减太过。”
“倭寇未灭,我辈军人若大腹便便脑满肠肥,岂非奇耻大辱。”章汉骞瞄了一眼特务营长,“你倒就剩一把骨头了。”
郁荩轩笑道:“职在蓝迦吃腻了,还是留给师座。”
章汉骞却冷着脸,“我在慕尼黑炮兵学院,连肉都吃腻了。德国人的牛肉汤,光奶油就腻死个人,哼,真不知节省。”
郁荩轩忍着笑意,仔细看桌上的地图,表情越来越严肃。
“有什么要说的?”
“这是史团长修正的?职保留原来的意见。而且,正要向您报告:明日特务营将派两个精锐连重新勘察对岸,职亲自带队。兹事体大,以史团长向来之误打误撞,恐有不察之处。”
章汉骞点头。
“史团长是个鬼才。收编他时,明明是个土匪出身,仗着好勇斗狠,两军对阵却能剑走偏锋,倒是可当一步险棋用。不过当下我们只有老老实实打攻坚战,却也没得滑头可耍。你这个特务营长,往日里也自夸文治武功,越到这刺刀见红的时候,越要学学他人的长处。”
“蜀有武侯,兼具五虎上将,却仍不免败于曹魏。”郁荩轩见师座拿史团长来比自己,一颗心暗暗刺痛,话就回得冲了。“职自知书生气重,却是不敢忘记师座的教导,‘学会用脑子打仗,自然胜过一味蛮勇。’属下如不力,师座尽管撤我的职!”
章汉骞拍拍心腹肩膀,“你跟着我这么久,又何必多虑?”
郁荩轩自知失语,低了头,“是,职言过了。”
“算了。你的特务营都领了防疫的药吗?美国货,想必管用些。”章汉骞问。
“领了!昔日秦军虎狼之师,初入岭南,受瘴气之苦,同南蛮竟也缠斗了三、四年之久。职的特务营自然更不敢怠慢。”郁荩轩说。
“北宋疲软,尚有岳家铁军。而今,国家如此积贫积弱,便是淡了老祖宗的尚武之心。我记得,刚进云南的时候,你还做了一篇《战国策》的心得,颇有锐气。”
“那时学生我还真不知天高地厚。说起来,一战区的孙蔚如将军,也做过一首《满江红》。”郁荩轩想舒缓上峰的郁结,便抑扬顿挫吟诵起来:
“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代鼓。怒皆裂,岛夷小丑,潢池耀武。锦绣江山被蹂践,炎黄胄裔遭荼苦。莫逡巡迈步赴沙场,保疆土。金瓯缺,只手补;新旧恨,从头数。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剿绝天骄申正义,扫除僭逆清妖盅。跻升平,大汉运方隆,时当午。”
“不错!陕军虽然杂牌,倒端的龙精虎猛骁勇善战。蔚如将军为人,能屈能伸,为抗战大业忍辱负重,我亦深为敬佩。”
“职记得,师座您说过,别人笑话我们黔军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我们的队伍从安顺拉出来,就没打算拉回去。”
郁荩轩想开个玩笑,却并未等来章汉骞的回音。
东岸的雨夜些微清凉。空旷的作战室脱去了白天的潮热,但依然沉闷。
见章汉骞只穿了一件月白的制式衬衣研读水文资料和诸方情报,额上还渗出汗,郁荩轩便在旁边脸盆里绞了一条毛巾。那井水打上来搁久了,也变得温热了。郁也只好把温毛巾拿给章汉骞。他还是个学生时跟上章汉骞,就当了章的亲卫,好多繁琐事务都做熟了的。
章汉骞揩一揩脸,并不言谢。
“不回去了,让那些嫡系看看,谁是坐井观天的,谁是只手补天的。”
“正是!”郁荩轩不假思索。他娴熟地把章汉骞看过的资料整理归档。
“有人说,我章汉骞最是狠毒,巧取豪夺。”章汉骞背着手踱步。
“对鬼子狠毒,就是我华胄的良药,就是大忠大勇。”郁荩轩望着那背影。
“不,他们说,我舍不得用学兵团,却让荣兵团当炮灰,有了战绩,我领,败了,荣兵团扛。说我章汉骞,过河拆桥。”章汉骞板着身体,不带一丝起伏。
郁荩轩睁大眼睛,“如此言论,实为大谬!学兵团荣兵团,不都是您的部属吗?职虽不才,军中沽名钓誉、损公肥私、狗苟蝇营之辈,之所作所为,也略知一二。仗总要人来打,您领军在外,劳苦功高,自然有人眼红,风言风语便多了。早就有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职只恨,打鬼子的人也要被编派,这世道还有公理吗?”他凝望着他,“师座,不管这仗打得多辛苦,职是跟定您了。”
章汉骞波澜不惊,昂起头颅,“抗战抗战,拼光我们这一代,豁出去下一代,干掉鬼子所有男人,才算胜利。”
郁荩轩少见的没有直接回应,却把北面半掩的竹窗推开,向外看了一眼,幽幽地说,“原来这楼后边还有虞美人呢,好大一丛。”
“那没什么,罂粟花吧,云贵自来种植很多。名声不大好,可是也能入药。”
“是,职听说,好多百姓,也就种了这个换钱,养家糊口。”
“也叫英雄花的。”章汉骞心情稍稍明朗起来。
“是个狠角色,红艳艳的,像一盏一盏斟满了血的酒杯,好看的噻,不负美人之名啊。”郁荩轩一时出神。
闻弦歌而知雅意。章汉骞心里叹道。有这般如臂使手,便是心底多少寒意都能融化了。
六 修罗
郁荩轩一个人扛着将近十公斤的肩射式火箭筒。刚填饱的肚子似乎转眼间就被掏空了,那火箭筒山一般压下来。他不抱怨。从“九一八”算起,十三年了,我们终于撑到大反攻了!郁荩轩心说,卧薪尝胆,鏊兵十万,不就等待这最后的冲锋吗?
冲锋队队员都在沉默中坚守。郁荩轩看不到预备梯队的贺幼麟,贺幼麟也看不到他,山势陡然,树丛茂密,谁也看不到谁。郁荩轩这个特务营长担任冲锋队长是当仁不让,他也严格照着冲锋敢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苦战恶战,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缺枪少炮的时候都挺过来了,何况现在。
统帅部的新方针是攻击攻击再攻击。身为军人,他会无条件服从。
可是鬼子没有默契。他们像土拨鼠一样安稳,藏在地堡里狠狠还击。几处机枪火力极猛,打得冲锋队这边抬不起头。装填着路易氏气和芥子气的毒气弹也从敌阵地掷放过来,令人作呕的黄烟就在眼前猖獗。
郁荩轩也绝不客气。掩体不成其为掩体,坑道也没有提供更好的保护。他戴上防毒面具,扛着他的巴祖卡火箭筒就冲了上去。巴祖卡似乎分外的沉重。他要把那个不断喷着火舌吞噬了数十个兄弟的火力点给端掉。
“哪个血溅了老子的透视镜!”郁荩轩一把掀起模糊了视线的防毒面具,顾不得没有人帮他校正弹着点,扣动了扳机——
干掉了!
毒气瞬间撕烂他的脸,钻进他的肺部。剧痛让他在心里挣命地呼喊痛骂“狗日的!”
冲锋队成批的冲上山坡,又成批地倒在火舌里,倒在血沃的山脊上。
郁荩轩命大,歪在坑道里,终是被预备梯队的贺幼麟几个寻着,拖下了火线。
医护兵们下破了胆,缩在后方隐蔽部里。贺幼麟只好笨拙又小心翼翼地先用酒精棉给郁荩轩擦拭脸上的灼痕。火辣辣地,郁荩轩并不感到疼。
“郁哥,往后你可要破相了。”贺幼麟说。他凑得那么近,眼泪鼻涕糊了郁荩轩满脸满颈窝。他在怨恨自己的无能和失职,让他郁哥受了这么重的伤。
眼泪真他妈的清凉。
“小贺,哥太冲动了。你可不能死。”郁荩轩说不出话来。他用微弱的眼神表达着。他觉得贺幼麟听到了,也听懂了。战争果然能让所有的男孩子都长大成人。
意识不在大脑里游走。
郁荩轩想起了很多,又全忘记了。他的父母,家乡,大大小小的战斗,美国人开的医院里火辣的护士姐姐,对他吃吃笑着的村妞,倚门而立纯得一汪水的姑娘……她们没出现一秒,一双修罗般充血的长眼睛,坚毅的面孔硬邦邦的身影,便把她们撵得烟消云散。
那是他的长官。他带他们杀鬼子,他们跟着他杀鬼子。他很会杀鬼子,他们誓死追随。
他清楚记得三七年打蕴藻滨的那次恶战。
团长章汉骞问他,“郁荩轩,你老家在宜宾吧?”
“是。宜宾迁到兴义的。自从跟您出了贵州,再没回过老家。”
“你家乡出过一位少年英雄,以寡击众,以弱胜强,保卫一方水土。后遇恩师,追随圣主,出入为帐前先锋,屡建奇功。这且罢了,杀敌无数仍心如赤子,无人能及。……章某甚为钦佩。”
郁荩轩脑颅里飞快地过电影,他拼命搜寻家乡的英雄,搜了半天,觉得竟是自己最符合上峰的描述。他没想到上峰当面夸他。
“你定知这少年是谁。”章汉骞略带着莫测的笑容。
“是职……”郁荩轩想脆生生回答“可是卑职?”
“果真想不起来?不是哪吒吗?”
郁荩轩钻地缝的心都有了。
传说,四川宜宾为哪吒故里,郁荩轩念私塾的时候,父亲还特地带他回宜宾去哪吒庙里祭拜。但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他忘却了太多东西。
郁荩轩抬手摸摸自己微烫的面颊。
“你也不用害臊,你就是我的哪吒嘛,我章某人的帐前先锋。”章汉骞赞道。
帐篷外炮火连天,隔壁床铺的兄弟的残腿要被截掉,正鬼哭狼号。郁荩轩躺在勉强可称之为伤号床的木板上,但他觉得挺满足,即便刚挨了小日本几枪,三天来一直在鬼门关徘徊。
……
“小贺,贺幼麟……”坑道里的郁荩轩臆语着,“别管我,该你们冲锋了……”
硝烟尚未散尽,怒江流域渐渐恢复了温吞暧昧的晴朗。远征军近两万人的性命换来了缅北滇西战场的运输畅通,失地相继收复。
东岸原本忽略了好久的一处温泉胜地,终于派上了用场。
章汉骞皱眉。他以为他没有皱眉。他靠在池水边,舒滑的温泉水仍然没有带来真实感。
郁荩轩闯进水雾中,甫一看到师长,又踌躇不前。他终于蹲下来,抓过毛巾鼓足了勇气给长官擦背,就像以前当亲卫的时候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