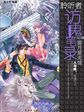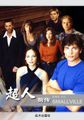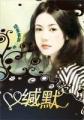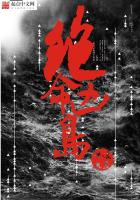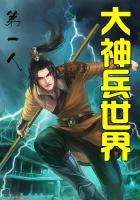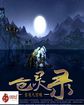自从听到传国玉玺的消息后,谢琰的内心无法平静。从刘秀的东汉开始,到曹魏集团,再到司马氏的晋朝,多少人梦寐以求得到传国玉玺,那可是最高统治权的象征。那时的人很迷信,传国玉玺在手,就可以说自己是天命所归,其作用不亚于百万精兵。
日月依旧,江山轮转。曹氏篡汉,司马氏篡魏,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有野心、有手段、有实力,敢于冒险一搏,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我谢家多代积累,到我这里也该由量变到质变,来个大突破了。再说,没有我谢家出力,在淝水挡住了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司马氏的江山早归别人。司马皇室,虽然给了我一些好处,但在皇族的内心深处,我谢家就是一条看门的狗。我不服啊!
谢琰的谍报人员骑着快马出发,他们的目标是会稽和东阳。几天后,谍报人员回来,说传国玉玺的事千真万确,已由东阳送到会稽,卢循正用传国玉玺做宣传,以图扩充兵力。
这是个机会,我要好好把握,把我谢氏家庭的荣耀推向极致。谢琰向朝廷奏请,说会稽天师军越闹越厉害,应该立即发兵,加以征剿。
皇室听说谢琰要发兵了,高兴得不得了,表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谢琰统领着战斗力最强的北府军,如他消极怠工,司马皇室心里就不安稳。
谢琰第一件事,就是请刘牢之打前站,当先锋。
将令到了刘牢之这里,吃了个软钉子。刘牢之病还没好,起不了床。谢琰的信使看着病床上的刘牢之,吃饭都费力,人参汤顺着嘴边往下流,衣领都打湿了。这哪里是能上阵打仗的样子?
信使回来报告后,谢琰半信半疑。叫他放下身段亲自去湖州请刘牢之出马,好像又有损尊严,自己是谁呀?堂堂的谢家领头人,你刘牢之,只是一个庶族而已,不是我谢家重用你,在淝水之战中给你提供了舞台,你是否成得了将军都难说。想来想去,谢琰决定不管刘牢之,自己领兵出战。百万前秦大军,都被我谢家打得丢盔弃甲,何况这些乌合之众的天师军。
谢琰出发时,给刘裕去了将令,要他加紧打下东阳,与自己合围会稽,如东阳之战不能速胜,就绕道而行,从东南方向会稽靠拢。
刘裕收到将令,表面应付,实则不理。他知道与谢琰会师,就得事事听令,就相当于被收回军权。他不会这么笨,他要看看天下形势再作定夺。
谢琰出发没几天,见刘裕没有按自己的将令执行,就派传令官前去催问原因。刘裕说:“东阳城池坚固,自己多次运用抛石机进攻,均未得手。城内和周边的天师军有三万余人,我只有一万五,兵力悬殊。谢将军要我绕过东阳,从东南到会稽,我也派人探明,东南的磬安一带,有天师军防守,此路行不通。”
刘裕将情况介绍完,又将五十两白银送传令官,请他到谢琰那里美言几句。传令官以为刘裕胆子小,怕谢琰怪罪,被撤职降职,所以才贿赂自己,就心安理得地收了银两,并按刘裕所讲在谢琰那里作了汇报。
谢琰心想,东阳攻不下,绕道不好走,就令刘裕从西原路返回,作为全军的总预备队。
这下刘裕没法说了,他不敢公然反对谢琰,只得下令收拾器具,准备退兵。
退兵路上,刘裕也玩了心眼,磨磨蹭蹭地,一天走不了十里。他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如谢琰得胜而归,顶多批评自己几句;如谢琰打了败仗,战死或被朝廷治罪,自己就甩掉了一个“婆婆娘”。
李流运用传国玉玺作饵,成功调开了刘裕。
卢循气得要吐血
孙恩向卢循行了文书,用非常严肃的口吻让他将玉玺送到海岛。卢循推三阻四,置之不理。他心里盘算着,孙恩的部队约十万人,自己在会稽有六七万人,加上东阳有三万多人,双方实力相当,你孙恩不敢来硬抢吧。
但卢循想错了。
孙恩打听到卢循在会稽大造舆论,说传国玉玺由他保管,乃天师神的旨意。这不是公然造反吗?孙恩坐不住了,决定带兵上岸,夺取玉玺。
卢循大惊,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与孙恩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还有个坏消息传来,谢琰在建康带兵起程,目标估计是会稽。这真是屋陋偏遇连夜雨。还好,传来的不全是坏消息,围东阳的刘裕率兵北归,李流的部队能抽出来了。他给李流下了将令,并附文书,要李流率东阳主力到会稽,与自己合兵抗敌。
到这时,卢循调不动李流了。李流拒绝了卢循,而且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已被天师王孙恩封为征南大将军,与卢循平起平坐,不再是上下级关系了。
卢循看到李流的回文,气得要吐血。
谋略比拼
孙恩的谍报人员也打听到谢琰所部的动向,于是叫来韩山友商议。他把局势分析一遍,说:“我军登陆才开始,是否按原计划到会稽,先打卢循,再战谢琰,值得斟酌。”
韩山友先是拍孙恩一阵马屁,说他一纸“征南大将军”的任命,就稳住了东阳的三万人马,实在是高!然后出主意说:“主公,我看这样:我们的战船在海岛与大陆之间来回穿梭,造成十万人登陆的假象,从心理上击垮卢循。谢琰到会稽后,肯定和卢循血战,双方都会大伤元气;不管谁输谁赢,都拿我们没办法,因为他们的水军可以忽略为零。如其两败俱伤,我们再视情况迅速登陆,一举歼灭之。”
“好,跟我想到一块去了!”孙恩敲定了战略部署。
打仗,不仅是比拼实力,更是心智的较量。会稽的卢循没闲着,也在反复思考,以图扭转不利的局势。当前,李流不听自己指挥了,凭会稽六七万人,要抵御谢琰和孙恩东西两面的进攻,这根本不可能。如何是好?
徐道覆献计:“我们退守磬安以东的山区,保存实力,让谢琰与孙恩狗咬狗。”
对这条计谋,卢循赞成一半,在乱世中有实力才能自保,如这点家底折腾完了,自己什么都不是。但他认为,徐道覆的计谋还有两个缺点:一是让出会稽这块富饶之地,去当山匪,真是舍不得;二是孙恩守不住会稽,又逃回海岛,北府没水军,望海兴叹,那时,谢琰会不会发兵向南,进攻李流或自己呢?
徐道覆的计谋不行,得自己拿主意。卢循把自己关起来,冥思苦想了两天,终于想出一个自认为万全的方案,归纳起来三条:第一,自己带五万人进山区,徐道覆带一万多人留守会稽。原来也想过自己留守会稽,但有李流的教训,他对徐道覆也要留一手。第二,你孙恩不是要传国玉玺吗?我答应给,但要我送来,没门!你真要,就自己到会稽来拿。而且必须你天师王亲自来,看你有没胆量。你孙恩要是不来,我就大造舆论,说你是个胆小鬼;你要是来了,就得与谢琰硬碰硬。第三,徐道覆与谢琰假装硬打,实则一接触就向南跑,把一万多人马带来与我会合。同时徐道覆还要注意打仗与撤退的时机和方式,确保谢琰会与孙恩交上火。
卢循这一招,又将皮球踢给了孙恩。
让出会稽,不甘心!
“妈的!考我胆量,这个世上还没有我孙某人不敢做的事。”孙恩骂了起来。
韩山友劝说:“主公,卢循这人反复无常,要提防诱骗之计。”
卢循哼了一声,说:“怕什么?据可靠情报,他卢循留在会稽的只有一万多人,由徐道覆指挥,我带三万人同时入城,就是硬打起来,也稳操胜券。如现在我不敢去,反倒落下笑柄。”
韩山友说:“卢循为什么要躲进山区,还带走几万人?值得思考。”
卢循说:“这个问题我想过:卢循想据玉玺为己有,但军力明显不如我,不交出不行,由他亲手交出,他面子上过不去,所以避到山区,由徐道覆办理,眼不见心不烦。这年头,带点部队走,心里踏实些。所以他带走几万人,正常。”
韩山友心想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但也不好再说什么。
孙恩从海岛急调两万人,会同已登陆的一万,一共三万人向会稽开进。
到了会稽城外,徐道覆前来迎接。假意的客套刚完,孙恩问:“卢将军来信说,传国玉玺在你这里,你带来了吗?”
徐道覆回答:“这传国玉玺乃至尊宝物,怎能带在身上。卢将军有交代,要请天师王进城后,举行一个隆重的玉玺交接仪式。”
孙恩怕城里有埋伏,说:“今天本王困了,就在城外扎营。韩山友带点人进城,为我打前站。”
徐道覆还想说点什么,孙恩不听了,说就这样定了,明日午时,交接玉玺。
韩山友带进城的不是一点人,而是整整一万人。
当夜风平浪静,第二日上午,孙恩带两万人进城。交接仪式果真隆重,孙恩拿到传国玉玺,叩拜了天师神。
如果卢循在现场看到这一幕,心里一定会滴血,实力不济时,再好的宝贝也保不住,必须乖乖让与孙恩,气啊!
多手准备
孙恩拿着玉玺,做了两天的皇帝美梦,又必须回到现实——谢琰的部队打来了。韩山友说:“卢循虽然跑了,徐道覆还有一万多人,令他们出战。如他们实在顶不住,我们再上。”
第二天孙恩召开军事会议,安排徐道覆率领本部人马迎战。徐道覆领命而去。会议结束后,孙恩留下韩山友面授机宜:“我在会上,说的全是鼓舞士气的话,但我心里其实不踏实,你想想,谢琰的北府军大概有五六万人,他徐道覆能抵挡得住吗?就算把我们的三万人搭上,也并无把握。”
韩山友问:“主公的意思是……”
“我要你做好撤退的准备。”
“撤退?!”韩山友吃了一惊。
孙恩说:“是的。你想想,如果我们打败,从海岛调兵估计来不及,卢循会来增援吗?肯定不会。叫李流来增援,估计也难。当下这情形,最好的办法,就是徐道覆一旦战败,我们就迅速撤回海岛,以保存实力。谢琰没水军,拿我们没办法。在撤退的同时,我向卢循和李流下令,要他们同谢琰作战。如打赢了,是我指挥有方;如打败了,我也消灭了两个后患;如不服从我的指挥,就留下了口实,今后有机会,可按天师教规定惩处。”韩山友听了,表示赞同,还用拍马屁的口气称赞了几句。
孙恩还有一种情况没说出来,那就是若能侥幸在会稽站稳脚跟,他孙某就要称帝,过过皇帝的瘾。不然,拿着传国玉玺不当皇帝,多没劲。会稽古代是吴国都城,有帝王之气。如回海岛称帝,不伦不类的,感觉就差多了。孙恩拜着天师神,幻想着徐道覆能打败谢琰,或者天师神显灵,让谢琰突然暴病死亡。
天师神没有保佑孙恩。徐道覆带兵出城,刚看到北府军的影子,就朝东南退去,到山区找卢循去了。
强行突围
谢琰见天师军如此不济,抽出宝剑向会稽方向一指,要全军马不停蹄,围攻会稽。
按照孙恩和韩山友的估计,徐道覆再差劲,也会抵挡上十天八天,没想到他小子脚底抹油——跑得飞快。
撤退不能按计划实施,会稽四个城门外均有北府军。孙恩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损兵折将,强行突围;要么据城死守,调海岛之兵解围。他对调卢循与李流之兵解围,是不抱希望的。这两个人,巴不得自己早死。
孙恩征求韩山友的意见。平时足智多谋的韩山友哑了,只说听从天师王的安排。其实这也不怪韩山友,军事决策是非对称决策,只了解自己的情况,看不清对手的实力和意图,有时决策要凭感觉,有时还要碰运气。在此重大时刻,这个运气只能由孙恩自己碰,决心必须由他自己下。
孙恩还在反复考虑。韩山友提醒说:“主公,现在围城还不紧,要突围,就要早;要调援兵,也要早,不然,信使都难以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