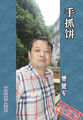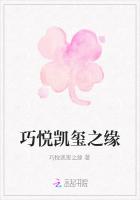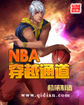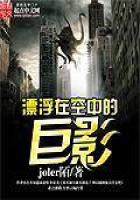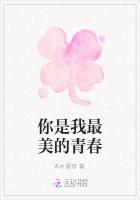韩山友的话有理。孙恩下决心了,今天夜里,从北门突围。按理说,从东门突围离海岸最近,孙恩想自己能想到的,可能谢琰也能想到,他就来了一个反向思维,从北门突围。
晚上要突围,下午命令传达,天师军开始作准备,城里也乱了起来。对于有的天师军士兵来说,这是第二次离开会稽,这次走后,能不能回来就说不清了。有的士兵想大捞一把,在城里公然抢劫;有的士兵看见姑娘,就往巷子里拖,如有不从者,一刀进肚。军官们也是各忙各的,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战乱中的会稽,最苦的是百姓。
孙恩全副武装,这套铠甲以前很合身,骑马行军很自然,现在觉得小了,也觉得沉重了。是啊,起兵成功后,自己养尊处优,人也胖了,小肚子隆起了。他把传国玉玺放进怀里,突然有种伤感涌上心头,现在还有退路吗?没有了,要么成功当皇帝,要么就死亡,没有第三种选择。虽然信仰天师神,但在他内心里,却根本就不信死后成仙那套,那是骗别人的。
赶到会稽的北府军是前部,总兵力不到三万人。北门外的北府军有六七千人。天全黑时,三万天师军一声呐喊,打开城门冲了出去。北府军急忙应战。论军事素养,北府军要强一些,再加上天师军部分人带着财物,负荷增多,也影响了战力。
天师军仗着人多,冲了出来,清晨一清点人数,只剩一万多人。
孙恩带着这支残兵败将,垂头丧气地朝海边走去。
骄傲了
谢琰骑着高头大马,在众人的簇拥中进了会稽城,自我感觉良好。他心想,以前与卢循的天师军交过手,战斗力不怎么样,现在孙恩的正牌天师军,也就这么点能耐,看来,自己手里的北府军,真的可以独步天下了。
谢琰给朝廷上书,说会稽此战,斩敌五万余人,孙恩只身逃到海岛。他夸大表功的目的,不是为了朝廷给他升官晋爵。到这个时候,不要说封官,就是封王,都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他的目标,是有一天登上皇位,享受一下三呼万岁的感觉。他上书,只是为了向东晋皇帝要点军饷,掏空国库,为自己夺权创造有利条件。
会稽之战,谢琰唯一感到不满意的,是孙恩带着传国玉玺跑了。如果传国玉玺在手,凭自己的实力,现在都可以拥兵自立了。好事多磨,慢慢来吧。传国玉玺,早晚是我的。谢家多年的积累,到我这里也该结出正果了。
谢琰曾当过会稽内史,在会稽很有知名度。他入城后,巴结者不计其数,在一片恭维声中,他感觉自己是改造时代的大英雄,开始飘飘然了。
有部下劝他,说现在虽然打了胜仗,但孙恩在海岛仍有实力,南边的卢循与李流,也不能小视。很显然,这是一个不识时务的部下。
谢琰分析说:“当年我谢家,只带八万人,就在淝水打败了苻坚的百万大军。现在这些天师军,不值一提。我要愿意,三个月之内即可荡平,但我不愿大开杀戮,因为天师军的士兵很多是被骗去的,我要用妙计,兵不血刃,结束动乱。”
这个一片好心的部下,听如此一说,感觉自己多嘴多舌,自讨没趣地走开了。
谢琰如此自信,还是有他的理由:一是自己这五六万人,的确比天师军能打;二是他还有刘牢之、刘裕这两支后备力量,随时可调到前线;三是孙恩败逃后,会稽南面的卢循与李流老实待着,没有异动。
谢琰没有考虑如何备战,而是派出信使,到海岛招安孙恩。他开出条件,说孙恩只要交出传国玉玺,不仅不追究造反之责,还能给个官当。
这样的招安注定不会成功,孙恩远没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有八万人。但孙恩也没完全拒绝,他应付着信使,为反攻争取时间。
孙恩反攻
天黑了,海飞吹来,孙恩关上门窗,点上灯,拿出传国玉玺看了又看。他派出信使去卢循和李流那里,联合他们一起夹击谢琰。这两人回信,完全同意。但,孙恩对他们的话不敢相信,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机会主义者。孙恩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干掉谢琰,所以他把备战放在首位。
准备差不多了,孙恩望着大陆,思考反攻之策。韩山友这个战术级别的军师献出两条计谋:“其一,夜里登陆,海船马上返回,部队晚上行军,白天在山林里休息,然后突然出现在会稽城外;其二,派出天师军混入会稽城,攻城时点火,制造混乱,里应外合。”
孙恩认为韩山友的建议不错,照单全收。
天师军打回来了,一路顺利,当内应打开城门,几万人拥进了会稽,与北府军巷战。
面对从天而降的天师军,谢琰慌了,保命要紧,下了撤退的命令。孙恩下令追击。
北府军的兵油子,经验丰富,在撤退时带着金银财宝,有的车辆上还装着抓来的女人。当天师军追近时,就将财宝丢下,将女人推下车。天师军的士兵穷得太久,见不得这些宝物,就去抢钱财、抢女人去了,谢琰得以逃脱。
是否称帝?
孙恩又成了会稽的主人,按原定计划,他该称帝了。他还没进城,一些看准主子心思的溜须拍马者,就开始进言上书,说他称帝是受命于天。
孙恩长子孙亮,极力怂恿老爸登基,他好早当太子。连韩山友都说,玉玺在手,及时称帝,君临天下,号召四方,大业可成。
劝进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人跪在孙恩门前,说孙恩不称帝,他就不起来。这不怪他们,众人都盼着“革命”成功,弄点好处:孙恩的妻妾,等着当皇后皇妃;文臣武将和身边的人,也想封官授爵。
当皇帝,是孙恩多年的梦想,是冒着风险造反的动力,按理说现在是水到渠成,只要往上面一坐,下面就有人高呼万岁,还等什么?
局面可喜,在进城之前,孙恩就找裁缝量了尺寸,制作龙袍。但进城后,城内的惨状与现实,使他清醒了几分。
会稽城这几个月战火纷飞,经卢循、谢琰、孙恩三支部队的多次抢劫,已是满目疮痍,大街小巷商铺全关门,城内闹粮食危机,随处可见饥民倒毙街头。战乱中最易受伤害的是女人,年轻的、有点姿色的女人,不是被抢走了,就是被糟蹋了,有的逃到乡下去了,如要登基,找装点门面的宫女都难以找齐。徐道覆来报告,说会稽附近征不到粮,军队给养需要从海岛运来。目前这样子,能登基称帝吗?孙恩犹豫起来。
探子来报,说谢琰战败后并没有回建康,而是在湖州以南驻扎下来,收拾残部,加以训练,有打回会稽的倾向。这对于孙恩来讲,肯定是一个坏消息。
孙恩心想:此时在会稽称帝,因客观条件限制,排场肯定不大。再说,如现在称帝,谢琰得到消息后,说不定会立即进攻会稽,自己龙袍刚穿热,又要领兵打仗,如打败了,又得退回海岛。与其这样不伦不类、心有不安地称帝,不如趁着士气高昂,一口气打下建康,把东晋皇室赶尽杀绝,再安安稳稳地称帝。
孙恩将自己的思考告诉了韩山友,征求他的意见。韩山友本来就是墙头草,顺着意思说:“主公所言极是,打下建康,灭了晋朝,天下自然姓孙。到时,我们再风风光光办一个登基大典。”
调兵遣将不如意
参加过淝水之战,自认为见过大世面的谢琰,没想到自己对阵天师军时,会不一小心“阴沟里翻船”,他不甘心。他自我安慰,说胜败是兵家常事,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笑。
到湖州境内,谢琰一清点人数,自己带去的近六万人马,如今只有四万人,中高级将领也损失十几个。他一方面收拢部队,就地训练;另一方面给刘牢之、刘裕下命令,要他们带兵前来增援。谢琰心想,刘牢之有三万人,刘裕有一万五千,所有北府军聚集在一起,就有八九万人,如进行针对性训练和备战,打败天师军应无问题。
传令官到湖州,刘牢之继续装病,不作答复。谢琰派出次子谢峻,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刘牢之。
病床上的刘牢之咳咳嗽嗽,说话时断时续,看样子病得真不轻。他当着谢峻的面,叫来副将张猛,叫他带两万人,去与谢琰会合。
向刘裕传令的人回来报告,说没找到刘裕所部。这不对啊,按行程计算,他该走到建康了。
原来刘裕从东阳撤离时,一路拖拖拉拉,每天只走十里。同时他派出探子打听战况,当听到孙恩反攻会稽得手,谢琰兵败退到湖州境内时,心想谢琰一定会调自己参加战斗,于是带着人马躲进山里,跟谢琰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
虽然调兵遣将不如预期,但谢琰打听到,会稽以南的卢循、李流所部并无动作,没有向孙恩靠拢的意思。这真是天助我也!自己手下的兵力,与孙恩相当,这仗可以打了。
一个时代的终结
谢琰带兵向会稽开进,离城五十里下寨,派出探马前去察看情况。探马回来报告,说会稽城门大开,旌旗全无,听老百姓说天师军全部离开了。
有这等事?孙恩没跟我交火,就逃跑?有人主张大军开到城下,如无天师军,六万人马一起进城。谢琰不同意,说上次吃了轻敌的亏,这次必须小心行事。他决定明日亲自去看个究竟,再作定夺。刘牢之的副将张猛主动请缨,说自己是会稽人氏,地形熟悉,愿一同前往。
第二天,谢琰带着长子谢肇、次子谢峻和张猛,以及几十名随从前去会稽。
前往会稽的路上,野兔林是必经之地。这个平原上的山丘树林茂盛,冬暖夏凉,是个路人歇脚之处。但在不太平的岁月,时有强人出没。张猛说:“野兔林虽然不大,但可藏兵,我先带人进去探看,如无伏兵,将军再入。”谢琰同意了。
一会儿,张猛回来,说树林里只见野兔不见人。谢琰放心入内,谁知当走到林子深处时,突然,树上射出一阵箭,随从多人被射杀。谢琰及儿子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往回跑。谢肇和谢峻跑在前面,被绊马绳绊倒,跌下马来,两边跳出蒙面人,一阵乱刀将他们砍死。谢琰在张猛的护卫下拍马疾奔,眼看就要跑出林子了,突然,张猛朝谢琰的马屁股猛砍了一刀,马剧痛,将谢琰摔下来,蒙面人跟上,一刀结束了谢琰的性命。除张猛外,谢琰带去的人一个都没活出来。
后面的情节不用多讲,刘牢之病好了,来到军中,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宣布,谢琰侦察敌情时,中了天师军的埋伏,为朝廷捐躯了。谢琰的部队,全部由刘牢之接管。刘牢之心想:终于没有管自己的“婆婆”了,凭着手里的北府军,该我登场了,为了这一天,我隐忍太久。
在晋朝,选官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朝廷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为三品,共九品,大官必须在上等的三品人中产生。品是按阶级成分划分:高门士族入上等,越是豪门品次越高;一般士族,就只能入中等;工、商、农、兵、佃之流,不论你多优秀,都只能入下等,要想当大官,门都没有。
刘牢之庶族出身,按理说只能当中级军官,因他屡立战功,在谢家的培养和保举下,他才当上高级将领。可是,他的官也当到头了,因为出身问题,他不可能位列九卿或者封王加爵。他心里不平呀!凭什么?自己的能力比那些王、谢士族都强,但他们的官就是比自己大。
其实,刘牢之对恩人谢琰下毒手,不完全是因为阶级裂痕,而是他的官场历练,培养了他的信仰——对权力的渴望。他要想夺得最高权力,必须掌控北府军,要掌控北府军,必须除掉谢琰。当你成为我夺权的绊脚石时,我才不管你是否有恩于我。这就是刘牢之的理论。
权力,让人痴迷也让人疯狂!
谢琰死了,豪门士族的旗帜倒了,一个属于士族的时代终结了!王、谢两家留给后人的,更多是“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慨。
刘牢之,东晋末年的权臣,从谢琰之死起,真正登上历史了的舞台。他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