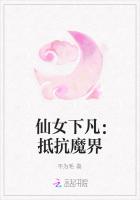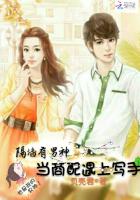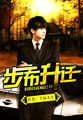你快乐吗?
起初,我想进大学想得要死;
随后,我巴不得赶快大学毕业好开始工作;
接着,我想结婚、想有小孩又想得要命;
再来,我又巴望小孩快点长大去上学,好让我回去上班;
之后,我每天想退休想得要死;
现在,我真的快死了……,
忽然间,我明白了,我一直忘了真正去活。
——无名氏
这本书探讨的是使生命富有意义的“真实刹那”,以及我们如何拥有更多“真实的刹那”。它要你去体验生命中每一刻的完满与奥妙,真正的满足就在当下的此时此刻,而不是非要等到赚了更多的钱、找到门当户对的另一半或减肥成功以后才能获致。它探讨如何重新看待你与伴侣和孩子在一起时的真实刹那,工作和游戏时的真实刹那,最重要的是,面对你自己的真实刹那。
诚实看待你自己的生命。你每天每夜所做的事都很有意义,且能使你心中微笑吗?你是否把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几乎毫无乐趣的事情上?当你生命终了,你会不会希望自己曾经以另一种方式过活?如果你只剩下一个月的寿命,你会做什么改变?
检视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你快乐吗?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必须拥有才会快乐?你确定拥有那样东西之后,你一定会快乐吗?那样你就满足了吗?
真切正视你自己心灵的价值。假设明天你突然死了,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哪些时光会是你最珍视的?你会最想念活着时候的哪一部分?
“用心”
借着这本书,你可以开始针对这些问题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就像我也一直在找寻属于我自己的答案一样。我相信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它会迫使我们不再麻木地、机械式地过日子,而必须用心去活。
有一个禅的故事很有名——一个弟子来到师父跟前,请求师父开示生命的智慧。师父对这焦急的弟子注视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毛笔写下“用心”二字。弟子不解,着急地请师父解释,师父又写了一次“用心”。这时,年轻的弟子又颓丧、又生气,完全无法理解师父要教给他的道理。于是,师父再次耐心地写着:用心……,用心……,用心。
生活的片段,有时是无尽的喜悦,有时是深沉的伤恸。然而不变的是,当你全心全意于你所处的那一时、那一事、那个当下,你所经验的便是一个深具意义、绝不枉费的刹那。这就是我所说的“真实的刹那”。
电影“银河飞龙”里有一句台词是:
我发现“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是人类常问的典型问题,然而,我倒觉得,不如问问:“我们真的在这里吗?”这似乎更值得深思……。
此刻,你正心无旁骛读着这个句子吗?抑或分了神想着其他该做的事,或盘算着晚餐要吃什么?你是不是好像在读着,心里却仍挂念昨晚和女朋友吵了架,或在猜想刚才碰到的那位男士,会不会打电话来约你出去?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全然专注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无法心无杂念地感受眼前时刻。我们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心不在焉上,以至于很难拥有真实的刹那,因为只有在你百分之百地经历当下的那一瞬间,真实的刹那才能富含力量,才能完满。
真实刹那的另一个说法是“全神贯注”。全神贯注是许多东方传统思想,特别是佛教的核心概念。简言之,就是将全副心神贯注在眼前手边的事物上,让心灵毫无杂念地去体验当下。
投入每一瞬间
全神贯注使你完全投入那一瞬间,它能把每一个寻常的经验——如散步、哄孩子入睡、拥抱伴侣、甚至单纯的开车,转变成一个个真实的刹那。当你全神贯注,就能毫无遗漏地去感受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和正在做的事,而不是麻木地让眼前这介于过去和未来的瞬间,成为又一个即将逝去、将会遗忘的时刻。稍后,我会在书里提供一些能帮助我们活得更全神贯注的方法。
全神贯注的相反是麻木,没有思考、没有感觉、机械化、无意识地活着。我相信,我们自己和周遭亲友的许多痛苦,其实是肇因于我们的麻木:
·因为麻木,你才可能维持着一段对你毫无益处、甚至可能有害的关系,而且全然无视于自己的悲惨不幸。
·因为麻木,你才会长年累月忽略身体对你发出的警讯,忽视它的慢性消化不良或胃溃疡,只晓得猛吞胃乳片,直到多年后医生对你说你已病入膏肓,才懊悔不已。
·因为麻木,你才会抽芋、喝酒或吸毒,无视于自己的日夜咳嗽、情绪不稳、精神时好时坏,不知道自己是在慢性自杀和伤害所有爱你的人。
·因为麻木,你才可能明知身处于不公平的境遇中,却仍默默承受,毫不反抗。
太多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受困于这个不健康的习惯;而一旦麻木地过日子,我们便错过了所有真实的刹那。心理学教授蓝爵(Ellen Langer)写过关于麻木的书,他说麻木生活和行动的人,一不小心就会堕入行尸走肉的泥沼里。我们顺着时间走下去,眼光却不看着当下,只着意于未来,之后则怀疑,为什么不曾走到任何能给自己有持久成就感的标的。
若想拥有每一个真实的刹那,
就要用心迎接生命为你展现的每一刻,
全心全意活在当下,
放开心胸去充分感受,尽情展现生机。
为未来而活
在美国要过得麻木很容易,因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为更美好的明天而活、而梦想”。美国向来是逐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从世界各地移民来这里,被鼓舞着去怀抱更大的梦想。问题是,整个二十世纪的后半段,我们都在为明天而活,对当下所付出的时间则少之又少。我们为未来计划、为未来担忧,然后不知不觉中,当生命走到了尽头才醒悟:我们一心一意计较已发生或希望到来的事,却忘了享受当下的每一个片刻;我们都变成“为生活做准备”的专家,同时也变成“现在就充分享受活着”的低能儿;我们为事业做准备、为休假做准备、为周末做准备、为退休做准备——总括起来,我们其实是在为生命终了做准备。
如此擅长于为未来而活,问题就出在我们已养成了不活在当下的习惯,于是当那些期待已久的美好事物真正来临——假期、升迁、狂欢会……,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享受了。面对这些引颈企盼了好久的美事,我们依旧匆忙走过,仿佛只是又一桩麻烦事,我们迫不及待要把它解决掉,但事过境迁,又想不透自己为什么还觉得失落、觉得不满足。
最近有一位好友结婚。她花了一整年时间来筹备她的婚礼——那的确是一场别致、出色的婚礼。第二天早上,出发去蜜月旅行之前,她从机场打电话来。我问她是否满意这场婚礼,她竟表示她感到异常空虚。“我几乎想不起来婚礼的样子,”她的声音里透露着失望,“好像迷迷糊糊地就过去了。”
我这位好友的经验并不特别:当我们将生命耗费在为未来做准备,而非享受眼前时光,我们便把快乐也给延误了。我们失去了欣赏和领受快乐的能力,一旦真有机会体会真实刹那,就只能和它们擦身而过了。
在美国,我们活在一个只重行动、不重实质的文化里,这也就难怪我们如此拙于创造真实刹那,更遑论能在每一个当下怡然自得。我们一向重量不重质,只在乎不断的活动所带来的刺激,对实质问题则不闻不问。我们常以外在的成就来论断别人或自己,却忘记自己在本质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群兴风作浪的行动者、成就狂,一如塔希(Nina Tassi)在《嗜快成瘾》(Urgency Addiction)书中所描写的“一群速度崇拜者”:“愈大愈好……”“任你吃到饱……”“买一送一……”“一样价钱买得更多……”“史无前例的速度感……”“最新、最先进的……”——这就是美国精神。
错用“消费意识”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消费主义时代。我们要尽可能地多,且尽可能地快速,消费和业绩成为我们的快乐之钥。我们对自己说:只要有汽车、房子、彩色电视和一个好工作,我们就算过关了;如果我的这些东西能比隔壁那家伙的更新、更好,或能谋到一个名号更响的差事,可就成就傲人了。我们的英雄是那些拥有最多的人,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事物上,人生的目标不再是生活,而是“拥有”和“完成”。
无可避免地,“消费意识”把我们通通变成了延误快乐的高手。延误快乐的意思就是:相信“为了要快乐,必得要有某些先决条件才行”;你想像自己:“等到……之后,我一定会很快乐。”
我们相信在拥有某种经验、或某种财富、或某种地位之后,我们就会快乐,而在这之前,快乐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努力工作,或任时间流逝,然后终有一天,我们所期待的快乐源头就会降临。我们完成学业、减肥、创业或买房子,然后欣喜地等待快乐的到来——同时大失所望;我们或许会觉得满足,却不快乐。
这样的过程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没错,我知道我曾说只要当上经理,我一定会很快乐;可是我现在才发现,真正能让我快乐的,是当老板。”于是我们再一次把快乐顺延到下个目标上。
时不我予
就像吸毒一样,总是需要愈来愈重的剂量,才能达到兴奋效果,最后终有一天,你再也离不开它。我们之中,一定有很多人已经步上了这条路。我们买了车子和房子,我们投身工作,并且正一步步爬上了成功的阶梯,我们努力供给小孩那些我们不曾有过的一切享受。我们得到很多想要的东西,也当上了我们从前所欣羡的成功人物;但是渐渐地,我们开始怀疑,好像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不停追求的那些梦想,已经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心灵和情感的死胡同:这一路上,我们拿出所有真实的刹那来换得财富、换取目标的达成,但是,我们换不到快乐。
而更可怕的是,在这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已悄然飞逝了。每个周末,我们奇怪一个星期又跑哪儿去了;每个除夕夜,我们感叹怎么一年又不见了;早上醒来,赫然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岁、四十岁或更老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时间是怎么流逝的!我们看着孩子毕业、有了自己的家,但总觉得摇他们入睡、教他们绑鞋带,都仿佛是昨天的事。
当我们将生命耗费在为未来做准备,
而非享受眼前时光,
我们失去了欣赏和领受快乐的能力,
与每一个真实刹那擦身而过。
我们不能教时间慢下来,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向死亡的那一端迈进、一点一点地在变老;但是我相信,一旦我们能更全心全意地体验生命的每一刻,就会觉得时间过得更有意义。
最长的四十秒
你的一生中,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明明是稍纵即逝的刹那,却觉得有好几个钟头那么长;明明才几个星期,却像是过了几个月;才几个月,却好像已经过了一辈子。通常在这种时候,你完全专注于当时的情境:分娩的时候、自己或家人在病床上等检验报告出来的时候、和心上人第一次亲吻拥抱的时候、整晚盯着电话等男朋友为昨天的争吵道歉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形下,时间的脚步似乎慢了下来,尽管你的理智告诉你,这一天、这个夜晚绝对跟其他任何时候一样,你还是会发誓:感觉起来起码有两倍那么长。那是因为当时你的人、你的心、你的感情已经完完全全地投注在每一个瞬间了。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七日凌晨四点三十一分,我和上百万的南加州人,一起经历了一场美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地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恐怖的感觉:我们夫妻俩只能死命地攀在床边,在寒冷的黑夜里,周遭的一切给震得地动山摇、隆隆作响,而听起来就像是世界末日到了!我们死定了!
谢天谢地,我们没死。之后的几个小时,我们缩在衣帽间的地板上,等着余震过去。我们简直不能相信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所有报导都说主震大约持续了四十秒。“不可能!”我和丈夫相互叫着:“至少有三分钟!”我们觉得新闻报导都错了;可是他们没错!后来的几天,我和很多朋友邻居谈起那次地震,也听了许多收音机和电视里的报导评论,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地震只有四十秒。他们都和我们一样,一口咬定地震持续了好几分钟。当然,我们都错了。我们经验到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长的四十秒。
毋庸置疑,那次地震是我有生以来最恐怖的经验。它绝对够资格成为一个真实的刹那,尽管我绝不希望常常遇上!然而,和所有真实的刹那一样,它赐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礼物——知道了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使夫妻间变得更亲密,家人关系更接近,明友和陌生人之间也增添了真诚的关怀和亲切感。经历过这样震撼的时刻,我们的心被震开了,我们的灵魂被震醒了。因为我们被迫放慢了脚步,在地震当天的每一分钟和往后的几天里,一心一意面对遭遇到的一切,结果,我们感受到了更多的爱。
我的寻乐之路
打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是一个探索者。凡认识我的人从不会形容我是个无忧无虑、天真快乐的小女孩。我父母的婚姻并不愉快,从孩提时代,我就想为母亲眼中的忧郁、父亲心中的迷惑和我自己的痛苦找寻答案。最教我小学老师讶异的,是我三年级时第一次写诗时,问道: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快乐?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人生的意义,找不到答案让我异常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