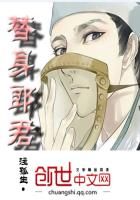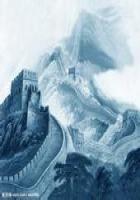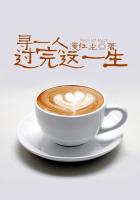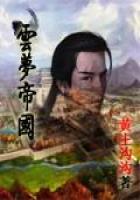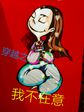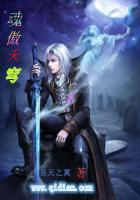腾冲自我军占领以来已有两年多时间,治安已趋于稳定,是一座充满和平、宁静气氛的城池。城内住户的屋檐下,梅花、桃花争奇斗妍;城外的村子里,白色的梨花和红色的木瓜花也互相美丽地衬映着。居民们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和平、宁静的小城不久就要陷入可怕的战火之中。尽管无情的战火大幕已经笼罩了城池周围。[[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7页。]
章东磐《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节选1944年5月,反攻发动之时,怒江峡谷的雨季也如期来临。想想吧,那半尺多厚的浮土全部变成胶泥,穿着草鞋的中国军人们要怎么仰攻这个要命的灰坡?在半尺深的稀乎乎的胶泥里走过路吗?踩下去像油一样滑,拔脚起来却比胶还粘。陡坡上,顶着泼水一样的弹雨,还要顾着脚下,一不留神,只要跌倒,几百米一路跌撞着滑下去,必死无疑。所有的参战者,只要听过、看过他们的回忆,无一例外都在诅咒那个该死的灰坡。年轻的美国陆军中尉夏伯尔,就与几百位中国军人一起献身灰坡。仅仅21岁,那个年纪的帅小伙,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就战死异国。60年之后,在美国陆军的档案里,他登记的两位联络人只有他的父母,他的双亲辞世之后,再没有一位美国人能给我们讲述他短暂而光荣的生命了。
我真希望看到那座纪念碑的建立。我还希望在我们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上在介绍高黎贡山的那一课加上这样一句:在这座山上,我们中华民族取得了一百年屈辱之后海拔最高的胜利。我确信,这句话,比纪念碑更重要。
师长的生死状
灰坡,是到达高黎贡山顶的必经之路,为了夺取这块阵地,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官兵在这里与日军展开厮杀。第二次攻击灰坡失利后,第一九八师师长叶佩高亲临前沿阵地,立下军令状:“第三次攻不下灰坡,这里便是本人的成仁之地。”时为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中尉通讯员的张庆斌回忆:叶佩高平常都穿普通衣服,那天穿上了他的毛呢军服,很威风。进攻时,一个营的人也攻不上去,往后退,一退下去,看到师长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命令他们打回去。那些士兵又转身往上冲,死了很多人。打了三天三夜,炸了敌人的碉堡,最后才把灰坡拿下来。
国殇(上)
亲历者
陆朝茂——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机枪连战士寸希廉——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
寸可富——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
张孝仲——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
钏相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张金政——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战士
李华生——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彭良——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六师战士
董澄庆——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何绍从——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运输团战士黄友强——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战士
周德黎——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师战士
张元称——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炮兵连连长周有富——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吉野孝公——时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必须承认,陆朝茂老人的故事最初并不是这集的主线。老人的讲述掩埋在一大堆方言和并不准确的“翻译”之后。采访笔录上的“来凤山”打成了“丰风山”,腾冲城则一概被老人称作“城里”。所幸,有一个词,老人的发音很清晰——墓园。
老人提到的墓园,就是国殇墓园。这座中国现存最大的远征军陵园,是1945年7月7日为纪念腾冲战役阵亡将士而修建的。曾经,陆朝茂的墓碑也在这里。只是,他还活着。
故事由此开始,这可能也是所有6集“滇缅系列”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故事。那块墓碑真正的主人,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早已逝去。我用尽全力去寻找一切有关他的信息,但我最终得到的,只是陆朝茂夹杂着浓重乡音的一句话:“他平时就睡在我旁边,是个保山人,名字叫李唐。”
做完片子,陆朝茂的这句话仍久久回旋在我的脑中。我忍不住遐想,这位名叫李唐的战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从战前不愿和战友们一起向菩萨磕头这一举动来看,他应该是个挺有个性的小伙子。他在参军之前有过怎样的经历?他的家人知道他的结局吗?他有多高?长什么样?对于战争结束后的生活,他有过怎样的计划?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又会成为怎样的人呢?
据说,抗战结束后,陆朝茂每年都会到国殇墓园里来为自己的墓碑扫墓。因为只有他才知道,这座墓碑下面那个年轻魂魄的真实身份。67年过去了,无论我们对那位名叫李唐的战士有着怎样的想象,这个年轻的生命留给我们的,只剩下那一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描述:“他平时就睡在我旁边,是个保山人,名字叫李唐。”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陇西行》陈陶
编导刘元
国殇墓园,位于云南西部腾冲县城西南1公里处的叠水河畔、来凤山北麓,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阵亡将士陵园,为纪念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战役中的阵亡将士而建,1945年7月7日建成。
“文革”期间,国殇墓园作为“反动四旧”,遭到了严重破坏,大量墓碑、墓穴被捣毁。
1984年底,国殇墓园开始重修。重修后的墓园现存墓碑3346块,这个数字,还不到整个腾冲战役中国军队阵亡人数的一半。
国殇墓园的这些墓碑上,有的空无一字,有的刻着烈士的名字和军衔。其中一块墓碑上,刻着一个名字:陆朝茂。
但是,陆朝茂还活着。
总攻前夜:士兵们在寺院磕头
1944年6月底的一天,高黎贡山西侧,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机枪连战士陆朝茂,正和战友们在日军战壕中摸索前进。四周,日军败退时扔下的装备随处可见。
陆朝茂回忆:“里面没有人了,我们就进他们的碉堡、交通壕里面去检查。一个小水壶,上面打了好几枪;血顺着交通壕淌,从这边一直淌到那边;敌人的饼干、罐头,全都在交通壕里面,我们拿起来看了看,沾了血迹的,我们就留给别人,没有沾血迹的,我们就尝尝,看看是不是下了毒要毒死我们,尝了以后觉得也没毒。”
陆朝茂是腾冲人,1942年6月入伍,1944年6月,年仅18岁的他跟随预备第二师突破日军高黎贡山防线,抵达腾冲近郊。这是陆朝茂从军两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乡。
陆朝茂说:“预备二师中腾冲人有三分之一,对地形比较熟悉,上面就把我们调回来了,也就是用腾冲的兵来攻打占领腾冲的日本人,可以保证打胜仗。后来我们就到了和顺旁边的一座山上,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能够看清对面山上的日本人。”
和顺乡,位于腾冲县城以西3公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西南商贸路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因从这里走出过很多海外华侨,而又被称为和顺侨乡。1944年7月2日,预备第二师进驻和顺乡,从这一天起,这座因拥有全国最早的乡镇图书馆而被誉为“书香名里”的村庄,成为远征军进攻腾冲的前线基地。
“我们来到了一户人家,问那家人日本人还有没有,那家人说(日本人)走了,天亮的时候就已经撤走了。”陆朝茂说。
确认完敌情,陆朝茂和战友们在老乡家里躺下休息。安静的住所,干净的床铺,再加上村民们的盛情款待,使得这些腾冲籍的远征军战士真正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前来劳军的村民中,有一个叫寸希廉的年仅12岁的男孩。在和顺乡,寸家是相当有名望的大户人家。远征军进驻时,寸希廉是寸家年纪最小的男孩。
在寸希廉的记忆里,远征军到来后家乡最大的变化就是自己很难再吃上肉了。
寸希廉回忆:“把和顺乡所有的鸡、猪等牲畜登记在案,每天轮流宰杀,供应部队,每个连队每天到乡公所领取肉、蛋、蔬菜、粮食。到后期的时候,和顺乡的鸡、猪都杀光了,每天早上,老百姓在菜市场里根本买不到肉食。”
让当地老百姓惊讶的是,一批金发碧眼的洋人也来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中国远征军部队中有一个美军参谋团参与战役策划,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也来了。
寸希廉记得:“中国军队进驻和顺乡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3号中午,一队美军从缅箐这个地方到和顺乡来,就在和顺乡对面的大庄村和下庄村的一片草地上,一些人坐着,一些人卧着等待安排住处。被来凤山上的日军发现了,就向他们开炮,那个方向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来凤山上一片烟雾。”
来凤山,位于腾冲县城以南,海拔高度约1914米。从山顶可俯览腾冲全城,是腾冲外围一处重要制高点。日军在山上修筑永久性工事若干,遍布鹿砦和地雷群,并挖有三重反坦克壕。[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1944年6月22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调整部署,令第十一集团军集结主力,击溃龙陵当面敌之攻势;第二十集团军主力保持于左翼,迅速南下,攻击腾冲而占领之。[臧运祜:《论滇西缅北会战中的中国远征军及其战术》;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
据守腾冲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于6月27日派出第三大队增援龙陵后,城内守军尚有2025名,连同非战斗人员等不足3000人。
7月2日拂晓,第二十集团军对腾冲外围据点发动全面进攻。[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页。]
据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经过概要》载:“巳俭,我五四军以迅雷之势,攻占宝凤山。兹为出敌意表,于午东夜,变更部署,将五三军主力由腾北上、下马坞转至腾东飞凤山附近,所遗阵地由五四军延伸。迄于江日,我五三军一举攻占飞凤山,五四军亦于同日攻占蜚凤山。于是,我已打破腾城屏障,三面迫近城郊矣。是时也,残敌一部仓皇南窜,其主力编成一个混成联队,由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大佐指挥,死守来凤山及腾城。该城为滇西最坚固之城池,兼有来凤山之屏障,并构筑坚固之工事及堡垒群,准备充分之粮弹,奉命困守至十月底,以待援军来到。我军既于微日迫近城郊后,除以五三军之一个师尾击溃敌,挺进至南甸、龙头街之线,并阻敌增援外,随即策定攻击腾冲及来凤山之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2页。]
7月6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下令于次日拂晓,即“七七”事变7周年之际,展开对腾冲日军的最后屏障——来凤山的总攻,计划以四个师的兵力,分别自南、西、东三面向来凤山发起攻击,其中预备第二师担任正面主攻。
总攻前夜,寸希廉正在上中学的同族兄弟寸可富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那时候,和顺乡的学生都去支援前线,当向导,去抬担架,送饭。我们那天是到东山脚,那边驻扎着一个连。那天早上天还没亮,点了一个火把,连长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我说:‘小兄弟,你把这张纸条递给我们的司务长,买来的鸭子让他帮我煮好。待会儿你们送饭的时候,帮我送到阵地上去。’连长和司务长是老乡,他说:‘如果明天打仗,侥幸活下来,那就是我们为抗日付出了努力,如果不幸牺牲,那么就请你帮我带个信给家里。’”寸可富回忆说。
总攻前夜,陆朝茂和战友们在和顺乡的一座寺院里集结完毕。庙堂里的菩萨引起了这些农家子弟的注意。
“班长说,这个寺院,我们进来以后要磕头,我们也真的就磕了头。”陆朝茂说,“和我睡在一起的是个保山人,他说:‘当兵的要杀人的,磕什么头啊?我是不磕。’他没有磕头。”
陆朝茂记得,他的名字叫李唐。
总攻前夜,腾冲县城东北角日军碉堡,不久前从高黎贡山撤回腾冲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吉野孝公做好了战斗准备。他已知晓,根据日军密探获得的情报,中国军队将在第二天一早发动总攻。
多年后,吉野孝公在回忆录中写到大战前的形势:
雨季的腾冲坝子上,绿油油的稻田朦朦胧胧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远处蠢动的敌兵身影视若蚂蚁,其人数在不断地增加。剩下的腾冲守备兵力有2800人,其中还包括在野战医院里的800名伤员。这样,剩下的2000兵力,将要迎击敌人的60000大军。[[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25页。]
1941年12月22日,日本陆军第一四八联队编组成军,1942年3月随第五十六师团入侵缅甸,同年5月10日攻占腾冲。此后,该联队一直驻守腾冲地区。两年的时间里,这些平日里并无重大战事的日本军人,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修筑工事上。大战在即,据守腾冲县城及来凤山阵地的他们,感到了紧张。吉野孝公回忆:
迎击敌人六万大军,紧张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