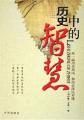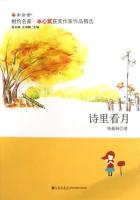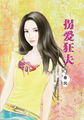守备队本部命令:“我腾冲守备队在此次作战中,将要迎击二十倍于我的敌人,也就是要面临二十比一的挑战,所有队员必须做好勇猛杀敌的思想准备,死守阵地!”[[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25页。]
7月7日:首攻来凤山,全村老小观战
第二天拂晓,敌人果然开始了总攻。敌人从稻田对面步步逼近地攻过来。敌人的炮兵阵地也一齐向我猛烈开火。飞凤山的敌炮兵阵地顷刻间不惜血本地向我阵内各阵地倾泻了约一千枚炮弹。[[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26页。]
1944年7月7日,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对日军来凤山阵地发起总攻。
这一天,12岁的寸希廉在自家窗口目睹了整天的战斗。
寸希廉回忆:“之前连续几天下雨,但那天放晴。刚刚天明的时候,和顺乡人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大家兴高采烈,倾村而出,有的站在屋顶上,有的站在后方的高地上,找好位置,看飞机轰炸,看炮兵轰击的那种壮观场面。没有一个人留在家里面,连一些最老的人、年轻的娃娃都出来看,那种场面就像是赶庙会看节目一样。”
由于来凤山位于和顺乡与腾冲县城之间,正在山下对峙的敌我两军都能看到山上的情况。硝烟笼罩下的来凤山俨然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山这边,中国村民们翘首观望;山那边,腾冲城里的日军则在焦虑中目睹着山上的每一个变化。
寸希廉回忆:“中国军队第一天攻打来凤山的时候,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不断地向日本人的几个据点攻击,工兵用破坏钳,破坏日军的铁丝网。当中国军人拿着破坏钳刚爬到铁丝网那儿的时候,就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连续打死了七八个。”
老兵钏相元回忆:“日本人的阵地面前是铁丝网,我们拿着钳子去把铁丝网剪开,好让战友们冲上去。铁丝网还没有剪完,日本人就看见我们,甩出来一颗手榴弹,把我的脚炸伤了。”
为了不让进攻的中国士兵找到合适的隐蔽物,日军事先将来凤山上的树木几乎清除一空。光秃秃的山坡上,无处可藏的远征军官兵们,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中伤亡惨重。
陆朝茂回忆:“日本人能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们,他们开始打枪后我们才发现他们,我们就把重机枪瞄准他们的碉堡打,打了5袋子弹。当时我动作很快,刚弯下腰去的时候,有一枪打过来,把我的帽子打掉了,那帽子上被子弹擦过,都糊了。班长说要不是有这帽子,你今天肯定就被打死了。结果那以后三四个月时间,我都没有剪过头发,就一直戴着那顶帽子。”
不是每个人都像陆朝茂这样有死里逃生的运气。老兵张金政说:“死的那些都是机枪子弹打到脑袋上,身子打不着,日本人他们都是在高处,我们是在底下,条件没有他们那么好。”
老兵彭良回忆:“日本人在来凤山上设置了机枪,我们有一个连冲上去,一个不剩全部被打死了。”
老兵李华生回忆:“攻来凤山的时候,已经攻上去了两三次,都是将要攻到坡顶的时候又被打了下来,人死的死伤的伤,能打的人越来越少。那个时候当兵的待遇也不好,看到人死多了,各个连队都开始动摇,有的想打,有的不想打。”
战至中午,远征军仍然被死死压制在半山腰,寸步难进。一直观战的和顺乡村民们,开始组织人员上山为远征军官兵们送饭,前一天刚刚接到煮鸭子任务的中学生寸可富也在其中。只是,他再也没能找到那位向他下达任务的连长。阵地上,除了死尸,再无他物。
寸可富回忆:“我提着煮好的鸭子上去,还没到阵地上,只听见有人喊‘来了来了’,滚下来一具尸体。我看了一下,不是日本人,是被打死的中央军,那个人被日本人的子弹从肚子外面打进去,从后背穿出来,肠子都被打断了。”
来凤山阵地和腾冲城内的日军受到了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吉野孝公回忆:
下午,敌人出动飞机进行攻击。二十五架飞机编成两组俯冲着攻过来。其中一组对城内和城墙进行狂轰滥扫。其他飞机则对来凤山及周边阵地实施猛烈攻击。约十分钟后飞机离去。与此同时,重炮和机枪又开始了猛烈攻击。
在敌人持续两个多小时的猛烈攻势下,城内的我军阵地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炮击后的来凤山笼罩在一片硝烟中,无法看清山体。据联队的西田少尉说,敌人为攻打来凤山,发射的炮弹不下两万发。[[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26页。]
寸希廉回忆:“炮兵将近百门大炮集中轰炸来凤山顶,把来凤山炸成一片焦土。”
傍晚,下起小雨。雨雾中的来凤山在人们的视野中渐渐模糊。寸希廉与观战的村民们默默散去。这一天的来凤山为他们展现的,毫无疑问是一出悲剧。
“一直打到下午4点多钟,还是无功而返,看着从上面抬下来的伤员,老百姓非常痛心。”寸希廉说。
时为军医的董澄庆回忆说:“那天抬下来,只是由我包扎的伤员就有380个。伤兵一来,有些起不来,要去扶他起来,靠在我身上,给他上药包扎。有打到头的,有打到身子的,血淋淋的,我身上从头到脚,到晚上全都被血染红了。那一天也挺难的,380个人就是靠我一双手包扎。”
“七七”事变7周年纪念日,中国远征军对来凤山的第一次总攻失败。陆朝茂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幸免于难,但他那位战前不愿向菩萨磕头的战友,却没能熬过这一天。
“早上打第一线的时候,他没有被打死。前进到了第二线的时候,就是朝前100多米左右吧,到了我们架机枪的地方,他在我的后面,扛着个子弹箱,敌人从碉堡里一枪就把他打中了,打中以后就躺倒了,也不叫也没有说话,就这样打死了。”陆朝茂重复道,“他平时就睡在我的旁边,是个保山人,名字叫李唐。”
7月24日:美国飞机来“倒洋芋”
攻打来凤山的战斗演变为山坡上不分昼夜的拉锯战。
7月16日,来凤山战斗进入第10天。山顶日军阵地前,中国士兵的尸体越堆越高。远征军一次次冲锋,又一次次败退。
老兵何绍从回忆:“那一天人死多了。日本人在山头,(我们的人)都死光了,眼看几十个人滚了下来。”
老兵钏相元回忆:“牺牲的战友脑浆淌一地。虽然我们看不见日本人,但是日本人看得见我们。”
就在这一天,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召开军事会议。据情报显示,来凤山上的日军人数不会超过600人,这位刚刚率领大军翻越高黎贡山的将军搞不懂,为什么眼前这座高度不及高黎贡山三分之一的山头,居然会成为数万远征军将士无法逾越的屏障。
对此,老兵黄友强认为:“日本人是不多,但日本人不怕死,这一点真的厉害。他们甘愿死也不愿投降,觉得一个人起码要换十来二十个才够本。”
老兵周德黎则分析了远征军士兵的弱点:“我们的人太紧张了,日本人的枪法很准,我们的新兵还锻炼不够,打仗时胆子也小。当时补充来的新兵多,一排人中只有六七个老兵,老兵少。”
老兵黄友强直言:“这不就是拿命去拼嘛。中国有的是人。死了100人,又去100人。”
就在7月16日的这次军事会议上,霍揆彰请求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加强空中轰炸,配合远征军地面进攻。
钏相元说:“那时我们攻不上去,停止了战斗,部队叫美国人开飞机来援助。”
1944年7月24日清晨,一阵沉闷的飞机轰鸣声从天空传来。
驻守腾冲城内的吉野孝公,注意到了天空中的变化:
7月24日,敌人重新调整了阵容,发动了第二次总攻。敌人的巡逻机一早便嘈杂地在上空盘旋侦察。五十多架战斗轰炸机的庞大编队,和敌人的地面部队互相配合,俯冲着对周围阵地和城内外我军阵地展开了攻击。[[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28页。]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来了。和顺乡的村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飞机,再次出门观战。
寸可富说:“那一天,我们和顺乡的老人、妇女、小孩,全部出来看飞机。炸弹来的时候,他们就说飞机拉屎。”
寸希廉回忆:“那一天首先是空军的轰炸,盟军轰炸机把那些炮弹一束一束扔下来,扔到了来凤山的山顶上。我们和顺乡人看到那个轰炸场面,把B-29轰炸机叫做‘倒洋芋’的飞机,因为投弹的数量之多,就像我们从箩筐里面倒洋芋。”
除了轰炸,远征军炮兵还用美国援助的新式大口径火炮对来凤山山头进行了地毯式的轰击。光秃秃的来凤山,无法为日军碉堡前的中国步兵提供藏身之所,却也将日军碉堡与工事完全暴露在远征军的火力打击之下。在强大的立体攻势面前,日军为扫清视线而把山上树木砍伐殆尽的行为,成了自作聪明的愚蠢之举。
老兵黄友强如此形容远征军炮火之猛:“后来我们上了来凤山顶,五寸好的地方都没有,左一炮,右一炮,打烂了。”
老兵张元称回忆:“我们的炮打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来凤山。记得来凤山攻下以后,没剩下多少炮弹了。”
轰炸还没有停歇,被日军火力压制多日的中国官兵们开始向已成焦土的来凤山发起冲锋。山下观战的和顺乡村民们发出了欢呼声。
和顺乡村民张孝仲回忆:“大家都忘记了打仗要死人的,都在那里助威,当拉拉队,老太婆和妇女也搬个小凳子到坡上去看打仗,这种事情,在全国战史上恐怕没有过记录。”
战场上,中国官兵们气势如虹。
老兵董澄庆回忆:“那一天攻来凤山,是恶打恶冲。步兵们端着冲锋枪,‘杀’!几百人一起喊,一个山都喊得震动了。”
老兵钏相元说:“日本人不能抬头了,因为我们有美国人的飞机来协助,冲锋上去,就和日本人拼刺刀。”
吉野孝公看到:
作为我主要阵地的来凤山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中几次易手。骁将太田大尉和成合大尉,不断鼓励剩下的二十几名勇士,英勇地反击逼近的五百余名敌军。他们捡起敌人投扔过来尚未爆炸的手榴弹迅速扔了回去。敌人来到近旁,就采用突击的方式,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殊死守卫阵地。[[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28页。]
寸希廉看到:“日本人从战壕里面四个四个冲出来,拼刺刀,嘴里面还说着话,他们的脸看得非常清楚。”
老兵周有富回忆:“我们和日本人拼刺刀,后来枪全部丢了,当时我们有一个姓李的班长,和日本人抱着打。那是一个斜坡山,一会儿这个在底下,一会儿那个在底下。后来有一个叫高峰祥的人,抱起一块大石头,趁日本人在底下的时候把他的头砸烂了。”
经过血腥的肉搏战,中国官兵终于突破设在半山腰的日军阵地。半个多月来一直战斗在最前线的陆朝茂,与战友们冲在了第一线。“我们把一个碉堡攻下来以后,日本人从碉堡里跳出来,跑的跑,滚的滚,当时也打死了几个,有个日本人一直跑,我们就在他的后面拿着枪扫射。我们一开枪,全都打在他的头上,那是一个小军官,他的脑浆都被打出来了。”
来凤山日军的抵抗意志开始瓦解。胜利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中国远征军倾斜。
就在此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老兵周有富回忆:“不知是不是有人把命令听错了,我们自己的飞机炸弹投了下来,把我们的人炸死了100多。”
寸希廉记得:“当时,一队队士兵从山下爬到了山顶,前面铺着一条条白色的布标,这种布标是陆、空、步、炮联络的一种信号,向空中指示敌人的据点和敌我之间的分界线。”老兵李华生说:“部队攻到一处,要把那个符号摆起来,到了另一处,也要把那个符号摆起来,符号摆慢了的话,后面的炮就跟着打过来了。”
由于对远程火力协同战术的不熟练,冲在第一线的中国官兵,在即将到达山顶的最后一刻,遭到了来自友军的误炸,陆朝茂也在其中。“我们以为(美军)飞机飞走了,就冲了上去,后来又来了30架,我们正和日本人打着,结果那飞机就来丢炸弹,扫机枪,机枪倒是没有打到我们,那个炸弹就丢在我们旁边。炸弹炸了以后,掀起来的土把我埋了,还好埋得不太深,只是我的一只眼睛伤了。”
虽然发生了这个意外,但战局至此,中国军队拿下来凤山已经不会有意外。
当天,吉野孝公见到几名从来凤山阵地下来的日军重伤员,满脸是血,奄奄一息,其中一人开口说道:“我们已经没救了。”[[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28页。]
7月28日:升旗仪式上飞来日军炮弹
7月25日,天气晴好,美军轰炸机18架轮番轰炸来凤山。炮兵集中百余门大炮,发射炮弹数千发。中午,步兵三个师从五个方向猛攻山头,工兵的火焰喷射器将敌人的鹿砦和暗堡烧成一片火海。入夜,山上火光熊熊,枪声彻夜不息。敌人从城内派出增援力量,激战通宵。
7月26日,美军B-29轰炸机57架次分4批轰炸来凤山,同时投掷凝固汽油弹。山头烈焰冲天,黑烟蔽日,大火燃烧一天一夜,敌人烧死烧伤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