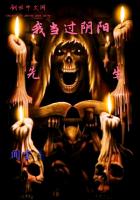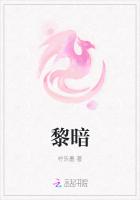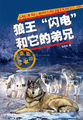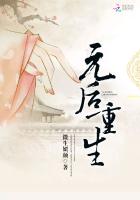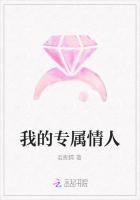8月23日,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接到前线战报:3天时间里,远征军官兵在腾冲城西仅仅推进了15米,城东只推进了10米。面对几乎无处不在的日军狙击手,中国军队不得不躲进房屋,与日军隔墙对峙,并用美式火箭筒与手榴弹,将日军据守的建筑逐个摧毁。双方在废墟里打进打出,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每一堵石墙,都成为血肉相搏的决斗场。
老兵徐有林提到一个细节:“日本人扔了一颗手榴弹过来,也许是它的引信慢了,手榴弹扔过来以后,我们班的一个战士叫吴德一,他把那颗手榴弹又投了过去,投过去以后,他们又把它扔了过来,扔过来以后,我们又扔过去,扔了四五次以后,那颗手榴弹在他们那边爆炸了。”
蒋自芳也提及一个细节:“一个日本人,我们打到了他的脚一枪,他招了招手,意思是把他打死,我们这边就不打,看他怎么办。他就掏出手榴弹来,把引信一拉,炸了以后就滚下去了。”
已经无路可退的日本军人,依然死守阵地。
黄友强记得,在城内一个角落,“那时日本人不多了,只有一两百人了,还是厉害的,只有一只脚或者一只手的伤兵都还拿着枪和你打。”
尹龙举感叹:“打到最后,日本人还是死不投降,他们的精神就是要为天皇效命。后来他们把电话、电报机全部砸碎,在那儿唱国歌,然后再冲出来。”
9月7日,远征军官兵终于肃清腾冲城西的日军,开始合围城东日军残部。日本人感到大势已去。吉野孝公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知谁嘴里嘟哝了一句:‘我们的生命就要在此了结了。’”[[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39页。]
9月10日,远征军官兵发起最后的总攻。吉野孝公回忆:
剩下的守备队兵力有三百五十余名。敌人根本不把兵力很少的我们放在眼里,抱定最后一击的准备,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后,依然是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激烈肉搏中化成了一片血腥的荒野。
……
壮烈得连鬼神都会落泪的腾冲守备战就要结束了。[[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42页。]
9月12日,日军指挥官太田正人大尉给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司令部发了一封电报:
我们已弹尽粮绝。守备队官兵准备在藏重联队长的忌日13日,进行最后一次突击,以发泄自怒江作战以来积压在胸中的愤懑,作为武人的最后一点点缀。我们在敌人强有力的炮火下根本抬不起头,但我们一时一刻也无法忍受敌人的嚣张。请求体谅全体官兵的心情。[[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43页。]
吉野孝公在回忆录中写道:
电报发出后,我们随即焚烧了一四八联队军旗。大尉召集了所有剩下的官兵,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
“腾冲守备队全体官兵浴血奋战死守到现在,已圆满完成了任务。剩下的各位,马上向城外突围,冲进敌阵,杀出一条血路,潜往芒市师团司令部,报告腾冲部队的最后情况。以后的一切责任由太田大尉担当。”
发布完命令,大尉和剩下的十几名近卫军勇士冲入了敌阵。[[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43页。]
布鲁威尔·赖文思的日记里记下了这场惨烈战役的尾声:
每天我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腐物在腾冲城这个巨大的“尸体”上蠕动蔓延。一间房屋一间房屋、一个坑道一个坑道,中国兵在搜寻、毁灭、杀戮。每一幢建筑,每一个生物都遭到了空前彻底的毁灭。死亡的波涛冲刷洗礼着这座古城,腾冲死了。
死城:“我讨厌战争!”
1944年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日军据守的最后一处房屋被炸毁,自8月2日打响的腾冲县城攻防战,在一片硝烟火海中落下帷幕。
中国远征军以9000多名官兵英勇捐躯(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从强渡怒江至攻克腾冲城,伤亡军官1234员、士兵17275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3页。])的代价,收复了已成一片废墟的腾冲。这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座日军设防城市。
日军腾冲守备队3000余人最终被全歼,连同随军慰安妇在内,仅有53人被俘。“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它们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
受伤的吉野孝公在突围过程中被俘。后来,他见到了一位远征军的高级军官,这位自称毕业于日本军校的中国将军用流畅的日语对他说:“腾冲守备队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们来说,也真是可怜。……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将军眼里闪着光说:“我讨厌战争!”[[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69页。]
吉野孝公的战友们没有他这么幸运。老兵张体留记得,打扫战场时,“从拐角楼跑出五个日本人投降,过来的那日本人还写字,写什么‘大日本’,后来打了他两个耳光,就不敢再写‘大日本’,又写他当兵三年,他家里面还有什么人,还拿出相片来,上面有他老爹、老妈、媳妇,还有个年纪很小的女儿。说老实话,当时年轻,看到日本人来投降,眼睛已经打红了,因为家乡人被打死太多了,战友也被打死太多了,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一排冲锋枪把他们都打死了。”
寸希廉回忆:“有两个日军俘虏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副营长让我妈妈做点东西给他们吃,我妈妈说:‘我们家在缅甸遭受那么大的损失,这里的家又一次次地被他们抢劫光,我还能给他们做什么吃?’”
在困守腾冲的日军当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家乡沦陷13年、被日军胁迫来的中国东北人。
老兵邵曰校说:“敌人有些兵说:‘我们是东北的,我们是中国人,是被逼着来的,我们当初被抓来,是10家保1个,如果打仗的时候我们跑掉了,那么这10家人就死光了。’讲得很可怜。”
老兵董澄庆回忆:“东北人全是高鼻子,人也高,他们和日本人在一起不能讲中国话,只能讲日本话,他们说,中国人之间讲中国话都不行,一讲就要枪毙。”
在中日两方的战史里,均未提到过这些在腾冲与同胞作战的中国东北籍军人。也许,从他们穿上日本军装的那一刻起,有关他们的故事,就注定将被所有人遗忘。
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的李坤拔忘不了战后腾冲城的惨状。“攻完城三天以后就让老百姓参观。真的是战场,非常惨,腿挂在树上,手挂在墙上,底下全部是血,真让人害怕。我记得有一个四川人,他在棺材里头骂,我就跑去问我父亲,他为什么要骂。我父亲告诉我,他还没死,就把他放进棺材里,美国人检查过了,他全身都烂了,没有办法医了,只是心脏还在动,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人很惨很惨。”
寸希廉眼中战后的腾冲城,一片瓦砾,没有一栋完好的房子,满目凄凉。“一个坑里边有七八个被杀死的日军军妓,还有一个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嘴里还在叽叽咕咕说着话。”
预备第二师老兵李忠用“瓦全是碎瓦、树全都只有树枝没有叶子”来描述这座死城。
战役结束后,根据师部命令,预备第二师所有腾冲籍官兵获准请假回家看看。对于这些家乡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官兵们来说,这一看似体贴的命令,却令人感到一丝残酷。更残酷的是,他们的很多同乡战友,连近在咫尺的家,都没能看上最后一眼。
预备第二师老兵谢大蕃说:“我们团长在电话上跟第六军军长说,原来我的兵,伙夫送饭有100多挑,现在如果送饭,没人提,他说哭了。一个团只剩十二三个人,还连团长都凑数了。”
“所有在城里边死了的日本人,挖了一个坑,全都埋在里边。解放以后,农民还去挖那些骨头土来做肥料。”预备第二师老兵李会映回忆,“在和顺开追悼会的时候,师长说,我们预备二师上火线时是一万多人,现在只有七八百人,那么多的人去哪里了?才说完就哭了。全场的那些机关单位人员、学校的老师学生全都哭了。”
李会映讲了一个带点奇幻色彩的故事:“打完仗,晚上的时候,只听见这些兵——日本兵,中国兵——在街上走,数一二三,闹得不得了,吓得老百姓不敢出来,所以腾冲人说要超度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吵下去了,所以就建了国殇墓园。”
1946年,吉野孝公和众多被遣返战俘一起回到日本。多年后,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写道:
年轻人在看中越纷争的新闻画面时,只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说:“我们真想在这种壮观的战场上,亲身体验一下战斗的滋味,哪怕一次也行啊!”当然这只是一群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的话语,但在残酷的战场上,并非每个人都能幸免于死。我想告诉他们,在子弹纷飞的战场上,每一颗子弹时刻都会夺去人的性命,而生命却只有一次。[[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3~4页。]
“人都死光了,还叫打龙陵”
1944年9月中旬的一天,第五军第二〇〇师接到了一项紧急调令。
时为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的杨光荣回忆:“那时第二〇〇师在昆明附近驻扎,上面让第五军赶紧派一师去攻打龙陵,就派了第二〇〇师,我连奉命配属第二〇〇师参加战斗。”
龙陵位于云南西部,北连腾冲,东抵松山,滇缅公路在此穿境而过。1944年9月7日,中国军队攻克松山。9月14日腾冲光复后,龙陵这座中缅边境上的小城,成为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的下一个目标。
杨光荣说:“松山过去就是龙陵,龙陵过去就是芒市,芒市有日本兵的司令部。日军失守松山以后,龙陵必须守得坚固。腾冲打下来,再打,没劲了,所以那时候卫立煌一看,部队已经疲了,打不下去,赶紧调援兵吧。”
9月下旬,从各地抽调而来的支援部队陆续向龙陵集中,刚刚经历腾冲战役洗礼的预备第二师也在其中。
董灯玉回忆:“上面又来个命令,说龙陵那边没有收复,又要调预备第二师去那里打日本人。我们的师长和上级吵,说我们预备二师人都没有了,死光了,还叫去打龙陵。不行,非走不可。师长虽然顶着闹,最后还是接受了,回来就说哪几个部队准备到龙陵打仗。”
9月底,10万中国军队在龙陵城外集结完毕。与他们对抗的,是在日本陆军中有着“龙兵团”之称的第五十六师团主力。第五十六师团是日军精锐,士兵来自日本九州的久米留山区,山民或矿工出身居多,也善于挖掘矿井式的地洞坑道、防御工事,作战特别强悍。
滇西大反攻即将迎来最后的血战。
腾冲战役后留在当地的一个日本兵
据《大国之魂》记载:驻守腾冲的日军共有17人活着回到日本。其中5人系受伤被俘,1人投降,其余突围。一个叫清太郎的上等兵乘夜逃脱出城,黑暗中不辨方向,一头钻进高黎贡山区的原始森林。迷路三天,幸逢一位善良的傈僳族老猎人收留了他,从此清太郎就在恩人山寨里定居下来。天长日久,日本人同当地人打成一片,生男育女,成为这个原始部落里一位外籍成员。1970年,傈僳山寨成立人民公社,喧天的锣鼓突然惊醒了这个年逾半百的日本人,经过一番曲折,清太郎离开山寨归国。[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333页。]
八年抗战中日军仅有的两次烧军旗
自1874年起,凡日军新编成的步兵、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由于军旗仅为建制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才拥有,所以也称为联队旗。按日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中地位重要,要挑选联队中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正因如此,二战中,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日本军旗,但是都未能如愿。因为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奉烧军旗。不管遭遇怎样的败仗,日军都有烧掉军旗而后自杀的时间。在八年抗战中,日军仅在松山和腾冲的两次“玉碎”战中烧掉了两面军旗,分别属于第一一三联队和第一四八联队。[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0~221页。]
龙战于野
亲历者
胡正昌——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八十七师警卫排排长王德五——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一营一连连长杨光荣——时为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
杨鸿恩——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陈宝文——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作战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