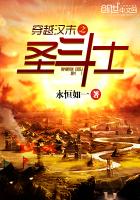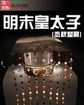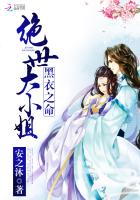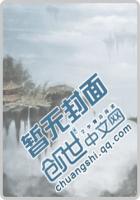熊世超——时为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唐玉林——时为中国远征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重机枪手付心德——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二野战医院少校医务主任朱锡纯——时为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不知是否有人知道,这句话其实是《周易》里的一条凶爻:“喻人事,则为上下交战,至于死伤流血的情形。”实际上,这集片子里出现的所有四句与龙有关的爻,都是凶爻。
这是6集“滇缅系列”的最后一集。龙陵,字面意思似乎可以理解为“龙之陵墓”——当然,龙陵县名字的实际来历未必如此——远征军三进二出,血战近半年,最终将有着“龙兵团”之称的日军五十六师团一部消灭于此。滇西反攻由此胜局已定。
三战龙陵,能够从前两次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如今已寥寥无几。但在我看来,龙陵之战最富有戏剧性的,恰恰是这前两次战斗。短短几个月时间,小小的龙陵四度易手。远征军连续两次,在胜利前的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战场的无常与日军的狡诈尽显于此。毫无疑问,胡正昌老人是本集能够成片的关键人物。
见到胡老,是在成都近郊一家僻静的养老院里。在我们到达前,老人早早起床,腰杆笔直地坐在房门前等候。与我们同行的胡老家人告诉我,这是第一次有媒体想电视采访胡正昌老人。采访刚开始时,摄像机前的胡老先生非常紧张,整个身体几乎都僵直着一动不动。面对这种情形,我不得不刻意打乱事先拟订的采访提纲。完全忽视时间顺序,用东拉西扯的方式让这位年近九旬的老兵放松下来。
终于,老人僵硬的背脊逐渐靠在了椅背上,语音也渐渐高亢了起来。我知道,此时此刻,才是老人回忆的真正开始。
回忆中,胡正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神经麻木了。”的确,面对死人堆中的爬行与密如雨点的子弹,“恐惧”似乎也成了一件无暇顾及的事情。胡老先生是我所采访过的老兵中,惟一一个详细描述督战队的人。身为排长的他,至今仍记得自己在督战队的枪口下,带领战士炸毁日军地堡的详尽过程。但当我数次问起:“您指派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在炸碉堡时牺牲的多吗?”老人却几次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当采访结束,摄像机关机后,这位当年只有22岁的年轻排长,突然轻轻对我说了一句:“我和那些战士感情很好的……”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龙陵战斗结束后,胡正昌再也没有回过龙陵。1944年夏季那座地狱般的龙陵城,在老人的记忆中永远定格。抗战结束后,带着左臂上那个终身的伤疤,由排长提升为连长的胡正昌跟着部队去了东北。他们出关后的第一个驻扎地很有名——四平。
临别之时,老兵胡正昌站在房门口目送我们离去,腰杆笔直,一如我们刚来时的样子。车子开动后很长一段时间,车上所有人都默然无语。这是年近九旬的胡正昌老人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第一次……编导刘元
1944年6月10日深夜,滇西龙陵县城外13公里的黄草坝,中国远征军第八十七师警卫排排长胡正昌在师部指挥所门口执勤。指挥所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那个时候,就是打龙陵。黄草坝是在松山与龙陵之间的一个地方,(日本人)去晚了,(我们)把龙陵到松山的那条公路切断了。”胡正昌回忆说。他是四川成都人,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时年22岁。
一个从前线打来的电话,引起了师部所有人的注意。
胡正昌回忆:“一个团长给师长打电话说,他们已经进入城区了。师长马上报告军长。军长接到这个电话好高兴,说:‘好,已经攻下龙陵了,好!’”
龙陵四面环山,中为盆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侵占龙陵的两年间,以县城为核心,以环山为依托,构筑了由据点群组成的防御体系,并储有数月的生活、作战物资。
在中国远征军分路进击松山、腾冲的同时,负责右翼攻击任务的第十一集团军所属第二军和第七十一军精锐部队,绕过松山侧翼直插龙陵。
龙陵本由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的第三大队防守,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开始渡江进攻时,该大队被调到腾冲,龙陵仅有少数留守人员。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渡江后,第五十六师团急调刚转隶其序列的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的第二大队增援龙陵。至6月5日,远征军开始进攻龙陵外围阵地时,龙陵日军仅有1000人左右。[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1页。]
6月6日,中国远征军兵分三路向驻守龙陵县城一线的日军发起进攻,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截断了龙陵与芒市之间的公路联系,并肃清了龙陵城外大部分据点中的日军。
6月8日,远征军向日军重兵防御的龙陵东南郊阵地发起进攻。到6月10日,龙陵城郊的所有高地都被远征军攻克,残余日军只得退回城内坚固工事中负隅顽抗。
此时,松山战役已经打响。日本人深知,如果松山、腾冲的战略支撑点龙陵失守,整个滇西战局将难以收拾。
龙陵战场,有人想起《易经》所言:“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一战龙陵:得而复失
6月10日深夜,中国远征军收复龙陵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重庆市民为此燃放了鞭炮。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对胜利却不知情。
卫立煌之子卫道然回忆:“第二天早上,蒋介石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昨天晚上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来电话,说他打下来龙陵了,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父亲说:‘我不知道呀,他没向我报告。’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我父亲觉得奇怪,马上给宋希濂打电话,打不通。这也奇怪,怎么会电话不通呢?”
几乎就在同时,远征军第八十七师师部又接到一个来自前线的电话。
“电话说日本人反攻龙陵以后,部队站不住脚,要退出。”胡正昌说,“从腾冲来了日军一个联队,他们增援以后,攻进龙陵城的两个团再不出去就完了,就退回来了。很快,攻城的两个师都站不住脚了。”
6月15日,从腾冲、芒市两地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在城内守军的接应下,向已经攻入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发动猛烈反攻。
时任中国远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一营一连连长的王德五回忆:“总冲锋开始后,我们营打掉了日本人的仓库,里面尽是军大衣和军靴,料子质量比我们的好几倍。一些弟兄以为龙陵就此拿下,于是扛起这些战利品就想占为己有。不料一会儿,漫山遍野的日本人反攻过来,我们抵挡不过,不仅退出城来,而且死伤大半,军大衣、军靴扔得到处都是。”
时任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的杨鸿恩认为日军先前是假装失败。他说:“等他们反扑过来,国军就吃亏了,伤亡惨重。”
“宋希濂给我父亲来电话:‘报告长官,现在日军的增援部队来了,这仗我吃不消了,这个责任我负不了。’”卫道然说。
6月16日,日军反攻部队突破远征军外围防线,一头冲进了龙陵城,将远征军第七十一军主力部队拦腰截断。腹背受敌的第八十七师伤亡惨重。迫于形势,远征军退到城郊一线。
身处师部的胡正昌虽然不太清楚前线的具体战况,但退下来的军官们脸上的惊惧之色,让他感受到了战局的险恶。“来了两个团长,灰溜溜的。师长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搞的?他们说,站不住脚啊。师长说,你们谎报军情了,不应该预先报告你们攻占龙陵了。”
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作战参谋的陈宝文回忆:“那时候老蒋打电话来说,你们已经得到了龙陵,为什么不守住?必须反攻龙陵,完全攻克。如果你们继续放弃,要军法从事。”蒋介石电令:“饬长官部追查放弃龙陵系何人下令。”[张组成:《龙陵抗日战争综述》,政协云南省龙陵县委员会编《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23页。]
胡正昌记得:“师长张绍勋急了,开枪自杀。我当时就在他身边,他拿着枪打胸部,一枪打偏了,没死。”
陈宝文说:“宋希濓去看张绍勋,把他送到后方去医治,让第八十八师副师长黄炎接管第八十七师,同时又调特务连到勐冒村的大桥上架起机关枪,防止部队向后退。”
宋希濂把首战失利的部分原因归结于“第二十集团军方面进展迟缓,未能同时进出腾冲附近,致腾敌抽出兵力二千余,附大野山炮,用汽车输送南下增援”,要求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先行进出龙陵以北地区。
6月22日,蒋介石急电卫立煌、宋希濂和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严厉指出:龙陵得而复失,“实有损国军荣誉”,远征军应积极进攻,排除万难,“如有作战不力,着由卫长官依法严惩”。当天,卫立煌调整作战部署,令第十一集团军集结主力,击溃当面敌之攻势;第二十集团军主力保持于左翼,迅速南下,攻击腾冲而占领之。[臧运祜:《论滇西缅北会战中的中国远征军及其战术》;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页。]
6月28日,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到达龙陵增援,配属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六师、荣一师各一个团向龙陵外围日军发动进攻。战至7月6日,日军逐次退至龙陵城区及近郊,远征军乘势将战线推进至龙陵附近。由于极需整补,远征军暂停攻击,在对峙中准备再度攻城。[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3页。]
二战龙陵:功亏一篑
7月13日拂晓,倾盆大雨,胡正昌和手下的战士们匆匆吃着早饭。“我们吃的是稀饭,饭桶里落了雨水,半桶米,半桶水,舀起来就吃了,没有办法。后来我们见到日本人的仓库里面都是罐头,他们吃得很好。”
胡正昌看到,不远之外,雨雾中的龙陵城透现出海市蜃楼般诡异的轮廓。
当天,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集结了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师、新编第三十九师的3万兵力,从东、北、南三面向龙陵县城一带的日军据点发起第二次围攻。一战龙陵时由于过早发布胜利消息而在英美盟军前丢了面子的蒋介石,严令部队必须尽快拿下龙陵。
胡正昌回忆:“陈明仁来了,对师部的人说:‘让师里全部人给我打龙陵,要是攻不下来,你们别来见我。’师里所有直属部队,都打到第一线了,警卫排也要上,警卫排是美式装备。非要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全部枪毙,这是军令。那个时候命令很严的。”
从没真正上过火线的胡正昌,带着警卫排全部32个弟兄踏上战场。在他眼前,“遍地死尸,日本兵、中国兵,都泡在雨水里”。他记得,那段时间龙陵天天下雨。“我们爬在尸体上进城,神经都麻木了。后退就枪毙,军长带着督战的上来了,你不上,后边打你,你只有前进啊!”
前面是日本人密集的机枪火力,后面是督战队冷酷的枪口,胡正昌带着弟兄们在死人堆里匍匐前进。“臭!死尸那个味道最臭!子弹那个密集啊,在头上飞来飞去,跟放爆竹差不多。一颗两颗子弹飞过来,还怕,子弹都成片了,已经无所谓了。”
经过连日激战,远征军依靠兵力上的绝对优势,逐渐夺回了龙陵城外的各个重要据点,重新将日军逼回龙陵城区。据远征军情报部门估计,此时据守龙陵县城的日军残余兵力,已减少至2500人左右。日军依靠城内的一座座地堡,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日本人的拼命让胡正昌感慨:“日军伤兵头上包裹着绷带,还端着刺刀跟你拼。”
无处不在的日军火力点前,胡正昌那些朝夕相处的弟兄们一个个倒下了。“一想起那个场面,确实寒心啊!”
胡正昌说:“敌人的工事是连环堡,一个接一个。大炮不行。大炮简直铺天盖地,总起不到好作用,就爆破筒打碉堡是最起作用的。我是排长,就对手下一个弟兄说,你拿爆破筒去炸碉堡,我掩护你。我拿冲锋枪打,打得日本人不敢抬头,他马上冲上去,爆破筒到那个碉堡里头就爆炸了。”
胡正昌记得,一些碉堡内有慰安妇。“把那个碉堡打开以后,男的女的都有,包括包扎起来的伤员,死不投降啊。”
到8月中旬,经过一个月的血战,远征军将龙陵城内的日军逼退至城南一角。8月23日傍晚,日军龙陵守备队队长小室钟太郎向第五十六师团发去电报:“龙陵连日来日夜遭受优势之敌空、地协同猛攻,即使奋战,也只能再坚持两天。”
8月24日,远征军再次发起攻击,困守城南的日军残部被逼向绝境。但此时,卫立煌却疑虑起来——几天前,一直在缅甸北部活动的日军第二师团主力1万余人,突然从远征军情报部门的追踪中神秘消失。有了一战龙陵得而复失的教训,卫立煌警惕性很高。
卫道然说:“这个第二师团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这不得了。我父亲就问美军,美军的飞机侦察很厉害的,他们说也没有发现。这很奇怪。”
卫立煌命令情报部门仔细分析近期内滇缅公路南段的所有航空照片。分析之后,一个可怕的结果浮现了出来。“头天的照片上明明能看见一个小树丛,但是第二天的照片上,这个树丛没有了,还有的树丛前移了,那肯定不对头,那就是援军。日军车辆都带着防空网,天上飞机一响,就罩上防空网,变成小树丛。看照片,他们已经到芒市附近了。”卫道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