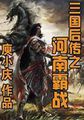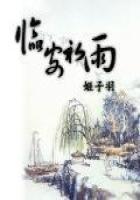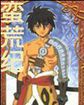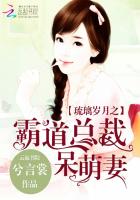7月7日,日伪庆祝会召开后,抗团成员皆利用社会关系进入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李振英发现现场日伪警戒严密,便决定改在会场外下手。而此时,纪采凤、朱慧珍等女学生开始悄悄向参加庆祝会的中国人递发传单。人们看到这些小姑娘衣着时髦、举止不俗,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几乎都是心照不宣,将宣传品悄悄揣在身上,并无一人喧哗或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俨然两个世界。刺杀吴菊痴后,冯运修没有停车,按照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迅速发出“得手”信号,通知叶于良和刘永康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本来,抗团成员的行踪仍然有可能像之前的行动一样,凭借他们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灵通的内部消息,消失于无形。但这次刺杀吴菊痴的行动影响力巨大,1940年8月上中旬,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决定,采取搜捕行动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展开了在北平天津两地同时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八月大逮捕”。这次行动中,抗团成员40余人被捕,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组织也遭到重创。北平抗团负责人李振英,叶于良行动搭档刘永康,递发传单的孟庆时、纪采凤(一说纪凤彩),介绍叶于良加入抗团的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
关于冯运修牺牲的过程,作家萨苏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
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发觉有变,立即起床取枪走出卧室,携带抗团重要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日军破门而入,捕获了冯运修的父亲和弟弟,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与特务们僵持良久。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袁规,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冯运修枪法极好,一枪打出,子弹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之后日伪特务纷纷爬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最终,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进行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据说,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
1940年8月的大搜捕后,抗团遭到严重破坏。大家被送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特课,经伪警察局特务课、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狮子胡同的炮局多次过堂,判决后押往位于雍和宫旁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地人犯临时收容所。因为集体关押,叶老认识了很多抗团战友,他们中除少数人被家庭营救,大部分人在监狱中一直关押到1945年抗战胜利。
出生于1922年的叶于良,1939年加入抗团时,只有17岁。1940年,他已经考上了辅仁大学,但被捕后他被关押在监狱,直至1945年出狱,再无机会读大学。可以说,他错过了生命中最为华彩的岁月。而其他被捕抗团成员的命运,与此相仿。
出狱后叶老被安排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工作,因不喜欢军警工作,一年后辞职到财政部福建区货物税局,不久又转至武汉金融管理局直到解放。解放后归口金融管理处,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劳模及中南区代表。“肃反运动”开始,老人没能幸免,抗团的经历成为劳动改造的理由,至1975年经特赦后回到北京,并在服装公司退休。
从17岁加入抗团,到18岁刺杀汉奸的一年时间,换来的,是18岁到23岁的5年牢狱经历;更换来了,29岁被“肃反”,53岁回家的24年劳改生涯。如今已是89岁的叶老,如何计算人生的实际长度,如何定义“青春”这个字眼呢?
我们无法探知叶老那24年是如何度过的。我在想,比起他,19岁身死的冯运修,显得那么幸福。
(文中资料参考了作家萨苏的文章,在此表示感谢!)编导李戎
1940年年初的一天,北平新新大戏院灯火通明,一派热闹。戏快要开演了。这一场是名角言菊朋父女同台演戏,票友们期待已久。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包下的二楼前排还是空的。两个坐在一楼前排的小伙子,不时偷偷回头望向二楼包厢。
“那时候我们听见人声一片嘈杂,回头一看,川岛芳子来了,戴着傻瓜帽和墨镜,穿着长袍马褂,还是男装,后面跟着十几个人,簇拥她上楼。进二楼前排后,她坐在前排当中。”两个小伙子之一的叶于良,70余年后仍对当时的细节记忆犹新。
叶于良和同伴密切注意着川岛芳子的动向,手枪藏在腋下。
“我们准备等散了戏,看她往哪儿去。”叶于良说。
没想到,戏开演不久,川岛芳子却起身离开了。“也就半个钟头,稀里哗啦又是一片杂乱的声音,我回头一看,不好,他们一群人走了。我们就追下去,看到她坐着汽车,呼呼跑了,就没干成。”
这一年,叶于良18岁,他的同伴李振英21岁,他们都是北平抗日杀奸团的成员。
这次刺杀川岛芳子,他们没有机会下手。此后,这样的遗憾乃至失手也经常发生,但他们不气馁,他们相信,一旦成功,就能名垂青史。
伪满总理孙子孙女入了杀奸团
20世纪30年代末,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对平民百姓来说,除了走过街头的成队日本士兵,日子与以前没有太大不同。当然,心情不一样——现在,是亡国奴了。
不时传来的汉奸被刺消息,让人们得到慰藉。
叶于良回忆:“好几次暗杀活动都让汉奸震惊,比如王克敏曾经被刺杀过。鲁迅的弟弟——汉奸周作人也在1939年元旦遇刺,那时候北平抗日杀奸团还没有成立。结果子弹打在衣服铜扣子上,没有打穿,他没死,受了一惊。”
有研究者指出:“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出于对周作人曾经的深刻崇敬,李如鹏枪打得不是很准。”[李远江:《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九死一生后成反革命》,《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8期。]
这个“抗团”,也就是叶于良口中的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是“七七”事变后不久,一些爱国青年在天津自发组成的民间抗日团体,后来发展到北平。抗日杀奸团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最初成员来自平津几所著名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年-1940年间为高潮。[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加入抗日杀奸团的不乏社会名流子弟,如孙连仲将军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君,宋哲元将军的女儿宋景宪,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等。[李远江:《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九死一生后成反革命》,《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8期。]“后来郭沫若住的什刹海那个大房子,原来是乐家的,那时候乐倩文就住那儿。”叶于良说,“还有魏文昭、魏文彦,开滦煤矿总工程师的两个女儿。”很多抗团成员来自教会学校,“那会儿能够上得起教会学校的一般家境都不错”。
作家萨苏分析说:“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和孙女郑昆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郑孝胥的孙子和孙女都在北平念书,一个在育英中学,一个在贝满中学。那时我常到他们家去,因为我们沾点亲戚关系,我的姨是郑孝胥的儿媳妇。”叶于良说。
串门时,在和郑统万的闲聊当中,叶于良听说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抗日组织。“谈起抗日,他说,有抗日的组织,你敢不敢参加?一说敢不敢抗日,还能说不敢吗?当然是敢啊。他就说,那我给你介绍去。就把我介绍给李振英,那会儿他是北平抗日杀奸团团长。”
神秘的地下抗日团体,通过可靠成员的介绍,接纳新成员的加入。1939年的一天,在中山公园,叶于良见到了李振英。“他给我讲杀奸团的任务,包括杀汉奸、搜情报、爆破日本人的设施。”
此时,叶于良上高中一年级,李振英上大学一年级。在李振英的带领下,叶于良参加了一个简单的宣誓仪式。
叶于良回忆:“一张小纸上写着誓词。誓词我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还有一个‘团训’,好像是‘遵守团的纪律,保守秘密,如有违反原则,受严厉制裁’,大意是这样。宣誓完了签字,签字完了就烧了,这东西不能存,存下来,将来万一被破获了怎么办?”
看着一纸誓词在火中燃尽,叶于良感觉兴奋多一些,“觉得这也是光荣的,不能到内地去参加抗日,在这里能够抗日,也是了了一个心愿吧。没参加抗日杀奸团的时候,我们哥俩就不想上敌伪的大学。”他说,“当然这是一件难免会牺牲性命的事,必须要有这种准备,如果被抓住了,只有牺牲。也不太害怕,反正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人逮着,就算被逮着了,是为国捐躯,是光荣的。”
马路上刺杀汉奸吴菊痴
开始接受刺杀训练的叶于良感觉到,成为一个冷峻杀手的同时,单纯的少年时代已经远去。
叶于良回忆:“后来李振英看我抗日热情比较高,问我敢不敢行动,我说,‘敢呢。’‘行动就要杀人的呢。’‘行,敢。’他把手枪拿来,告诉我怎么拆,怎么擦,怎么使。小时候玩的只是玩具,现在是真家伙了,所以觉得挺新鲜的,就拆了擦,擦完再安上,学会瞄准、射击。那时候我们没有爆破材料,要自己做,我们曾试过拿汽油或者酒、酒精,泼在日本商店里头,然后点火,试验了几回,点不着。结果就想办法弄材料,从天津弄来。”
在磨练中等待,直到1940年7月7日。这一天是国家蒙耻三年的日子,也是杀奸儆敌的日子。这次的目标,名叫吴菊痴,是北平《新民报》社长兼总编。
叶于良说:“当时北平有两份主要报纸,一份是管翼贤主编的《小实报》,另外一份就是《新民报》。”《新民报》1938年1月创刊,是华北伪政权机关报,鼓吹中日亲善,为日本侵略者粉饰太平。该报总编吴菊痴是一个甘愿为日本人充当舆论吹鼓手的汉奸文人。
叶于良回忆:“7月7号那天,日本人庆祝所谓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在中山公园的社稷坛搞庆祝活动,组织了好多人去,包括吴菊痴在内的几个汉奸在那儿大肆吹捧日本皇军,痛骂爱国军民。当时李振英就跟我说,我们带着枪去,到那儿刺杀吴菊痴。我们到了社稷坛,就在台下四处转,观察动静。”
在人群中,叶于良看到李振英身边多了两个陌生的面孔。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这两人的名字分别是刘永康、冯运修。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一书中如此描写冯运修: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