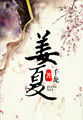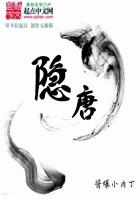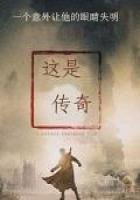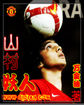据叶于良回忆:“那时候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就是互相不认识。在社稷坛,我不知道他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但知道他是抗日杀奸团的,因为他跟李振英在一块儿。他看见我跟李振英在一块儿,也知道我们都是同志。”
台上,吴菊痴正声嘶力竭地演讲,台下的冯运修忽然将手伸向腋下的手枪。
“冯运修跟我说:‘咱们上去就把他打死算了。’但他也犹豫,又说:‘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干掉他?’李振英说:‘不行,不行。这里边有多少特务,你现在一动手,咱们谁都跑不了,让人家把咱们消灭了。还得找偏僻地方下手,保险。’我们就等到他们散会。散会了以后,吴菊痴他们就坐着黄包车往南走,我们就跟着去了。”叶于良说。
据叶于良回忆:李振英和冯运修骑上自行车,耐心地跟在吴菊痴的黄包车后,一直跟到石头胡同同和轩饭庄。在那里,评剧演员白玉霜,正在等待吴菊痴赴宴。“吴菊痴到那里不久,不到一个钟头吧,出来了,还是坐黄包车,从李铁拐斜街穿出去了。李振英跟冯运修两人也跟下去。”
此时,李振英、冯运修等人从到社稷坛算起,已经苦等了几个小时,眼看着黄包车一路接近《新民报》总部,再不动手,机会将一去不返。
叶于良回忆:“到新华门外,那时候师范大学在那儿,距离师范大学很近的时候,正赶上有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的,声音挺响。”
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终于出现。冯运修看看周围没人注意,猛蹬两步,接近吴菊痴的黄包车。
叶于良回忆:“冯运修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连开两枪,当时就死了。当时现场的声音非常嘈杂,所以没人听到枪声,好像连车夫都没什么察觉似的。”
冯运修射击后没有停车,和李振英迅速离开现场。吴菊痴的车夫拉出去很远,才发现吴已经毙命。[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李振英派人通知刘永康和我,说:‘你们撤吧,现在他们马上要戒严了,不然就跑不掉了。’我们就撤了。”叶于良说。
成人礼:战胜初次杀人下不了手的迟疑
同样的年代,另一些年轻人,走着一条相似的道路。1938年的一天,山东少年郑需凡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第三年,他已经是山东纵队政治部锄奸部的组长。这年,他跟叶于良一样,只有18岁。
1941年,日军在鲁中地区大“扫荡”。郑需凡回忆说,这是最残酷的一次。“日本人突然包围了马牧池的村子,把我们的伤兵打死了,还放了毒气。村村有日本人,杀老百姓。他们杀了人,不是埋了,把尸体吊起来,叫大家看,叫嚣‘谁敢反对皇军?’”
为了完成锄奸任务,郑需凡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青帮分子,学黑话、喝酒、赌钱,常常与汉奸和青帮头子混在一起。当日军“扫荡”形势严峻时,纵队机关离开了根据地中心区,锄奸部在马牧池地区留下郑需凡等5人坚持斗争。
扮成黑道人物的郑需凡代号为“彪”:“郑彪,彪子,虎字三撇就是彪。其他人的代号是龙、虎、豹等。当时如果杀了坏人,贴上代号,就知道是谁杀的。我们不能待在同一个地方,互相都找不着,就靠这个传递信息。”
据郑需凡回忆:他从当地老百姓口中听到一个伪村长的劣迹,人们谈起他,无不咬牙切齿。“他们说这个村子死的人太多,伪村长贼坏,给日本人干这个干那个。经过好几天的反复调查,证实了。我就去把他引出来。我们可以晚上混进村里头去。我找到他,说是有事,就把他引出来了。”
村外,郑需凡押着伪村长,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处理他。此时,不远处出现了一队人马。“正好遇到我们的武工队。凑一块儿,他们说也想来抓这个人,说这人太坏了。巧就巧在这儿。”
郑需凡回忆:武工队决定处决伪村长。“枪毙他,会暴露目标,一打枪,日本人都上来了。最后决定拿刀砍。他们中的一个人就对我讲:‘你是锄奸部的,会杀人,你来杀。’就给我把刀。”
武工队的人不知道,刚刚成年的郑需凡,此前从来没有杀过人。
“杀人我倒是看过,但自己真没杀过人。”郑需凡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却下不了手。“一面往山上走,一面在心里数落他的罪状,他干的坏事,鼓励自己啊。怕倒不怕,但总觉得他也是个人啊,拿刀杀还真不行。也非常恨他,觉得他该杀,欸,但是怎么就是不行!”
郑需凡手里握着刀,迟迟无法动手。
武工队的人急了。“他们告诉我,踢倒他,看他挺脖子,就拿刀砍。我练过武术,刀法还不错,这时候怎么那么不中用!一刀砍到他背上,他哇哇叫,呵呵。所以说,我是干好事的时候,老干成坏事。只好抬脚踢他,他跪下了……武工队几个人看着我说:‘我以为你们锄奸部的会杀人,你怎么这样杀法?’”
伪村长到底还是被郑需凡砍死了,尸体上被贴了一张纸,上面有个“彪”字。郑需凡体会到手刃汉奸的快感,也体会到一个杀手肩上担子的沉重。
1942年,与叶于良、郑需凡同龄的张晋,从河北邢台“抗大”毕业。在一次日军扫荡突围战中,他的右手臂关节被打断,左胸和左肺受伤,亲眼目睹两名战友被日本兵用石头砸死,自己也被鬼子砸伤了头部,奄奄一息。死里逃生的张晋,康复后任工兵连长,活动于河北省武安县。
张晋记得,当地有个山口叫南大社,过了南大社以后,路上有敌人的一个坐探。“名字叫宋白妮,二十来岁的姑娘。她和我们一个侦察班长,姓朱,有乱七八糟的关系,和东边苏村的伪军也乱七八糟,是这么个破货。我们的人,根据地向敌占区去的、敌占区向根据地去的过往人员,她一发现就报告给敌人。她有她的一套联络信号,用手电筒,晚上联络。我们要想回到‘敌战区’,这个人必须除掉。”
对于站在敌人阵营的这个年轻女人,张晋说,自己也有过迟疑,但他说服自己要果断。“死在她手里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因为她不是直接杀人,她一报告敌人,就把我们的人逮捕起来了,有的杀了,有的关了,所以这人比公开的敌人更可恶,更可恨,危害更大。”
张晋下了决心。杀奸的过程,比郑需凡更麻利。“一到那村,先进到她家把她抓出来,带到村边。村南有个干涸的河沟,在那地方用刺刀刺死的,因为四面都是敌人,我不敢开枪。”
战火纷飞之时,手刃汉奸,是这些少年特别的成人礼。他们战胜了自己曾经的片刻迟疑,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真正的战士。
“兄弟九个,死我一个没关系”
抗日杀奸团的杀奸行动一个接一个。
1938年12月27日,祝宗梁、孙湘德、孙若愚刺杀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成功。次年1月11日,天津汉奸为王竹林举行葬礼,当棺材行至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引爆,一人死亡,三人重伤。
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国影片《为国干城》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
1940年7月18日,北平前门劈柴胡同,李振英和刘永康、孟庆石联手暗杀伪北京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同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总务处处长俞大纯被刘永康、叶于良枪杀,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被“抗团”成员乱枪打死。[李远江:《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九死一生后成反革命》,《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8期。]
头顶悬了一柄正义之剑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每有汉奸被杀,报上大肆宣扬,汉奸当然害怕。大点的汉奸都配备保镖了,出门都有警车跟着。那个时候时兴三轮摩托车,我们叫‘跨子’,三个警察,弄了一个大瓦圈搁车上,枪架在上面。”
吴菊痴的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展开“八月大逮捕”。平津两地的抗团成员40余人被捕。冯运修在敌人抓捕时英勇抵抗,中弹牺牲。叶于良也被捕了。经受酷刑后,他被押往监狱服刑。此时的他,已经考上辅仁大学。5年的牢狱经历,让他与大学生活失之交臂。
“八月大逮捕”后,抗日杀奸团残存人员继续坚持十分困难,组织部分骨干人员从天津撤离,将“抗团”总部转移至重庆。此后军统为“抗团”成员提供电台和武器,进行人员训练,经过一个恢复时期,从1942年起,又陆续返回平津开展活动,直至抗战胜利。
萨苏提到:“‘八月大逮捕’让抗团遭到重创时期,日军不自觉地放松了对于军统组织本身的压力,军统的正规特工乘机抬头,直接投入行动,给了日伪方面更大的打击。军统特工在华北的一对煞星王文和麻景贺连续出手,先后制造了枪击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飞机场、刺杀日军高级顾问山本荣治和大汉奸王克敏等一系列惊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军统的行动遭到日军反扑进入低潮以后,共产党的‘别动队’又开始活跃于北平城内外,其主要成员多有1939年从抗团中退出的共方成员(抗团早期成员中国共间杂,1939年,因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逐渐暴露,国共合作也已经出现裂痕,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脱离,却侥幸躲过了‘八月大逮捕’的劫难)。”他说,包括冯运修在内的很多抗团成员“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3页。]
抗战胜利后,一腔爱国热血的叶于良出狱,被安排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工作。因不喜欢军警工作,他一年后辞职,后来任职于武汉金融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叶于良曾因工作出色被评为劳模。
镇反运动开始,叶于良被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经特赦后,他回到北京,后来在服装公司退休。
追忆往昔,89岁的叶于良老人讲起当年自己被捕后的一个细节:“那会儿也许是太年轻吧,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就这一条命,牺牲就牺牲了,无所谓。日本宪兵问我:‘你兄弟几个?’我说:‘九个。’他开玩笑似的说:‘九个,死一个没关系,还有八个。’我也笑,说:‘死就死吧。兄弟九个,死我一个没关系。’”
传说中的《色戒》女主角原型郑苹如
郑苹如(1918-1940),民国名媛,中日混血儿,父亲是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的国民党元老郑钺(又名郑英伯),母亲是郑钺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名门闺秀木村花子(随丈夫回到中国后,改名为郑华君)。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曾将郑苹如作为封面女郎。上海沦陷后,她秘密加入与军统同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中统,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后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邨,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但她咬定是为情所困而雇凶杀人,此事成为当年上海滩重大花边新闻之一。1940年2月,她被秘密处决,时年23岁。
“民国第一杀手”和他的铁血锄奸团
1929年,王亚樵(斧头帮帮主,民国史上“暗杀大王”和“民国第一杀手”)在上海开展反霸除奸活动,组织“安徽籍劳工总会”,自任会长,颇得人们拥护,从此当上了“安徽帮”的领袖。王亚樵把他的秘密社团改组为“铁血锄奸团”,专门暗杀汉奸。这个组织包括政工组、联络组、情报组、后勤组及锄杀组等,团员有郑抱真、余亚农、余立奎及华克之等30余人,声势较大。王亚樵1936年身故后,该组织继续活动。
铁血锄奸团的主要锄奸活动有:1931年,日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热水瓶炸弹炸毙,由王亚樵参与策划,韩国志士执行;1935年11月,汪精卫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孙凤鸣击中三枪,留下致命伤;1935年12月,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被刺杀。
鬼子!
亲历者
铃木良雄——时为侵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一一〇大队伍长金子安次——时为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二等兵河村太美雄——时为日军华中派遣军步兵第三十四连队少尉我们的总策划崔永元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话:“我非常担心,年少的孩子们有没有毅力看完此片,我们甚至很困惑,要不要把事实真相这样告诉他们?最后我们选择告诉。因为不说不行。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想,让他感到“困惑”的几集节目中,《鬼子!》差不多首当其冲。因为这种“困惑”我也曾有过——真实到底该如何呈现?
当然,我们的节目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实,但让我们“困惑”的“真实”却另有所指,那“真实”充满血腥、残忍、丧失人性和道德……在节目中我强调了一个事实: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只是400多万侵华日军中两个最普通的日本兵!
被遗忘、掩盖、丢失掉的真实又有多少!
日军的随军记者曾经记录下的日本士兵勇武、干练,又不失阳光、善良,他们是日本人民心中的天使。天皇的部队,是世界上最好的。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大多数日本人民仍旧坚持这一看法,即便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完毕后。
但日军的随军记者也曾经拍下另一部分照片,这些照片全部加盖了“不许可”的印记,而这部分照片中的日军形象完全不同于流传在当年的杂志、书籍上的,他们狰狞、残忍,毫无人性。
当这些真实被刻意掩盖、又在时过境迁后被遗忘的时候,我们所要呈现的“真实”就被赋予了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