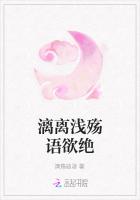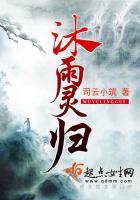黄埔毕业生宋锡善回忆:“一个老百姓变成一个军人还是不容易的。吃饭8分钟,紧急集合8分钟,走路挺胸抬头,步子速度、长度都有要求。那个时候新兵训练整死人,不习惯,你说紧急集合怎么能够那么快?”
黄埔毕业生饶平如慨叹:“说句老实话,我原来在家里是当少爷的,家里有烧饭的大师傅,有黄包车,有车夫。我18岁之前,什么事都不做的,连打洗脸水什么的都是人家帮我做好。”
这些来自各地的青年们脱掉便装,剃掉长发,头戴军帽,腰束皮带,足穿青布鞋袜,打着绑腿,这是抗日军人的戎姿。
宋锡善说:“紧急集合的时候就考察你的着装,不光是白天的着装,还有晚上的着装,那么你晚上着装要快的话,睡觉时衣服怎么摆放,背包怎么打,这些都是在训练范围之内。”
黄埔毕业生李颂卓说:“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兵,都要统一接受专门的训练,这是黄埔的特色。这个训练期满后,就开始接受军事教程了。”
“成为预备军官后,军装就不一样了。”王用中说。
虽然训练、学习艰苦而紧张,不过,黄埔军校学生在当时总是让人艳羡的。
在《黄埔校友抗日回忆录》中,有人如此描述:“星期天放假,我们穿着新发的学生制服,佩学生领章,胸前佩上军校学生符号,三五成群地朝着纳西墟镇游览市容。四川人总爱叫我们老总,同学们说我们不是老总,是学生。在茶座中有一位文化较高的人笑着说:‘你们同学今天是学生,将来就是老总,还要成为抗日英雄呢。’同学们感到自豪,大家都希望当抗日英雄呢。”
人生课、沙盘演习、夜间训练
1938年的一天,张访朋和同学们被通知到大礼堂集合。他到达时,礼堂里已坐满了人,却鸦雀无声。这一天,前线又有失利的消息传来。
张访朋说,黄埔第十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张汉良讲话,“他就讲,做一个黄埔军人,一定要以身许国,你们进了黄埔军校,就把性命交给国家了。”
据张访朋回忆,张汉良给大家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商人到了海边,看到许多渔民在海滩上补渔网。商人问一个渔民:“老兄,我问问你,你的爷爷是做什么的?”渔民说:“我爷爷打鱼。”商人问:“他是怎么去世的呢?”渔民说:“出海打鱼,天气本来好好的,忽然间大风大浪,船翻了,死在海上了。”商人听了之后,挺同情,“哦,这样啊。你的父亲做什么的,又怎么去世的呢?”渔民告诉商人,他的父亲也是渔民,同样死于海上。商人听完渔民的讲述后,便开始劝说渔民转行。渔民说:“先生,我要问问你,你的爷爷是做什么的?”商人讲:“我的爷爷做生意,在外跑来跑去,年纪大了,生病了,死在床上。”渔民又问:“那你的父亲呢?”“我的父亲也是做生意,年老多病,死在床上。”渔民就站起来了:“哎呀呀,你又做生意,你将来会和你爷爷、父亲一样,又死在床上啊,你赶快改行,赶快改行。”
听到这里,礼堂里的500名学生哄堂大笑,掌声一片。
“张汉良说:‘你们反响这么热烈,可见你们懂得了这个故事的真谛。你们来黄埔军校,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祖国尽忠,就是最有意义的。’”
为了锻炼预备军官们的指挥能力,军校里不时进行沙盘作战演习。张访朋回忆:“在一个大厅里边,我们100多人围着一个沙盘,那沙盘比乒乓球台稍微大一点,上面有山、道路、河流、森林、士兵,两军对垒。一边是红的,一边是蓝的。教官讲怎么指挥作战,讲得很生动。”
这是张访朋第一次从军官的角度去思考应该如何作战。“教官通过沙盘教我们,假设你现在是连长,你怎么安排排长、班长,你这个部队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占领阵地,敌人从哪个方向来进攻,面对敌人的飞机、迫击炮轰炸,你怎么指挥。”
黄埔军校迁址成都后,迫于形势,学制大大缩短,教官们选定最重要的基础科目,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些军官必备课程全部讲授完。
王用中记得,紧急集合后,“连长把我们带到野外去,教投手榴弹,还有各种工具的使用,就这样天天训练不停”。
张访朋印象最深的是,“夜间教育特别多。我们都在山地训练,刮风下雨的时候,道路泥泞,遇到大坑,叫跳下去就跳下去,锻炼勇往直前的精神。夜间教育回来时往往到了半夜,脚上都是泥巴,很累了嘛,顾不上洗脚就睡了,被子上沾了脚上的泥巴。天亮时被子上的泥巴就干了,脚上的泥巴也掉了,等以后再洗被子,所以叫‘洗脚不如洗被子’。”
上战场:和老兵比武的新排长有两下子
1938年的一天,黄埔军校成都本校训练场,王用中和同学们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值星官宣布:全体同学到校礼堂集合。
到礼堂不到两分钟,王用中就听到了立正、整理着装的口令。接着报告人数。此时,王用中意识到,一定是蒋介石来了。
王用中回忆起蒋介石的讲话:“他说:‘本首长是全国的统帅,带着这个责任,不能天天来看你们训练。抗战打了一年了,可不得了,紧张到极点了,本校长晚上只睡4个小时觉。你们说训练苦,你们是本校长的学生,应该刻苦,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辛苦,还要牺牲,为什么,你们说为什么?’”
学生们沉默不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自沦陷区。
“蒋介石说:‘你们是步兵,现在各战区牺牲的官长挺多,特别是下级军官不够用,让你们牺牲去。我们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呢?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争取抗战胜利。’”
王用中说,那一刻,聚集了几百人的大礼堂里异常安静,每个人都神情严肃。
经过为期半年的训练、学习后,王用中和同学们被送上战场。
1940年春节过后,张修齐在黄埔军校完成了6个月的加强训练后,被分配到驻第三战区的第109师担任排长职务。
张修齐回忆说:“我们刚到的时候,师长就讲了:‘你们这些学生,在学校里边搞军事演习的时候,那个敌人是假的,他不打你的,现在到这个地方来,你们在敌人面前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战争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学校里不知道,你们自己到战场上去看。’”
张修齐被带到了一个叫做柴家畈的村子。几小时前,这里刚刚进行过一场战斗。阵地上,到处是尸体、丢弃的武器和被炸毁的车辆。
“有野狗去拖尸体,拖得那个乱七八糟的,哎呀,味道臭得不得了,到那儿都恶心。哎呀,大家心里震荡很大,原来战争是这么回事。”
这是张修齐第一次目睹真实的战争场面,眼见的一切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回来以后,师长说,你们现在考虑怎么分配。因为当时我才20岁,还有一个同学也20岁,师长说,你们两个年龄太小了,你们去当排长,士兵岁数都比你们大,你们管不了。我说我们希望到前线去。”
师长没有阻拦,张修齐和同学直接转到了前线部队。
“我们去的时候,那些士兵已经很苦了,由于棉衣没运上来,冬天他们还穿着单衣,身上都生脓包疮,手指上、胯裆里面都有疮,枪都抓不起来。所以分到连队里,我一看,不得了,这不能打仗。”
疲弱不堪的士兵,陈旧的武器装备,让初上战场就指挥一个排的张修齐心急如焚。
“我心想,一有情况,这个仗怎么打?而且我所在连队的连长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对士兵也很刻薄,我心里很难过,我都哭了。那时士兵看到我们也不亲切,因为从未谋面嘛。他们喊我小排长,连问我姓什么都不问。”
张修齐说:“我们有许多班长都是老兵了,都是负过若干次伤的。他们就跟我讲,小排长,打仗你有什么本事?”
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过来的老兵根本瞧不上这个小排长。
“我记得一天晚上有情况,我就带我这个排到外面去搜查,那时候部队没给排长配手枪,我拿了一支步枪,上了刺刀。后来,有个班长对我说:‘排长,你到后头来。’我去了,问什么事。他背着大刀,说:‘我这个大刀砍了不少日本鬼子了。’又说:‘士兵们都认为你不行,他们不敢公开说出来就是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回来以后,他说:‘排长,你说你行,我们来比试比试。当然我不用大刀了,用竹片子当大刀。’我说:‘那我就用竹竿子当枪,我们试试看。’”
听说这位新来的小排长要和老班长比试,士兵们纷纷围观。
“我出枪很快的,刺杀主要就是反应要快。我们在学校学的:首先,你不要看敌人的刀,也不要看敌人的枪,你要看敌人的眼睛,他的眼神就是他的意图表现,这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一点,反应要灵敏,让人家的刀来不及。就这两点很要紧。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我体力不一定比你强,但动作比你快。’确实,他跟我比试过后说,‘哟,小排长还有两下子嘛。’我说:‘怎么样,你大刀刚提起来,我刺刀就到你胸口了,就这么快。’”
这次比试后,老兵们对张修齐的态度和以前大不一样,慢慢的,他们开始接近这个黄埔军校出来的小排长。张修齐带着这些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兵,在战场上一次次出生入死。
“黄埔精神战胜了武士道精神”
1942年3月,黄埔第十七期学生杨岑峰,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二八六团排长,随黄埔三期生——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的部队,进入缅甸同古城。
杨岑峰回忆:同古阻击战即将打响之际,戴安澜带头写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各级军官纷纷效仿。“部队里比较友好的,互相抄抄通讯录,说:‘如果我战死了,你幸存了,通知一下我家人。’”
历时12天的同古大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日军占领了一座空城结束,日军伤亡5000余人。后来,蒋介石听了戴安澜的汇报,夸奖道:“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李菁:《同古:夭折的会战》,《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同古一战后,1942年4月28日拂晓,缅甸平满纳的中国军队阵地遭到日军猛烈炮击,日军轰炸机低空扫射,步兵向杨岑峰所在阵地步步逼近。
杨岑峰回忆:“敌人猛攻了半小时,阵地上死了不少人。有个班长说,排长,你流血了。我一看,身上流血了,我说,没事没事,你们继续战斗。”
杨岑峰咬牙将嵌进肉里的弹片拔出来,简单包扎伤口后,再次投入战斗。
此刻,日军已杀到面前。杨岑峰手下的一个士兵,“四川人,也就20来岁,他喊了一声排长,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机枪打死了”。
杨岑峰说:“我这个排是先遣排,相当于团里一个前哨,距离团主力有三五里路,孤零零的在一个高地上。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前哨,敌人来袭击的话就不知道,那不全军覆没了嘛。当时我看了一下,排里也就剩下不到一半人,副排长倒下了,二班的机枪手已是奄奄一息,一班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
这场战斗打了整整8个小时,阵地最终保住了。杨岑峰的排原有60人,幸存者不过10人。
“那个场面太惨了。炮火非常猛烈,有的士兵衣裳都烧光了,有的负伤了,趴在地上不能动。那个时候心情非常悲痛,打仗啊。战场上,枪炮没长眼睛,打起仗来之后只能前进,不能退却,如果没有命令你就退却下来,马上就有上级一枪把你处决。如果有士兵临阵脱逃,我作为军官有权力把他打死。所以当时两种心情交错。”
1942年5月18日,戴安澜率领第二〇〇师向北转移时中弹,5月26日,戴安澜以身殉国,年仅38岁。
从1942年3月入缅作战到1945年1月缅北、滇西反攻战胜利结束,5700多名黄埔军校毕业生,长眠在了异国土地上。
多年之后,王用中还对他和同学们走出校门上前线的情景记忆犹新。
王用中记得,那是1940年2月23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的操场上,他和同期毕业生们列队唱响校歌。
“宋庆龄先生来了,在台上和校长并排站着,她表情非常和蔼,看着我们,就像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的慈祥,我们心里都很激动。校长走下台,开始骑马检阅队伍,前边有一个卫士牵着马。马走得挺慢,校长看着每一个学生,脸上的表情也和宋庆龄先生一样和蔼,但又透出一种特别的威严,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怒而威。我们都注视着他。”
熟悉的口号声渐渐远去,熟悉的歌声再一次响起,久久回荡。王用中和同学们心里明白,这将是他们在黄埔军校的最后一次集合,同学少年也即将踏上赴死之旅。
初春的寒意还没有退去,冷冷的春风中,隐约飘来一股硝烟的味道……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
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
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编:《黄埔军校史稿》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抗战时期的黄埔分校
抗战时期,黄埔军校一共设立了9所分校:原来的洛阳分校改为第一分校,并迁往陕西汉中;武汉分校早已停办,1937年冬在武昌南湖成立第二分校,后迁往湖南武冈;第三分校成立于江西瑞金;第四分校由原来的广州分校改名,抗战爆发后多次迁移,最终以贵州独山为校址;第五分校成立于昆明;第六分校由原南宁分校改名,后迁往桂林;第七分校最初成立于甘肃天水,后迁西安;第八分校成立于湖北均县;第九分校成立于新疆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