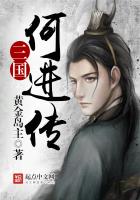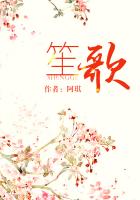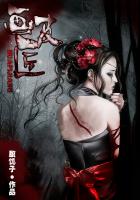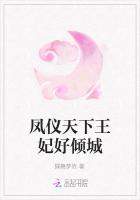1943年夏秋时节,日军驻济南细菌战部队于鲁西北地区扒开卫河大堤,同时播撒霍乱病菌,致使鲁西北、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一带霍乱流行。时至今日,受害者的人数尚无法准确统计,但据估计应不少于20万~30万。
细菌战遗留问题
数十吨生化武器在战争期间被存放于中国东北多处,至今对平民还时有伤害,如2003年9月,在黑龙江,29名建筑工人无意间挖掘到了埋藏地下近60年的化学武器弹壳,造成多人受伤,一人死亡。
黄埔军魂
亲历者
李承勋——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
张访朋——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生
易庆明——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
王用中——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
张修齐——黄埔军校第十五期学生
宋锡善——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生
饶平如——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生
李颂卓——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生
杨岑峰——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生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如若过于强调背景,缺乏个人的鲜活的故事、细节与情感的叙述,注定会让人觉得百般空洞与枯燥。整篇编导手记写下来,像是在作论文,但我始终难以从这空洞与枯燥中跳出来,暂且这样,我想,黄埔军校的将领们,他们的命运也注定要与这跌宕起伏的历史息息相关!
现实亏欠历史良多!
“黄埔”一词淡出人们视线多年,大多数人们知道“黄埔”时,它被定义为蒋介石培养嫡系的一己之私,完全背离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的初衷。在“黄埔”被提及的时候,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是强调最多的。
历史,当然需要多一些层面的了解。北伐不必说了,抗战却需“斟酌”。
1937年抗战开始后,部队里最需要的其实是连、排一级的指挥官,而这些指挥官除了从有经验的士兵中提拔,几乎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这一集亲历者的讲述中,以十四期至十七期黄埔军校学生居多,印象深刻的是李承勋和张访朋两位老人,他们报考黄埔军校的初衷源于1925年,那个春天,他们被孙中山和一群年轻的学生军所打动。
在报考黄埔军校的故事里,在许许多多决心以身许国的年轻人中,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初衷。王鼎钧在《从八年抗战念黄埔先进》一文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他的偶像,在那个各种思潮奔涌、到处都在乱折腾的时代,青年人最羡慕4种人,这就是黄埔军校学生、新闻记者、土木工程师、外科医生。那时候,外科非靠西医不可,西医外科简直是神医;那时候,新闻记者穿长袍大褂,衣襟上插一支自来水钢笔,为民喉舌,见官大一级;那时候,皇权被废除,民国建立,国家建设刚刚开始,到处修桥铺路,盖大楼,修工厂,土木工程师吃香,下巴翘得很高;那时候,黄埔军校学生穿着呢子军服,披武装带,挂宝剑,天子门生,成功成仁,一半是人,一半是神。”
英雄般的偶像,总是让人羡慕,然而,探寻历史,发觉荣耀背后的代价却异常沉重。淞沪会战,自1937年7月至11月4个月间,有一万多名黄埔军官牺牲在抗日战场上。黄埔一期生胡宗南战后回忆道:“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撑持……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
淞沪会战,一批批黄埔将士在战场上倒下去时,更多的青年学子迈入了黄埔军校的大门。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1939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200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于缘木求鱼”……创作中,看到过这样的文字:“鬼子的武士道精神就是杀人很凶,蒋介石说它赶不上黄埔精神。”我的疑问是,黄埔精神到底是什么?
王用中是黄埔军校十四期学生,上学之前就已经打过忻口会战。1940年毕业,后来担任连长,战至抗战胜利幸存下来。70年后,他仍能大段地背诵当年上课时教官的讲话。王用中复述了一段蒋介石的讲话:“蒋介石说:‘你们是步兵,现在各战区牺牲的官长挺多,特别是下级军官不够用,让你们去牺牲去。我们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呢?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争取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至今已近70年,黄埔军校的名称也几经变革,1924年6月16日创办时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3月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8年5月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同年9月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1946年1月,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学校国有化。国民党迁台时,军校一并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
据《广州日报》2010年2月25日的报道,建于1924年的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已被改造成了夜总会。
编导赵慧
1937年的一天,南京城秦淮河边桃叶渡旁的一座小院内,李承勋一家充满了离愁别绪。从这一年8月15日起,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南京,南京城里人心惶惶。李承勋的父亲决定带着全家逃离南京。不过,李承勋有自己的想法。
李承勋回忆说:“我决定进黄埔军校,跟日本人好好打一打,出出气,报仇。”
他对父母表示,已经下了决心,非去黄埔不可。
“儿子要走了,我母亲哭得不得了,缝补我的破衣服。”李承勋说,“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我爸爸就在旁边叹气。”
看着执意要去上黄埔军校然后上战场的儿子,李承勋父母放心不下。他们不知道,儿子的黄埔梦已经在心里藏了很久……两个少年的黄埔梦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灵柩由北京西山碧云寺移送到南京,在紫金山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南京城几十万市民守候路边,为孙中山送行,少年李承勋也在其中。当时的情景,在他心中掀起波澜。
“我一生看过好多名人出殡,这一次是最壮观的,最感动人心的。”李承勋说,“送行队伍很长,有海军,有陆军,有炮兵,有学生,有工人,有农民,有商人,有各国代表。那时我还小,不懂,只是想着,我们中国,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去世了。”
李承勋听说,孙中山曾在广州办了黄埔军校。他对这所学校充满好奇。
1924年6月16日,广州黄埔长洲岛,新创办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清晨,近500名师生列队肃立军校门前,恭迎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孙中山,后来成为陆军中将、时年21岁的湖南人郑洞国也在其中。
多年后,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忆及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演讲:
中山先生在训示中开宗明义,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的事实……这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郑洞国、郑建邦、胡耀平:《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宣布校训为“亲爱精诚”。这是由校长蒋介石拟选的。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的“本校誓词”是:“尽忠革命职务,服从本党命令。实行三民主义,无间始终死生。遵守五权宪法,只知奋斗牺牲。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利钝。”[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编:《黄埔军校史稿》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黄埔军校大门彩楼两旁原挂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额为“革命者来”。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改为其政治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5年,少年张访朋被黄埔军校走出的一群学生军打动了。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征讨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部,取得胜利。其中,黄埔学生军勇敢作战,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
那时的张访朋还是广东揭西一个普通的小学生。他记得,东征军“往梅县那边走,经过我们那个大道”。他从大人口里听到了关于黄埔学生军的故事。他见到,学生军在东征中高喊着“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一路向前。“大家都来看学生军,烧茶,做了很多糕点。端到路边,献给他们吃,大家向他们鼓掌。”
张访朋说,从那时起,他就对黄埔军校有了深刻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20岁的张访朋投考了由广西南宁迁到桂林的黄埔第六分校,成为第十六期的一名学生。李承勋告别父母后,来到武汉,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组织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成为一名学员。后来,这一期战干团学员,被划入黄埔军校第十四期。
军校生活:从少爷到老总
从1937年起,黄埔军校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置招生点。报名者络绎不绝。当南京考生易庆明赶赴黄埔军校设在武汉的招生点时,考试时间已过。
易庆明回忆:“我到那里去时,录取学生的体格检查都过了。我就要求补考,考官说:‘你不是冒充的吧?’他怕我冒充。他让我用英语背《总理遗嘱》,我就背给他。考官说:‘好好好,就背到这里,你是个高中生,不错。’”
易庆明顺利通过了考试。他没想到,在检查身体时,自己却被考官从队伍中拉了出来。“他检查以后说,‘别的正常,血压过高。’我问:‘血压过高,有什么问题没得?’他说:‘带兵管理,血压过高恐怕脾气躁,将来对士兵不好,会虐待士兵。’”
这让易庆明很着急。“我说,那我不虐待士兵,对当兵的像兄弟一样对待啦,我保证不会虐待他们。”
听了易庆明的话,考官没有多说什么。几天后,易庆明的名字出现在录取榜上。
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前夕,黄埔军校撤离南京,经九江、武汉、铜梁,历时十六个月的辗转,最终到达成都,在原成都分校的基础上,建立了黄埔军校成都本部。
抗战爆发后,黄埔军校在全国开设了九所分校,学员毕业后,多充实到军队,成为下级军官。
郑洞国在回忆录中用“火热”二字来形容他的黄埔岁月。火热,是当年黄埔学生们对军校生活的一致感受。
清晨,睡梦中的黄埔第十四期学生王用中和同学们被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声惊醒。
王用中回忆:“按规定只有5分钟时间着装、洗漱,然后带上枪,准备出操。刚洗完脸,就见有个同学没穿好衣服在走动,远处有一个军官向他招手说,过来过来。”
着装不整的学生忐忑不安地走了过去。
“过去了一看,哎哟,是校长。在那儿站好,这个同学吓坏了。”
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的严格要求,王用中和同学们早有耳闻。他们听说,黄埔军校建校之初,一次全校集合时,教官顾祝同迟到了,一边扣衣服扣子一边插入队列之中。这一幕被正准备训话的蒋介石看到了,他马上喝令顾祝同出列,当众罚跪。蒋介石讲完话后径直走了,一眼也没看顾祝同。顾祝同就这样一直跪到第二天早上。
郭一予在《我对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中写到蒋介石对学生的严格:“我记得有个学员因为违反了校规受处分,被关在禁闭室里大哭,恰逢校长蒋介石经过禁闭室,听到哭声,马上说:‘革命军人是有价值的、自爱的,犯了校规受处分,认错悔改就是了。哭!丧失了革命军人人格,错上加错,再加禁闭三天。’”[郭一予:《我对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第78页。]
在王用中记忆中,那个同学走过去站在蒋介石面前,“校长笑说:‘同学,你干什么去?’他说:‘报告校长,我洗脸去。’校长说:‘你怎么不把衣服领口扣好?着装要整齐,明白了吗?’他说:‘校长,明白了。’校长就让他回去了。”
原以为会受到重责的学生,从此再也不敢在着装这样的细节上疏忽大意。
王用中记得,黄埔的严格纪律体现在细节处,比如课堂上有《修学规则》:军帽一定要放在课桌的左前方,不抄笔记时双手放置于膝盖上,坐姿挺直,不准有半点歪斜,双目注视教官,抄写笔记时身体不准扭动。关于讲堂和自习的规定多达20条。
黄埔军校第十五期学生张修齐说:“强迫你要习惯军营的生活,所以刚去时有一个转变过程,哎呀,大家都是懊悔死了,跑这个地方来受这个罪。”
张修齐进入黄埔军校一个星期的时候,觉得盼望已久的军校生活无比枯燥。“天天出操,还没开始文化教育,主要就是锻炼身体。早上跑步,还有机械操、单杠、双杠、木马这些,都是强制性的,一定时间内要达到标准,完不成,就等晚上人家都睡觉了,到操场去加练。那时我们抓那个单杠,手上磨损后都起血泡,不能动了,但你抓在上面不许下来,下来就拿皮带揍你,没有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