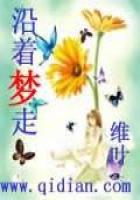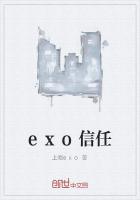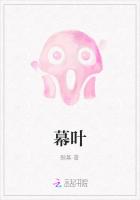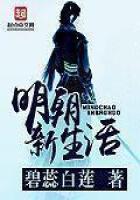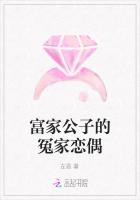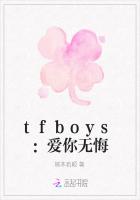祥子今年二十六岁,他是村子里几个念过“大书”的人中的一个,差半年在县城里高中毕业。
当时,家里很穷,父亲的身子骨也一年不如一年,再加上父亲那“透彻”的眼光,虽说祥子还只差半年就高中毕业了,但他仍是坚决反对祥子再念下去。母亲倒是希望祥子将来能有个出息,可面对着眼前家里的环境,她又拗不过祥子的父亲,觉得祥子念也中,不念也行。
父亲说:“一个庄户人家的孩子,尤其像咱们这样的家庭,能念这么多年的书就算不错了,别再想那高口味儿了。庄户人家的孩子,到多咱还不都得种庄稼。比你强的有的是,想吃金饭碗,那得烧多高的香,下多大的雨点儿才能淋到你身上。还是别念了,下来帮家里一把吧。”
祥子一心要念书,他固执地说:“我不下来,我不但要念,我还要参加高考。”
父亲生气了,说:“你说得轻巧,家里这么穷,拿啥来供你?”
祥子说:“我不用家里来供,假期和星期天我找点儿事儿做,我能供自己念书。”
父亲火了,说:“好啊,把你养大了是不是?你还想不想回这个家?还想不想要这个家?”
“我。。”面对着发火的父亲,祥子不知道该怎么说。
母亲也劝慰着说:“孩子!不是当爹妈的不让你念,当爹妈的也盼望你能有个出息,可咱们家现在这个样子,也实在供不起你了,哪怕有一点儿法子,当爹妈的也会让你念的。你爹的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了,吃力的活儿又干不了。咱家这么穷,你妹妹们还小,就靠你弟弟自己怎么行。你还是下来,帮家里一把吧!”
面对着生气的父亲和可怜巴巴的母亲,祥子的心动了。他不再是小孩子,他理解父母,知道父母的难处。尤其是弟弟,十三岁便跟父母下地了。在这样的家庭里,能念这么多年的书,也应该知足了。他没有再和父母反驳什么,默默地回到了家里。只是他的心里不甘,在背人的地方,不知哭过多少次。
本村的李万财有个女儿叫李玉香,照祥子小一岁,就在祥子弃学回家不久,上赶子要将玉香许配给祥子。把祥子的父母可乐坏了。
母亲说:“祥子!你就答应这门婚事儿吧。玉香这姑娘很老实的,我觉得不错,又花不了多少钱。就凭咱这样的家庭,能遇上这样的好事儿,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呀!”
父亲说:“我看这门婚事儿就订下来吧!能有人上赶子给媳妇儿,还得说咱们王家有人性,也说你小子还像个人样儿。”
祥子不同意这门婚事,他有他自己的婚姻观。同时他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过早的被家庭所束缚。虽然说玉香也算是一位不错的姑娘,并和她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可和她之间总觉得只是平平常常,没有什么情分可讲。他想自己的婚事由自己来选择,自己来定,于是他说:“爹!妈!这门婚事儿我不想订,我想等两年再说。”
“为啥?”父亲问。
“我才二十岁,而且。。”
“好了好了。”父亲不耐烦了。“你以为二十岁还小啊?过去像你这么大,早就做孩子爹了。”
“可我跟玉香根本就没有什么话可说,感情怎么能合的来?”
“你以为你小子念了两天半的书就很了不起了?不是这儿合不来就是那儿合不来的,啥叫合得来?啥叫合不来?当初我和你妈的时候,从订婚到结婚,连五句话都没说上,现在不也是有了你们,不也是挺好吗?”
“反正我的婚事儿不用你们来操心。”祥子扔不肯答应这门婚事。
父亲火了:“你小子是不是想把老子气死?你有能耐了是不是?这个家,还有你弟弟,你都不想了是不是?”
母亲也央求着说:“你就别挑三拣四的了,就答应这门婚事儿吧。你也不想一想,现在的姑娘找对象,哪个不喜欢找个家里富点儿的有钱的人家。像咱这样的家庭说媳妇儿,有几个不花大头钱的,还得说人家姑娘愿意的。现在人家玉香家上赶子来,还不是看你不错。你要是不答应,不用说你的婚事儿往后不好办,就连你弟弟的婚事儿也要给耽误了啊!你不为我们这儿当老的想想,可也要为你的弟弟想想啊,他十三岁就下了地,还不是为了供你念书吗!”
母亲说着话,眼泪流了下来。
看到父母这样,祥子的眼睛也潮湿了。只是他心里实在不愿订下这门婚事,可又没有什么办法。
一连几天,家里都被一层阴云笼罩着。父亲不是看这儿不顺眼,就是看那儿别扭,一天吵吵骂骂。母亲也只是不住地叹着气,并用一种渴望。哀求的目光看着他,跟他说话。弟弟也是阴沉着脸,不跟他说一句话。全家人都把他看成了冤家似的。
祥子不愿看到全家人这样下去。他谁也不怪,只怨自己命该如此。他知道父亲的苦衷,不愿意再因为自己而叫父母伤心。难过。还有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对得起自己,自己怎么还能伤他们的心呢?他答应了这门婚事。
转年,祥子便和玉香结了婚,跟父母一起没过多久,就分家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