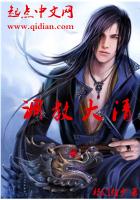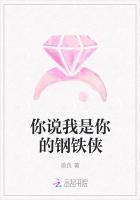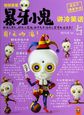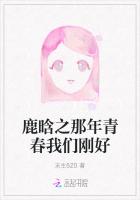近日,媒体报道了一件奇事。去年10月初的一天,成都市武侯区顺江村临街个体诊所“爱心诊所”的老板姚某将前往求医的外来妹刘某麻昏,把她强奸了。之后,姚几次三番以用“炸药炸死你全家”相威胁,逼迫刘某与他同居。愚昧的刘也以为“反正是他的人了”,心甘情愿地作了姚的“妻子”。刘怀孕后,姚对她虐待更甚。刘一出门,以“合法丈夫”自居的姚某就怀疑她与别人有染。终于在今年2月17日,又一次“发挥”他的“医术”,丧心病狂地将一把生了锈的铁锁装在刘的下体。几天后,倍受摧残的刘女才被邻居解救,摆脱了姚某的魔爪。(详见今年2月25日《文汇报》第8版“恶男虐待弱女子,今世惊闻‘贞操锁’”)
在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的已婚妇女是要戴上贞操琐的,尤其在丈夫出远门的时候。那玩意上开了两个小孔,以供排泄,只有丈夫才有钥匙。一些有钱的贵妇便贿赂锁匠,在钥匙打造之时就一式两份,老公一把、情夫一把。对于怕戴绿帽子的先生,真是绝妙的讽刺。
千百年过去,贞操锁阴魂不散,又借尸还魂,以更血腥更残酷的手段蹂躏着女性的身心。虽然刘某的遭遇只是个案,但在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逼良为娼、视妇女为玩物的新闻早已成了旧闻,年轻女子为保住清白不惜跳楼的惨剧也时有发生。大众在赞许那些以死抗争的女性的同时,无形中又强调了男权社会的贞操观念。残废事小、失节事大;摔死事小(?!)、失节事大。刘某在被害之初,从未想到依靠法律保护自己,与贞操观的浸淫不无关系。许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的头脑里还残存着一把把无形的琐,在他们眼里,失去了贞操的女子(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的),仿佛连人格也失去了。于是,一边是高唱贞操赞歌的媒体和大众,一边又是笑贫不笑娼的现实社会。那些不幸失去了“贞操”的女子,她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刚刚欢天喜地地庆祝自己跨进了新世纪的人们,你们头脑里那把绣迹斑斑的锁,什么时候才能砸碎呢?
附注:近闻沈阳有个叫赵林的警察发明了男女皆可穿的贞节裤,赵先生和他的女友带头穿了起来。贞节裤于保住贞节大约很有效,却保不住感情。听说赵先生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了,又听说赵先生闹着要自杀。看来,贞节裤只能锁住“贞节”,却锁不住别的东西。
女人回家的好处
日前,读《南方周末》百姓茶坊版(1999年6月25日出版),异常欣喜地知晓了经济学家钟朋荣先生的高论。钟先生在他的《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中指出:“我国的劳动力总量过剩了两三亿,这些劳动力必然要回家待业。与其让一部分家庭夫妻俩都上岗,而另一部分家庭夫妻俩都回家,还不如让男人留岗,女人回家。这样,有限的就业机会在不同家庭中可以进行比较均匀的平均分配。”同时,钟先生充分考虑到了自由竞争上岗未必能把岗位都留给男人,又提出了“政策引导”的妙方。他还在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呼吁“为愿意回家的妇女创造条件。”果然,“不少女性朋友都表示如果条件允许,本人愿意回家。这其中既有机关干部,也有大学教授。”
读罢这些,我深感吾道不孤。在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尽管鄙人早有此心,慑于半边天的雌威,也只敢在私下里问问朋友。身为经济学家的钟先生敢为天下先,能大张旗鼓地发表这一观点,我除了举双手赞成之外,还要补充几个论点,以助钟先生一臂之力。
第一、女人回家有利于社会稳定贫富均衡。
表面上看起来,妇女同志不论老少贤愚一律回家,是剥夺了她们的就业机会,但这项措施有利于减轻就业压力、有利于财富的平均分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试想,甲夫妇都是硕士,乙夫妇都是高中生。若放任他们自由竞争,对乙夫妇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而一个夫妻双双下岗的家庭,是很容易走向歧路,扰乱社会治安的。妇女一回家,社会总体的就业机会多了一倍,捧饭碗的人则少了一半,再也不会有人(当然是男人)下岗待业了,这是多么美妙的前景啊!
第二、女人回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
妇女同志回家后,摆脱了繁重的工作,由与男人们竞争变成由男人们(一般是由丈夫)供养,身心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原本无暇打扮自己、呵护家人的,如今有了充分的时间烹饪、插花、化妆、逛街购物。因此,服装业、旅游业和百货业将蓬勃发展,并将举一反三,促进其他行业的兴旺。
第三、女人回家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当今激烈的生存竞争,使得诸多高学历的年轻夫妇不敢生孩子,专家们早就担心在人口质量上,会出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状况。如今女人能安心回家,高素质的小宝宝便能安然出世,得到精心的培养。于国、于民、于己,利莫大焉!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就能打破记录,捧回大把的诺贝尔奖。
第四、女人回家有利于重振夫纲。
妇女解放喊了这么多年,我看真有些过头了。以至于夫纲沉沦、夫威尽失,社会大众不以怕老婆为耻,反以“气管炎”(妻管严)为荣。倘若能使女人回家政策化、法律化,让婚姻成为女人唯一合法的饭碗,看她们还敢不敢离婚,还敢不敢做单身贵族!
第五、女人回家有利于廉政建设。
老话说“妻贤夫祸少”,从业已曝光的贪污受贿大案来看,有不少贪官原本也是清官,他们的堡垒,大多是从老婆那儿被攻破的。因此,有的地方专为相当级别的官员的太太举办了学习班,以期“枕头风”吹走“腐败风”。照鄙人之陋见,这都是因为妇女在外工作之故。见的世面多了,难免眼高心大,贪欲膨胀。倘若都象阿拉伯姐妹那样足不出户,只管相夫教子,我国的吏治一定会好得多。
我建议出版社立即重版《围城》中张小姐熟读的那本《How to gain a Husband and keep him》(《怎样获得丈夫并守住他》)。我还打算马上写一本书,题为《怎样讨丈夫的欢心》。希望读者诸君为我保密,别让那些愿意回家的女干部女教授知道,抢了我的生意。
杜康之忧
一提到酒,国人是颇可以骄傲一阵子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中国的谷物酿酒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古往今来,关于酒的典故、酒的诗词,真是俯拾皆是美不胜收。酒中有权谋,比如青梅煮酒论英雄、杯酒释兵权;酒中有豪情,诸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酒中有感慨,比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中更有悲壮:“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酒能助兴,助谈兴、助诗兴,酒逢知己千杯少,李白斗酒诗百篇。酒能壮胆,壮英雄之胆,也会壮贼胆和色胆。几杯酒落肚,平时说不出口的说了,平常不敢做的事也做了。所谓以酒盖脸、酒后吐真言。酒能使人放松,令人陶醉,所谓一醉解千愁。酒更能叫人忘形,发酒疯、“开介橱门(介橱,沪语:碗橱;开介橱门:呕吐)”的也多的是。也有并未喝醉的,借酒装疯、发泄不满,人称酒醉心里清。过后又是一句酒后失德,把错误罪过,全都记在了酒的帐上。我们的文学家,更是把酒的功能夸张到了极致——鲁智深醉拔垂杨柳,武松醉过景阳岗、醉打蒋门神。后来的拳术家索性弄假成真,编出了一路醉拳,也算是丰富了祖国的武术宝库。
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会喝酒就是讲义气、够朋友。到了场面上,好饮之人乘机开怀畅饮,不会喝的,也要强撑着灌几杯,不然就是看不起人。喜酒寿酒,那是一定要喝的。婴儿满月、小孩周岁、乔迁、上大学,亲人故去,都要摆宴请酒,以示热烈或隆重。老友重逢、新知幸遇,谈生意签合同,更是少不了酒。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抿一抿。不喝倒几个,不足以表达幸福快乐之心情,全不管各人体内消解酒精的蛋白酶是有多有少各不相同的。如今,便是因公陪酒,“壮烈牺牲”在酒桌旁的“先驱”也颇有了几个,有的还被公家追认为“烈士”。
酒能成事,亦能败事。除了以上的诸般美名,酒的恶名也不少。殷纣之亡,始于酒池肉林。张飞因酗酒丧身,吕布因酒色授首。李白大醉溺水,“捉月”而死;陶渊明嗜酒如命,害得后代智商低下。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啦、酒囊饭袋酒肉朋友啦,不一而足。老婆骂起贪杯的丈夫来,好端端的佳酿更会变成“猫尿”和“黄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