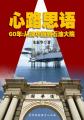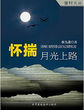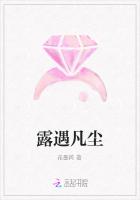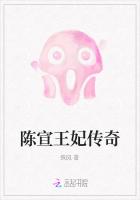北京大学中一些生活困窘的学生如刘仁静、蔡和森、高君宇等人,时常得到李大钊的接济,李大钊还将工资的一大半都用做革命活动的经费。本来教授的薪水还是不菲的,但李大钊每次发工资后很快就所剩无几,一家人的生活几乎难以维系。得知情况后,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已通知财务部门,在李大钊开工资时,留下部分工资直接交给李夫人。
2012年10月,笔者来到北京。此时正是满山的红叶层林尽染红遍香山的最佳时节。笔者来到了和“五四”大街毗邻的当年北京大学的校址,一幢临街气势宏大的红色墙壁的楼房映入笔者的眼帘。这里就是当年遐迩闻名的北大图书馆和北大办公楼所在地,这里就是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在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时,北大学生游行队伍就是在这里集结在这里走出去的。
尽管岁月的时光已磨蚀了这里往日的辉煌,在现代周边高耸的建筑群中,它已没有过去独一无二的雄伟,可是时间的长河中冲淡不了历史的记忆,人们仍然习惯地叫它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一楼的东边,就是当年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这里的一切还照原样摆放,外间是会客室,里间是李大钊的办公室。
如今这里庄重静谧,当年这里却高朋满座,热闹异常,像磁场一样富有吸引力。因北大校长蔡元培倡导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因而北京大学吸纳了当时中国学界许多泰斗级的人物。由于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主任一职,一改以往北大图书馆作为藏书楼的模式,引进了大批当时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理论学说书籍,使北大图书馆成为了解世界的窗口。李大钊被美国图书杂志称誉为中国图书馆之父。同时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强烈地吸引许多同人和学生聚集在他的身旁。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北大的名流陈独秀、胡适、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都是李大钊会客室的常客。他们都直呼李大钊的字号,守常或守常先生。
现在已听不到北大红楼的走廊里纷至沓来的脚步声,也听不到会客室里当年学生们激扬铿锵、教授们学富五车的渊博宏论。但是在这里,睹物思人,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
李大钊就是用手中的笔拨动了时代的旋律,用他的思想谱写了时代的乐章。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文章中说:“在北京惟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大家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那时常去北大红楼的张国焘还回忆道:“那里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集新奇思想的****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那间会客室是社会主义和激进人物荟集所在,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会,很是认真,……1920年时,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浓厚起来。……”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建党后担任了****北方区委书记,****北方区委的秘密机关就设在北京大学的校内。
1921年7月,李大钊创办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工人周刊》,启发工人觉悟,号召各地成立工会组织,并在刊物上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工消息,《工人周刊》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成为北京最受欢迎的刊物。在李大钊的引领下,****北方区委在长辛店等地开办了补习学校,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训工人运动的骨干。
李大钊亲自领导了北方工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仅1922年,罢工的浪潮接二连三风起云涌。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10月唐山铁路工厂和唐山五矿联合罢工的人数超过3万人,12月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又开始了工人大罢工。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形成了北方工人运动的高潮,显示了在党的领导下,北方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都在不断地提高。
在开展如火如荼的工农群众运动的同时,李大钊还积极派遣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北方的许多省份,深入播撒革命火种,筹备建立各地的党团组织,使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燃遍北方大地的燎原之势。
李大钊还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主要决策者和卓越的实践者。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五个成员之一,他同孙中山一起主持了大会,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共青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使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全国逐渐形成。
孙中山对李大钊精辟的见解和非凡的才能十分欣赏。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回忆时说:“中山先生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李大钊的名声越来越大,风云人物李大钊,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极端仇视。1924年5月下旬,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暂时躲避到家乡昌黎五峰山。
为了避开敌人的盯梢和跟踪,李大钊在离开北京西城石驸马胡同35号的住宅时,剃掉了胡须,打扮成商人,装上账册,摘掉眼镜,与儿子葆华带了两个轻便的包袱,乘上晚间的京奉路火车直去五峰山。当晚,北洋政府的警察总监派军警闯到李大钊在西城石驸马胡同35号的家里抓人,扑了空,胡乱搜查一番,扫兴而去。
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看着被军警野蛮搜查后显得凌乱不堪的房间,她由刚才应付搜查的故作镇静,变得忐忑不安,她的心被一缕缕地揪紧。她牵挂着丈夫和儿子,此时他们身在何处,是否安全地登上了去往昌黎五峰山的火车,军警会不会跟踪他们,他们能躲过此一劫吗?
望着窗外冷月清光,赵纫兰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丈夫当年东渡扶桑赴日本留学与自己分别三年整,“五四”运动中险遭被捕,建党后,多次远离家门在外面奔波,每每分开,都是担心挂念和她做伴。这一次丈夫遭受通缉化装出走,如果稍微走晚些,就会被敌人真的抓走了。
想到这里,她有些心烦意乱。她觉得这一夜是那样黑暗恐怖,又是那样漫长。她恨不得立即动身赶火车去老家五峰山,唯有看见丈夫儿子平安,内心才会安静下来。望着身边受了惊吓后才入睡的孩子,想到丈夫临走前“不要为我焦虑,一定要照顾好孩子”的嘱托,赵纫兰禁不住有些泪湿眼角。
在度日如年的忧虑和苦苦的盼望中,一个星期后,葆华回到了母亲身边。他告诉母亲,在五峰山避难时,父亲接到了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给他的通知,党中央决定派他率领****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父亲化装离开五峰山来到了北京,和其他几位代表集合后,已秘密地登上了中东铁路火车。为了让母亲放心,葆华是亲眼看到这一切后回到家中的。
葆华还带回了父亲的信件。听了儿子的讲述后,赵纫兰感到如释重负,她欣慰地看着丈夫的信,信中写道:“……种种的无耻迫害是吓不倒我的,反动派凶恶狰狞的面目只会激起我的愤恨,增强我的斗志。”“以后我再也没有时间顾及家庭了,你要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要振作精神扶养教育好子女……”
丈夫走了,她已经习惯了离别。站在宽阔庭院的海棠树下,在如筛的阳光照耀中,望着夏季茂盛的透着红色的绿叶,一扫心中的阴霾,赵纫兰的脸上现出了几年以来难得的笑容,她在心中祝福丈夫和他的同志一路平安。
1924年6月初,****代表团悄然登上了北京开往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火车,踏上了中东铁路。同行的五位代表是:工人领袖、中央委员王荷波,工人代表姚作民,妇女代表刘清扬,青年代表彭湘、卜士奇。罗章龙也是代表之一,但是后去的。
在硬座客车上,李大钊和五位代表坐在同一车厢中,却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这是为避免发生意外互相牵连。
坐在一个角落的刘清扬在中国妇女界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在“五四”期间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她曾和马骏等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北京请愿,她还是天津觉悟社的重要成员,她是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她和丈夫张中府在法国留学期间,共同成为了******的入党介绍人。
这位叱咤风云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杰,在火车上装扮成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头上还戴着假发髻,一副谨言慎行的农家女子做派。前几天她从上海到天津给母亲过生日时,邓颖超特意过来看望她,帮她做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邓颖超还将自己紫红色的毛衣借给了她,并将所有证件缝在毛衣下摆的一个角上。
每次到站停车或新上来乘客,甚至火车响起“呜呜呜”的鸣叫声,刘清扬表面上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内心却很紧张。她悄悄地提醒自己要镇静。她身上藏着****代表团所有成员的证件,牵一发动全身,一旦证件被敌人发现,所有的代表都无法出国,而且还将遭遇危险和不测。
所幸一路都很顺利,他们平安到达了哈尔滨。
此时,李大钊的好友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已迁往北京,李大钊带着一位青年代表投奔他的党兄李祥年,其他四位代表则住进了一个苏联人开办的小旅馆。
李祥年当时在哈尔滨道外八站与人合资开了一家宏昌远牛店。考虑到李大钊的安全,李祥年安排李大钊住在王芳田在道外太古街开设的宏昌茂杂货店里。王芳田与李祥年是商界的好友磕头兄弟,为人忠厚,老实可靠。
当时,李大钊身穿灰色旧西服,头戴一顶八角帽,脚穿一双旧皮鞋,没有一点来自北京名校教授的架子。受好友之托加之对李大钊人品的好感,王芳田对北京来的李大钊非常关心,在生活上给予了热情周到的照顾。
白天李大钊外出办事,到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会晤朋友,到工人中考察工运,了解哈尔滨建立党组织后开展革命斗争的相关情况。晚间李大钊和王芳田、李祥年亲切交谈,谈到了国内外的形势变化,也谈到了苏联的新变化。
当时的哈尔滨人对红色苏俄是很向往的,多数人对十月革命的故乡都是很敬仰的。宏昌茂杂货店做的是小生意,但当王芳田听说李大钊要到苏联去,便和李祥年等人为李大钊提供了经济上的资助。
那时****北方区委经费十分紧张,代表团去苏俄的资金还未筹齐。况且李大钊又在被通缉中,他几乎是没有时间和自由去筹款,因而李祥年、王芳田等人的资助等于是雪中送炭。
2007年10月,在北京,笔者终于寻访到李大钊唯一在世的儿子84岁的李光华,李光华依然记得哈尔滨人曾为李大钊提供资助的往事。李光华说:“我们家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好心人的帮助是不能忘的。我听哥哥姐姐讲,我父亲曾几次提到哈尔滨人对他的帮助。父亲到苏联开会是住在道外一个叫宏昌茂的商号里,老板王芳田和我父亲非亲非故,不但热情接待,保护了我父亲的安全,还给了资金上的帮助,李祥年也给了路费和生活费用,听说还有别人的帮助,我父亲很感动,曾说过哈尔滨人很有热情和觉悟。”
当时李大钊在哈尔滨通过组织关系找到了共产国际驻哈尔滨办事处,共产国际驻哈尔滨办事处派出交通员负责护送代表团在满洲里出境。
这次出国,因李大钊还在被通缉中,就不可能在哈尔滨办理出国手续。没有护照,就必须想办法绕过张作霖设在边境上的检查站。
李大钊在哈尔滨住了三天,做了必要的准备后,李祥年陪同交通员全程护送李大钊和五位代表,从哈尔滨坐火车走中东铁路到了边境小城满洲里。
李祥年为代表们换了一些卢布,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些路上要用的必需品。
在交通员的安排下,李大钊一行住进了一家小旅馆。这时,交通员引来了干练的老板,并介绍说:“自己人。”李大钊紧紧握住店主人的手。店老板直率地说:“你们六位同志,起码要坐三辆马车,每辆车连车夫在内不能超过三个人。每辆马车一定要用四匹马拉,这才能安全地偷越国境。”“怎么需要这么多的马来拉呢?”李大钊惊奇地问。“少了不行。”店主人说,“偷越国境的时候车子一定要跑得快,马多车轻才能跑得快啊!而且要选择膘满肉肥的好马。”
这时,店老板又详细地向李大钊介绍了国境线一带的情况。在越境必经的中苏两国分界处中国一侧有一个光秃秃的山坡,没有一点隐蔽的地方。山头上设有碉堡,不分昼夜有士兵放哨,一旦发现有人偷越国境,哨兵就开枪射击,有时还派出马队追击,所以绝对不能疏忽大意。闯越国境的马车必须要轻便,能一口气闯过山坡。
翌日凌晨,天色还黝黑的时候,交通员已把雇来的三辆马车停在旅店的门前,李大钊和妇女代表刘清扬坐在前面一辆马车上。
天将蒙蒙亮时,12匹快马拉着三辆马车赶到国境线。有经验的马车夫把马车赶进两个碉堡中间的一条草原小路上,扬鞭催马飞快地向国境线冲去。马蹄声惊动了哨兵,顿时,碉堡里传出来高高的吆喝声和密集的枪声。猝然间,枪声、鞭声、马蹄声相融相织汇成一片,震撼着黎明前的国境线。赶车人轻车熟路非常灵敏地左躲右闪避开了纷飞的弹雨,三辆马车终于有惊无险地闯过了国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