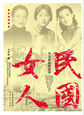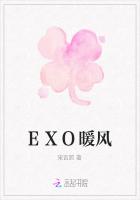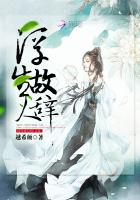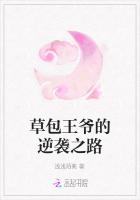警官带队正准备撤离时,忽然一个警察回头时发现大通铺下面有一块可移动的木板,他向警官示意并用手指了指那块可疑的木板。
李芳神色镇定、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主动掀开了木板,说:“这个是菜窖。谁家没有菜窖呀?”警察追问:“别人家的菜窖哪有你家的大?”“我家食杂店,还要卖菜,菜窖能不大吗?”“放的什么菜?”“大白菜,还有大萝卜。”“这么大的菜窖,藏两个人也没问题哟!”“是放菜,不是藏人,不信你就下去搜,搜一搜不就知道了嘛。”李芳的回答不带犹豫,脱口而出。
李芳抱起了正在哭泣的孩子,趁着警察不注意时在孩子的屁股上用力地拧了几下,孩子放声哇哇大哭起来。李芳望着警察说:“这孩子是不是吓着了,不听话,别哭了,别哭了。快搜,你们赶快下去搜,这孩子得让他睡觉了。”
领头的警察开始看菜窖时,还真有些怀疑菜窖下面可能藏了人,转念一想,如果藏了人,眼前这位农村妇女模样的老板娘,在这么多带枪警察的面前,不早就吓得尿裤子了?她大大方方掀开木板盖子,又主动要求警察下去搜查,就说明她的菜窖没有问题,不怕搜查。正在琢磨,孩子大声哭叫起来,这让他感到心烦,于是他挥了挥手,带警察们撤走了。
夜色已经漆黑,万籁俱寂。房间里俄式座钟敲响了12下,已是半夜钟声了。李芳心疼地轻轻揉着儿子屁股上被掐得有些青紫的印痕,望着孩子熟睡的小脸,禁不住泪水滴落在孩子的面颊上。静静的夜里,她不由地想起了远方的丈夫,想起了刚才发生的那惊心动魄的场景,如果敌人真的下到菜窖里,该怎么办?会是什么结果?……她几乎不敢再去想了。
机敏的李芳早已听说敌人到居民家中搜寻外地可疑分子的消息,也打探到警察有时会在夜晚搞突然袭击,她便提前将四位准备越境赴苏联的同志,都藏在了大通铺下面的大菜窖里。从上面看,菜窖垛满了白菜和萝卜,可是如果警察真下去搜查,就会发现堆积很高的白菜和萝卜的后面藏着人呢!
长期从事复杂多变的地下斗争,让李芳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够随机应变、机智果敢的革命者。当危险来临时,外表农村妇女打扮的李芳往往能够做到不温不火、淡定从容。
李芳确定已安然无恙了,便在大通铺下面的那块木板上,悄悄地扣击了几下,这是表示已经安全的暗号。藏在下面屏住呼吸、随时准备与敌人搏斗的四位同志,长吁一口气,有惊无险地踩着梯子爬上来。
这一夜显得那样漫长,大通铺上面的四位同志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外屋床上的李芳,斜靠在儿子身旁,也是难以入眠。
厚厚的深颜色的窗帘严丝合缝,完全遮盖了房间里的一切。这座普通的俄式平房也被黝黑的夜色所湮没。
当时,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归属于****满洲省委领导,具体领导的是哈尔滨北满特委所属的哈尔滨“彩霞湘绣”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也是以杂货店为掩护,负责人是老季。
老季经常以办货的名义和满洲里国际交通站保持联系,他们的联系用暗语,以做买卖的方式进行。或是写信,或是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就通过发电报进行沟通。
如我方人员准备从哈尔滨出发去满洲里,就发“红高粱已准备发货”,如果说敌人的事,就写“白高粱如何如何”。
在哈尔滨交通站和满洲里国际交通站事先秘密约定好接头暗语后,老季就会将这些接头暗语告诉那些从外地来哈尔滨,再离哈走中东铁路到满洲里的同志,并叮嘱他们接头暗语务必要记牢。
满洲里晋丰泰食杂店的老板娘李芳负责出面接待这些特殊的顾客,有一次以黄瓜和苹果为暗语。
这一天,一位陌生的外地人来到了晋丰泰,他询问老板娘:“有黄瓜吗?”李芳回答:“有,买多少?”来人说:“买两三斤吧。”品种、数量和约定的暗号都对上了。
李芳为来人称了三斤黄瓜,她心想,这只是对了一半,如果他拎着黄瓜走了,说明来者不是同志,只是巧合而已。李芳表面上一切如常,并笑着应对别的顾客,却暗暗地观察刚刚买完黄瓜的外地人的动静。
外地人和李芳又继续对话了:
“有苹果吗?”“有啊,你要买几个?”“五个。”“多一个少一个不行吗?”“只要五个!”“好,好,就五个!”
李芳和来人相视微微点头,会心一笑,自己的同志到了!
岁月沧桑,物换星移,往事早已如烟散去。
在查阅资料中,笔者有幸发现了1963年时任江西省副省长兼赣南行署主任王淦撰写的一篇回忆录,文章标题是《经满洲里去苏联》。作为亲历者,他写道:“当时,江西中央苏区曾派许多红军军官经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学习,我们一行四人受上级指派去苏联学习,一路上几经周折到了满洲里。下车后,由一名伪路警(我秘密交通员)将我们送出火车站,交给了乔装成马车夫的同志,他驾车将我们送到晋丰泰食杂店。我们走进这个店里,看见这个屋子不十分大,店堂有个拐把子形柜台,摆满了日用杂品,周围还有蔬菜、水果等。有个女人在站柜台,我们按照上级交代的联络暗语进行联络,这接头暗语很重要,我们都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联系上后,有人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是一间俄式的平房,里面有一个顺长的大铺,能睡五六个人,外面是站柜台的那个女的带着孩子睡觉的床铺,她来掩护我们,对我们很负责任、很热心,生活上的事和所有的事都由她来出头应付……”
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和苏联交通站经常联络,苏联交通员时常来晋丰泰以喝酒为名,送来报纸、文件,晋丰泰老板纪中发有时也把满洲省委的文件交给他带走,同时秘密约定护送赴苏联的同志越境的时间和地点。
越境的时间,一般都是夜晚,由苏联交通站安排有越境经验的俄侨马车夫驾车,趁着浓浓的夜色,东躲西绕,避开戒备森严的重重岗哨,越过边境。马车夫将同志们送到苏联境内的小火车站,由此上火车经赤塔通往莫斯科。
李芳在1984年撰写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文章里写道:“通常是由一个以铁路扳道工为掩护的苏联交通员,来我们这里把准备越境的同志们接走,苏联交通员在前面走,我们的同志远远地在后面跟着。”
“我和纪中发在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送走七十多位同志去苏联学习或开会,没有发生什么问题。1934年5月,我被派往苏联学习,后来纪中发也调走了,满洲里交通站的工作就由别人接替了。”
在满洲里建立的“红色之路”纪念馆内,可以看到专门展示晋丰泰食杂店的场景。情景再现是用建筑材料精心制作的,布景逼真,栩栩如生,带有明显的年代印痕和质感。当年曾掩护和安全护送七十多名同志越境赴苏联学习或开会的晋丰泰,已经成为当时满洲里隐蔽战线中的一面旗帜和重要的历史符号。
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满洲里市政府正准备新建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陈列馆,其中一个重点项目就是在晋丰泰食杂店遗址上恢复其原貌。
国际交通站的故事很传奇,可老板娘李芳后来又在何方,尤其是她离开晋丰泰之后,漫长的岁月中,她的工作生活是怎样的呢?
带着悬念搜寻线索,终于得知李芳解放后在吉林舒兰矿务局工作,可因矿务局已变成矿务集团,打了很多次电话,怎么也联系不上。
2012年6月,笔者坐上哈尔滨开往吉林舒兰镇的长途汽车,决定直接去那里一探究竟。
下车后,就向人询问是否听说过李芳,她的原单位怎么走?
镇上的居民,尤其是四五十岁以上的居民几乎都知道李芳的名字,说她是老革命,人好,愿意帮助别人,并说舒兰镇就是舒兰矿务局的天下,居民基本上都是舒兰矿务局的职工,李芳当过矿务局的领导,所以很多人都认识她。
顺着居民指引的路线,笔者找到了原舒兰矿务局的领导。谈到李芳,他们充满了敬重和怀念之情。
李芳1934年5月离开工作和战斗两年半的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民族殖民地研究院学习深造。1936年6月,被****驻共产国际代表****回东北抗日联军二军,担任二师四团政委兼妇委书记。这位女政委在抗日战争的焰火硝烟中,巾帼不让须眉,率领四团的战士英勇杀敌,卓有功绩。
在战乱的年代里,李芳与从事地下党领导工作的丈夫陶惠明失去了联系。费尽周折,打听来的消息竟然是陶惠明牺牲了。
1936年12月,李芳随同东北抗日联军二师政委王润成去苏联向****代表团请示工作,不久与王润成结婚。
李芳在个人生活方面,命运是多舛的,也是不幸的。她由于从事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不能与家人通信,不能向任何人泄露自己在满洲里晋丰泰的情况,而与原来的丈夫陶惠明失去联系。后来等到的是令她痛彻心扉的消息:陶惠明牺牲了!让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第二任丈夫王润成到苏联后,又赶上苏联肃反扩大化,被以“日寇侦探嫌疑”的罪名逮捕入狱,李芳也无辜受到牵连,被判刑五年。出狱后在苏联当工人,直到1954年才得以回国。
回国后,经过****北京市委组织部审查,李芳恢复了党籍和名誉,后被调到吉林舒兰矿务局工作。
不论命运怎样跌宕浮沉,岁月如何更迭变化,李芳坚定的信仰始终不变。她在舒兰矿务局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为人很低调。在满洲里,晋丰泰老板娘李芳的名字和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在吉林舒兰镇包括矿务局机关内部对她的光辉事迹却鲜为人知。李芳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同事满腔热忱,但从来不提当年勇,也不愿意讲述自己的功绩。矿上的职工和居民,包括矿上的领导都知道李芳是老党员老革命,却很少有人知道她曾是我党隐蔽战线和抗日战场上的女英雄。
1987年9月,曾长期担任舒兰矿务局工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的李芳因病逝世,享年88岁。
原舒兰矿务局老领导对笔者说:“我们矿务局的‘大事记’上面,在显著的位置上登着李芳的名字和她的照片,她是我们全矿的骄傲。”
接着他们找来了李芳的儿媳赵凤臣,赵凤臣对笔者说:“妈妈不在单位讲她的革命经历,她生前在家里曾对我们谈起过在满洲里做交通员的往事。那时一旦有同志们到来,她还是只能按日常用量做饭菜,仅够外来同志用餐。当时形势很严峻,同志们都是藏在屋子里,冷不丁来了许多人,你不能上街买很多东西回来,也不能从晋丰泰往回带,怕引起怀疑。加之当时经费也很紧张,所以她常常吃不上饭。反正来一批外来同志,她就要饿上几天。还听妈妈讲过,她有时要到不同地方去联络,还要有不同身份的打扮,也要带上必要的道具,比如一把伞,怎样撑开,怎样放,放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接头的暗号和暗语,不容得半点马虎。有时周围有敌人盯梢,就更得从容面对。”
在李芳儿媳赵凤臣的讲述中,笔者仿佛依稀看到了李芳当年在隐蔽战线同敌人斗智斗勇、果敢机智的形象,同时禁不住感叹,在敌人的刀尖上周旋的“老板娘”是何其不易。
当年我党为保证红色之路的畅通,不仅在边境地区设有固定的交通站,同时还设有流动的“交通站”。
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枢纽,经满洲里出境为西线,经绥芬河出境为东线。不论西线或东线都是党的红色交通线。
从东线的绥芬河出境后,抵达的是苏联远东海滨城市海参崴,然后从海参崴换乘火车可以通往莫斯科。
群山环抱的绥芬河小镇,平时寂寥冷清。但是每天由绥芬河开往海参崴的国际列车经过时,就给这座荒凉的小镇带来了浓浓的洋气,也为色彩单调的小镇增添了一抹光鲜艳丽的色彩。上上下下的乘客们,不仅有俄罗斯人,还有来自欧洲、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其中一些浓妆艳抹的太太或小姐们或许为了冲淡她们腋窝的异味,故意喷洒浓郁的香水。随着她们勾肩搭背款款而过,那刺鼻的香水味道在徐徐的风中氤氲弥漫开来。
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对这些洋人太熟悉了,他融入在来来往往的洋人中间,和洋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内几乎形影相伴。
随着“呜呜呜”的汽笛声,开往海参崴的国际列车缓缓地驶离了绥芬河站台。在宽敞舒适、设备考究的车厢里,走出来一位身着笔挺铁路制服英俊的中国青年。他穿行在各种语言各种肤色的洋人之间,安放行李包裹,为他们端送热气腾腾的开水,同时还要收拾卫生,做一些擦桌子扫地的活。这位面带微笑、服务热情周到又非常能干的中国小伙子常常受到乘客们的赞誉,俄罗斯人会对他竖起大拇指说“哈罗绍,哈罗绍”(很好)。他是绥芬河至海参崴国际列车上的乘务员,他的另一个秘密身份却无人知晓,就是****党组织委派的国际交通员,负责传递****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信件。同时,车上如果有由他秘密带上来赴苏联的同志,一路上他就要利用自己公开的身份,给予全程保护和掩护。
他的名字叫李春荣。
李春荣是天津人,他是随父辈闯关东来到绥芬河的。他父辈的血汗都倾注在修筑中东铁路的劳作中,后来李春荣也成了绥芬河的铁路工人。在铁路机务段工作中,他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1932年初,19岁的他加入了共青团,还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他带领进步青年贴标语、撒传单,发动铁路工人购买衣物和食品去慰问抗日部队。由于他机智勇敢表现出色,****吉东局便选择他做秘密交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