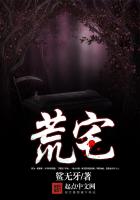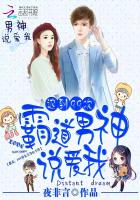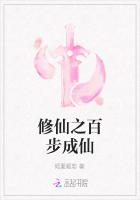1934年10月,受党中央委派,杨光华从上海来到哈尔滨后,重建了遭到敌人破坏的满洲省委,由赵毅敏担任组织部长,谭国甫担任宣传部长,张林担任团********,省委委员有杨靖宇、魏拯民等人,秘书处有雾仙和冯咏莹。
杨光华在担任满洲********期间,卓有成效地落实党中央“1·26”指示,以抗日救国为旗帜,不分贫富,不分职位高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发动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商人包括宗教界人士投身抗日。在满洲省委的引领下,抗日烽火燃遍东北大地。
为了提高各地干部的领导水平,增强各地党组织的战斗力,同时提高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军事素养和战斗力,杨光华先后分别举办政治和军事短期培训班,由省委宣传部长谭国甫具体负责,杨光华还亲自担当了授课任务。
多才多艺的杨光华还以杜嘉的代名,创作了振奋人心朗朗上口的《抗日先锋歌》和激励民众奋起抗争的《满洲地狱歌曲》。
杨光华在《抗日先锋歌》中写道:“赴国难,共伸义愤,破日寇血染战袍,百战铁将军。勇杀敌,齐奋进,朔风难冷救国心,抗日先锋威风凛凛……”
这铿锵有力的《抗日先锋歌》,似战鼓,如号角,为在朔风凛冽,冰封雪裹,山谷作枕,大地为床,吃树皮,食草叶,喝雪水,驰骋丛山密林的抗日将士们击鼓助威,激励他们奋勇杀敌争做抗日先锋。
抗日硝烟早已散尽,歌声仍然萦绕在抗联老英雄的心中。
2013年5月,在哈尔滨东北抗联老战士,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敏的家中,90岁的李敏回忆往事如数家珍,她说:“满洲********杨光华创作的‘抗日先锋歌’,我们抗联战士都会唱。那时候条件太艰苦了,所以我特别喜欢那句歌词,‘朔风难冷救国心,抗日先锋威风凛凛’。这句歌词太好了,很豪迈,很激励人呢!”
名震遐迩的东北抗日英雄赵尚志,就曾在逆境中得到了****满洲********杨光华的鼎力支持。
当年,由于珠河县委部分领导****思想严重,和赵尚志产生矛盾,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杨光华闻讯后,委派省委组织部长赵毅敏深入到珠河县委和赵尚志领导的抗日部队走访调查。在听取赵毅敏汇报后,杨光华亲自批示恢复赵尚志的党籍,鼓舞了抗联部队的士气和斗志。
在生活中,由假夫妻变成真夫妻的杨光华和冯咏莹,性格相投,志同道合。他们都是为了党的事业,远离亲人从南方来到哈尔滨。他们既是革命的战友又是生活中的伴侣,从未谈过恋爱的他们,非常珍惜这份特殊的缘分和情感,彼此关心,深深相爱着。有一次,冯咏莹半夜发烧,身体非常虚弱,作为地下工作者,他们需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尽量不在医院等公开的社会场合留下记录,所以冯咏莹坚持不去医院。在家中,杨光华细心地为冯咏莹用毛巾一遍一遍热敷,冯咏莹高烧不退,他又将生姜切成丝煮成姜汤,冯咏莹恶心呕吐难以下咽,他就用小勺一口又一口地喂到嘴里。在他精心的照料下,冯咏莹终于退烧了。
1935年5月,正是满城丁香花姹紫嫣红竞相盛开的时节,冯咏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也怀孕了。
做为********的杨光华,重任在肩,工作非常繁忙,常常要忙到很晚才回家。当27岁的他知道要当爸爸了,内心里充满了幸福和快乐。作为丈夫和准父亲,他也和常人一样对不久就将分娩的妻子格外呵护。
有时,挺着大肚子的冯咏莹说:“这孩子用脚踢我呢。”
杨光华好奇地俯下身贴着妻子的肚皮说:“让我听听,哎呀,小家伙在动,有造反的精神大闹天宫呢,还挺有劲。”
冯咏莹半开玩笑地说:“这是革命者的后代,有抗争的遗传啊。”
杨光华开心地笑起来:“革命自有后来人啊。”
就在孩子即将出生,冯咏莹急需杨光华照顾的时候,杨光华接到通知要他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对于组织上的安排,杨光华是没有二话的,可是杨光华又多么希望能够陪伴照顾冯咏莹和即将出生的孩子,他真想看到母子平安,亲亲孩子可爱的小脸蛋再走啊。可是党性和责任感使然,他又不得不尽快上路。
临走前,杨光华对妻子殷殷叮嘱,依依惜别。
他安慰妻子说:“你要保重,要照顾好自己和我们的孩子。”
妻子也劝慰自己的丈夫:“你一切放心,工作要紧啊。”
他握住妻子的手说:“我很快就回来了。我们俩是中秋节见面的,这是天作之合,我们很快就会团圆的。”
妻子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说:“我们一起吃的月饼,很难忘。中秋节,但愿人长久——”
杨光华将妻子揽在怀里,抚摸着妻子的双肩,深情地说:“千里共婵娟。”
杨光华再次俯下身来贴着妻子隆起的肚子,贴了好一会儿,喃喃地说:“爸爸听到了你的声音,叫爸爸啊,要听妈妈的话,等着爸爸……”
冯咏莹艰难地挺着肚子倚靠在门口,向走出家门的丈夫招手致意,杨光华停住脚步回望着妻子,并又挥了挥手。在夫妻彼此关切的视线中,杨光华远去了。
冯咏莹已经看不见杨光华的身影了,依然倚靠在门口向杨光华消失的方向远望着……
21岁的冯咏莹想不到此一别,竟是茫茫无期难重聚。
杨光华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从哈尔滨坐上中东铁路的火车从绥芬河出境赴苏俄。
在杨光华出国后不久,冯咏莹在同志们热心的照顾下,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孩子白白胖胖很招人喜欢,逗一逗就会露出笑容,还会“咯咯”地笑个不停,形象也很英俊,挺像父亲杨光华的。
冯咏莹拒绝了组织上安排她休假的照顾,顾不上产后调养和休息,一心扑在了交通员的工作上。
日伪当局为加强控制,在哈尔滨设置的搜查站不断增加。为了应付敌人的盘查,有时为了保证省委文件的安全传递,冯咏莹就将文件秘密地塞在孩子的尿布里,用孩子作掩护。
1936年4月,组织上安排在交通员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二年,没出任何纰漏的冯咏莹赴莫斯科去学习深造。
能够有机会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学习,这是年轻的冯咏莹向往已久的夙愿,她感到欣慰和振奋。
此时有的同志担心冯咏莹带着6个多月的孩子,万里迢迢远赴莫斯科,一路上会很辛苦,尤其是在跨越国境时会增加负担和风险,便提出可以帮助冯咏莹来照顾孩子。
冯咏莹婉拒了同志代她照顾孩子的好意。
她想,再苦再难冒着风险也要带上孩子,这孩子是杨光华最牵挂和惦念的。能把孩子带到莫斯科,让丈夫看到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儿子起个名字,一家人得以团聚,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临走前,冯咏莹连夜为孩子做起了衣服。平时一心忙于工作的她,觉得自己对孩子的关爱和呵护实在是太少了,她望着窗外飘洒着的雪花,生怕孩子经不住风寒。她将拳拳的母爱都编织在为儿子赶制的棉服中,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针针线线总关情啊。
冯咏莹抱着6个多月的孩子,在风雪中坐上了中东铁路的火车。到了绥芬河,却遇上了麻烦。
冯咏莹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心情很沉重,她说:“到了绥芬河下火车,因为日本人看得很严,交通员带着我们白天在村子里转,晚上过境。本来交通员是熟悉秘密过境路线的,可是我怀里的孩子哇哇大哭,越哭声越大,就只好又返回到村子里。交通员劝我把孩子留下来,因为孩子的哭声一旦被敌人听到就会出危险了。我真心要把孩子带到苏联去见他父亲,就坚决不肯把孩子留下,我最终说服了交通员。第二天都半夜了,我用棉被捂住孩子的嘴,防止他出声跟着交通员向国境线跑去。我心揪得难受,也要上不来气了。咳,真难受啊……总算硬撑着闯过去了……”
“我抱着孩子过境后,做火车到了海参崴,苏方发给我服装,又坐上火车走了12天,到了莫斯科。”
听着冯咏莹缓慢低沉的讲述,眼前幻化出一幅画面:年轻的妈妈怀抱着6个多月的孩子,在漆黑沉寂的半夜里,颤抖着手用棉被捂住孩子的嘴,被捂的孩子的呼吸急促细若游丝,已无力啼哭,命悬一线,心如刀绞的妈妈抱着已发不出来声的孩子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前行。这是怎样一幅让人酸楚,令人震撼的画面啊。
如此折腾,孩子活了下来,让笔者觉得庆幸,也不禁感叹,才6个多月的孩子,生命力何等顽强,真是命大啊。
长长的中东铁路,通往世人向往的红色苏联。在众多革命者留下往返身影和足迹的红色之路上,这个小生命,在红色之路的史册上续写了新的一页,可谓创造了奇迹。
杨光华临别时曾说过:“我很快就回来了,我们很快就会团圆的。”言犹在耳,出国已近一年却没有信息。冯咏莹猜想,或许因工作需要,丈夫暂时留在苏联了,但即便如此也该来信告知啊。
冯咏莹作为一名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非常自律,她不会主动去询问组织上没有向她说明的事情,但她内心却很困惑。
尽管紧张的交通员工作,让她会暂时忘掉牵挂和忧虑,可是每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望着身边一天天长大的孩子,对丈夫的想念和惦记,如春天的青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魂牵梦绕,挥之不去。
她抱着孩子坐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听着火车快速行驶时车轮发出“隆隆”的响声,心情好多了。即将见到丈夫,孩子也第一次见到亲生的父亲,一家人能够得以团圆,这是22岁的冯咏莹历尽了艰险磨难后,心里最高兴的事。
然而,让冯咏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到了莫斯科,迎接她的将是一场噩梦。
此时,冯咏莹迫切想见面的丈夫杨光华,却正在遭王明、康生的政治排挤打压,处在被审查的逆境中。
原来,杨光华在上海中央局工作期间,曾经抵制过王明、康生的错误路线,王明和康生便怀恨在心。
此时的王明和康生是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趁杨光华来莫斯科汇报工作之机,对杨光华鸡蛋里挑骨头肆意诬陷和迫害。
杨光华来到莫斯科后,冷板凳坐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才通知他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二楼一间会议室召开满洲省委工作汇报会议。
杨光华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本子上也认真地撰写了汇报提纲。在会上,杨光华很全面地作了满洲省委的工作汇告。汇告完毕,王明建议先休息一会儿,于是大家都走出会议室,这时王明一反常态走到杨光华身边,亲切地问杨光华的身体如何,并建议他到南俄罗斯去调养些日子。一个俄国人走到王明面前,用俄文同王明交谈几句,然后锁上会议室的门走了。杨光华急忙和王明说他的本子还在会议室里,王明看了看表说该午休了,下午接着开会,再拿本子也不迟。
下午再开会却换成三楼的会议室。杨光华对王明说,他的笔记本还在上午开会的那间会议室里。王明反问:“你汇报还用笔记本吗?”杨光华说:“可以不用,但本子必须拿出来。”王明敷衍说:“回头我让他们拿出来便是了。”杨光华汇报完毕,王明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总结,会议就算结束了。杨光华又提出要取回笔记本,王明却不耐烦地说:“在共产国际的机关里,你还不放心吗?”
然而,就在会议的第二天,该招待所职工支部就传出一条重要消息,说杨光华故意丢失一个秘密的本子,已被招待所清扫工拾到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了。接着,杨光华便被监查委员会拘留审查,杨光华试图解释,却受到不许诬蔑王明同志的严重警告。
1935年7月29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早在湘鄂西根据地时,杨光华就被选定为出席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三人团团长。现在杨光华就在莫斯科,却没有让他参加会议。
杨光华只能无奈地接受没有期限的审查,审查期间是不允许写信的,也得不到外面的信息。
这时的杨光华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十分强烈,他常常在想:他们母子平安吗?孩子长得什么样?省心吗?他曾贴着妻子的肚皮听孩子的胎音,依稀听到孩子连踢带打的声音,太好玩太可爱了。他猜想,小生命这样好动有劲头,十有八九应该是个儿子。
在妻子最需要丈夫关爱,在儿子最需要父亲呵护的时候,他却不在妻儿的身边,他恨不能立刻飞到妻子和儿子的身旁,可惜自己的翅膀被折断了,想飞也飞不动了。他与外界隔绝,感到很压抑,有股窒息的感觉。
1936年5月,恰巧在杨光华离开家门一整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儿子万里迢迢到了莫斯科,望穿秋水般地要见他,要和他团圆。那六个月大活泼可爱的儿子也等待着父亲的拥抱和热吻,等着父亲给起名字,但这一切,杨光华却全然不知……
冯咏莹回忆到这里,沉默了好一会儿。她用手捋了一下银白色的头发,脸上现出了无奈和无助的表情,她想接着往下说,声音却有些哽咽了。
女儿杨剑如握住母亲的手,稍停片刻,激动地说:“妈妈到了莫斯科,康生不让妈妈去见爸爸,妈妈第一次向组织反问为什么?康生严厉地说,杨光华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在审查,不许见。康生说:‘孩子交到幼儿园,以后你要安心学习,不许见孩子,影响学习不行。’那时孩子还不会叫妈妈,六个月的孩子哪有会叫妈妈的。很快就有人把孩子抱走了,妈妈心里非常痛苦,经常夜里想孩子,哭泣不止,又没法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