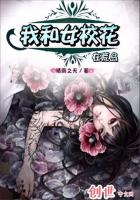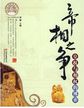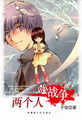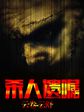政府军冲进了马科斯的小屋,毁掉屋内堆满的书籍,像对所有的原住民萨帕塔人的家庭一样,政府军复仇、亵渎式地粉碎了屋内的一切。与此同时,无数支巡逻队、配备了大量警犬的武装警察部队开始在整个地区大规模地搜捕马科斯和萨帕塔运动领袖。曾为马科斯拒之门外的官方背景的媒体(诸如维萨和阿兹泰克电视台)此时奉命随军拍摄。但在镜头之外,拉丁美洲反抗历史上“例行”的一幕上演了,到处是逮捕、拷打、强暴和毁灭。萨帕塔运动领导人的棚屋被涂上了白色的标志以资辨认。同情萨帕塔运动的记者指出:这一切极像圣巴托罗缪之夜或纳粹大屠杀。如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列托实事求是、但听上去颇富反讽的说法是,“如果用拉丁美洲的标准来衡量,政府军其实保持了高度克制。”而同时在墨西哥各地出现了比23人的通缉令的规模要大得多的搜捕行为:纪廉的前女友、坦皮科市纪廉儿时的邻居、今日的反对党领导人..都遭到逮捕。而恰帕斯的一个普通鞋匠也成了众多被逮捕的嫌犯之一,当他满脸伤痕地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他被控的罪名是“向萨帕塔人传授制鞋技艺”。以此为开端,政府陆续派遣了6万正规军进入萨帕塔地区,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低密度战争”。
如果我们将萨帕塔运动的12年视为一部壮观的大型剧目的话,那么,政府惟一一次拿到好牌的机会,便是这次“揭秘”之举。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破神秘莫测、高来高去的马科斯的真实身份,彻底粉碎马科斯神话,抹去他超凡魅力的光环;更在于还他“本来面目”: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后现代革命者,符号学游击战、或赛伯空间游击战的创造者,无外乎是一个“老旧”且“面目可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一个激进的、行动派大学教授。或者如CIA背景的美国“报人”丹尼尔·詹姆斯对切·格瓦拉的定位:一个花衣吹笛人:以曼妙的笛声迷住众人,将他们一步步引向死亡的峭崖36。然而,这张好牌的效应不足72小时。面对政府的揭秘,原住民革命委员会、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立刻予以否认,同时发出了一个此后数年将在墨西哥和世界许多地方回荡的呼声:“我们都是马科斯!”
而通缉令发出三天之后,从“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发来政府进剿之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第一份公报,当然也是被揭露了“真实身份”后的马科斯的第一份公开信:《萨帕塔人提升了墨西哥原住民鲜血的价格》。在义正辞严地痛斥政府暴行之后,如马科斯惯常的文风,出现了精灵古怪的附言:
我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另一个“马科斯”,据说他是坦皮科人。听来不错,一个美丽的港口城市。我记得我曾在[坦皮科州附近的]马德罗城的一家妓院当保镖..“又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仍不弃其自恋:那么..这个新的副司令马科斯是否英俊?因为最近他们派给我几个实在丑陋的家伙,害得我的女性笔友深感幻灭。“又及”清点着时间和弹药:我有300发子弹,所以会试着吸引299名士兵和警察来抓我。(传说中我弹无虚发,想不想来证实一下?)既然有300发子弹,干吗是299个兵?是了,最后一颗要留给知名不具的发信人。大结局就将这样出现,一颗子弹成了这孤独之心的惟一抚慰。又一次道别了。祝你健康,在她的心里可为我留有一小点位置?(署名)副司令,以骷髅卖弄风情的姿势重整他的滑雪帽。
马科斯确实“重整了”他的“滑雪帽”。如果说,揭秘行动曾一度使某些时尚中人与另类青年热情褪色的话,那么,这写在重兵围剿与军警大搜捕中的、充满马科斯特有的机智、调侃与爱欲(或干脆称之为色情兮兮)风格的言辞,片刻间重新点燃了人们对这另类偶像的赤诚。通缉令数天之后,墨西哥城和其他大城市爆发了数万人参与的抗议示威。示威者抗议对马科斯等人的通缉,要求立刻停止围剿,停止对萨帕塔人的屠杀和迫害。
数万人在都市街头高呼着:“我们都是马科斯!”被称作“萨帕塔人的约翰·里德”37的美国记者约翰·罗斯写道:他遇到了一位显然颇为高雅的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后者走在游行的队列中,十分惶惑地自问、也是回答记者:“我从不参与这种事儿。可我今天这是怎么了?”38在国际社会上,艾柯——著名符号学家、中世纪史学家、《玫瑰之名》、《福柯摆》等全球畅销书的作者,首先向萨帕塔人发表了声援信,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和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根廷的人权运动领袖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和危地马拉维护原住民权力的斗士里戈韦塔·门琴·图姆及全球各界知名人士。同时,在巴黎、巴塞罗那、柏林、斯德哥尔摩、圣地亚哥、马德里及意大利全境,爆发了萨帕塔运动支持者的声援示威。人们在墨西哥使馆门前以各种语言高喊着“我们都是马科斯!”
在围剿开始的第一周之中,传媒不断惊报“已然抓获马科斯”的消息,其中一次,竟然是在同一天内、两处同传“抓获马科斯”的“捷报”。很快便证明,被抓获的所谓“副司令马科斯”,一个是经历车祸至今仍神志不清的老神父,一位是外国的鸟类观察家,另有一个是曾参与尼加拉瓜革命的、的确名为马科斯之人。更有甚者,便是军方报道了“击毙马科斯”的消息。对此的回应,便是马科斯的公报和书信(时而达每天万字之多)如雪片般地自丛林深处飞出。在“击毙马科斯”的消息传出之后,马科斯称此后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再一次与死神面对面,令马科斯的创造力呈现了眩目的迸发。
这每日飞来的公报和信件逐日记录着“战略转移”(或称“大逃亡”)中情境:与政府巡逻兵(“身着橄榄绿的死神”)近乎“零距离接触”;没有水、没有粮食,试图以尿解渴;拖着负伤的身体,攀上高山峭岩,穿越泥泞沼泽;“盖着猎户星座和军用直升机的噪音”,在暴雨的丛林中度夜;最终进入“只有野兽、死神和游击队的原始丛林”——杜里托/那尊贵可爱的小甲虫在那里正式登场,在丛林中经历“逆进化”——从人到猿。也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马科斯持续地书写着,以后现代式的拼贴、游戏的笔调书写他的抗议、政治论文、呼唤着市民社会、探讨着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及全球格局;以戏仿或近乎于色情的笔调撰写记忆、寓言和故事;和世界知名作家、学者们通信讨论着哲学、思想与斗争。有论者提到,马科斯1994—1995年之交的公报,犹如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日记》的遥远而震撼的回声。39
事实上,当政府军全线推进之时,人们曾推断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可能拼将一死。但这并非第
一次、也非最后一次令人们始料不及: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未发一枪,全面撤退,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不曾与政府军发生过任何军事接触。只有马科斯以笔为剑。如果说,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全线撤退、战略转移绝非游击战史的特例,那么,作为惊人之首例的事实是,大举后撤的不仅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而且是整个萨帕塔社区。人们扶老携幼、背负着政府军过后幸存的一点粮食、“财物”,追随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举部迁往大山、丛林深处。支持萨帕塔运动的传媒称之为“出埃及记”。那是一个极为壮观而惨烈的场景:在高速公路、山间小路上,在根本没有路径的丛林、山崖间,老人们拄着拐杖,年长些的孩子背抱着年幼的,头顶着包裹、怀抱着婴儿、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妇女,行行缕缕、络绎不绝地行走着,越来越缓慢、却义无反顾。从政府军发动进攻的2月10日,直到这一年酷热的7月间,这迁徙方告一段落。等待他们的,是人类难于生存的丛林、饥饿和轻车熟路的死神。但萨帕塔社区的人们信守他们的公决:不投降,不妥协。
在国际舆论和市民社会的巨大压力之下,3月,政府军停止了朝向丛林腹地的推进,新的相持局面再度形成;但不断加派军队的行动仍在进行,终于6万政府军以铁壁合围之势紧紧地围住了只拥有数千人象征武装的萨帕塔人。继而开始的,是旷日持久的“语词的战争”。也就是在1995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危机全面爆发,股市崩盘,迫于美国压力而开始自由兑换的墨西哥比索在短暂的升值之后一落千丈,贬值达50%,原本数量惊人的外债此时变成了天文数字。失业与破产成了日常剧目。萨帕塔人及其支持者的洞见成了现实: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步入第一世界行列的许诺,此时成了南柯一梦。
面具,智慧的即兴创作
在萨帕塔运动——这场符号学游击战之中,最为突出的符号,无疑是萨帕塔人的蒙面形象。面具——滑雪帽或红帕子,便成了萨帕塔人的核心能指。对殖民统治500年间的玛雅原住民说来,当他们用面具遮住了自己的容颜,他们才第一次成了美洲、乃至世界传媒的焦点;他们才不再是一段古老而神秘历史的遗民,现代社会愚昧而麻木的奴隶;而是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政治力量,是向现代世界展现并阐释何为尊严的人群。用马科斯的表达,便是“我们是武装起来方才获得倾听,遮住面孔方始获得注视,隐匿了名姓方能获得命名的人们”。那面具是一面镜,映出你心中的反叛的呼唤:“在面具背后,我们就是你。
”对每一个萨帕塔和萨帕塔运动的支持者说来,你蒙上自己的面容,你便成了萨帕塔运动的战士;你摘下面具,便“恢复”为一介平民。来自墨西哥和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汇入了萨帕塔运动的波涛和潜流;而萨帕塔人也正是在“出入”面具之际,以和平的方式直面着、规避着杀戮和暴力。于是,无疑是世界游击战史上的奇观:当政府杀入萨帕塔地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战士不是迅速撤离村庄,避走上山,而是摘下面具,下山返回村庄。当政府军声称他们从未遭遇到任何萨帕塔人的时候,他们可能正与一位萨帕塔战士交臂而过。而在漫长的相持之中,每次以人盾/血肉长城来和平阻止政府军侵入之时,政府军面对的,是蒙面人的海洋。这里,无所谓士兵与平民、军队与人民、萨帕塔社区与外来的支援者。
而面具无疑是马科斯魅力的来源之一。这固然由于面具令马科斯迷人而飘逸,墨西哥著名作家、记者、公共知识分子蒙斯瓦伊斯说,“不戴滑雪面罩的马科斯将不会被接受、也不具有上镜头性,更不会成为一个活着的神话”。而不无敌意的讥刺者则写道:这张蒙着面具的脸“使人直觉地感受到一位英雄,他是凌空出世的半神或一道永恒的闪电”,“在‘历史的终结’和全球化的开端之际,
‘马科斯’犹如防火墙上一道突如其来的红色火焰”。40面具成就了马科斯的神秘与谜语——尽管Who is Marcos?的浪潮不再翻卷,仍没有人能在持枪蒙面的马科斯与哲学教授拉法埃尔·纪廉间划上等号。但更重要的是,面具令马科斯以迥异于其他拉美游击领袖的形象,凸现出后冷战喧嚣画面的世界图景所遮掩了的画面;令他得以融入“土地之色”的人们中间:不是代言人,而是翻译者。
或许,由于“20世纪的所有记忆都是关于革命的记忆”,但每段记忆的终了处,却是革命被背叛、遭出卖的记录。因此,萨帕塔运动之初,便不断有人预言着运动的失败、至少是推测其终了的形式。其中的内容之一,便是马科斯何时、如何摘下面具?对此,马科斯的回答是:当墨西哥摘下面具之日,便是马科斯除去面具之时。而“面具摘下之时,‘马科斯’便不复存在”。因为
“马科斯”原本是这出剧目中的一个角色。
如果说,马科斯成功地以面具挪用了大众英雄佐罗的形象,从而消融了全球甚嚣尘上的、对革命、革命者的敌意和缺席判决;那么,鲜为墨西哥之外的世界和人们所知的是,面具不仅是墨西哥人深爱的、大众文化独有的形态,而且有着历史和现实斗争的传统。在墨西哥,不仅有着黑斗篷的蒙面侠士佐罗,有着面具戏剧的传统,面具也是鬼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在为墨西哥所深爱的自由式摔跤中,面具则是摔跤手必须的装备和道具。因此而诞生了一种墨西哥特有的大众文化偶像:蒙面摔跤手+电影明星。名传遐迩的有:桑托(意为圣者,亮银面具)、“蓝魔鬼”(海蓝色面具)、“千面人”(彩色面具),他们都是著名的摔跤手,也是深受观众爱戴的、分别主演过50部以上通俗系列电影的明星。无论在摔跤场上,还是在影片中,他们都不曾摘下面具,面具是他们定型化形象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如佐罗,他们大都出演着惩恶扬善的喜剧英雄,在其影片的大团圆结局中第N次地战胜形形色色的邪恶、魔鬼,拯救美人、人民、墨西哥和世界。在墨西哥的蒙面英雄系列中,最富戏剧性的,却是当代墨西哥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