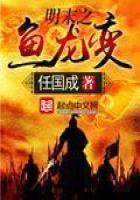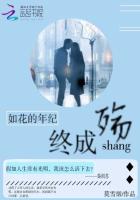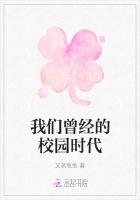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政府谈判代表的一轮又一轮、旷日持久的谈判之间,1996年初,萨帕塔人又一次敞开大门向全世界发出了邀请,邀请所有反对新自由主义、渴望一个不同世界的人们前来萨帕塔人新的首府:拉坎顿丛林中的“真实村”。于是,1996年的春夏,偏远、蛮荒、遍布泥泞、弥散着浓雾的真实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中心和另类的嘉年华会。约翰·罗斯以调侃的口吻写道:“1996年春,群星降落恰帕斯。”46先是好莱坞名星与欧洲名流的“分列式”:以著名电影导演奥利佛·斯通及其摄影组为先导——他刚好在奥斯卡之夜进入丛林,那一天,他的巨片
《尼克松》正以四项提名角逐奥斯卡;接着是电影明星埃德华·詹姆斯·奥尔摩斯。此后是法国著名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紧随其后的是国际著名人道主义活动家、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达妮埃尔·密特朗。提供“背景音乐”的是拉美数个旁克乐队。美国记者不无醋意地写道:因为马科斯的法语更加出色,所以法国贵宾备受青睐。如果说,马科斯与德布雷的在林间、树下的长时间恳谈,令全世界忆起了切·格瓦拉和他在玻利维亚的游击营地;那么他一度与达妮埃尔·密特朗的“亲密接触”,则使得传媒继马科斯的情人究竟是安娜—玛丽娅少校还是拉莫娜司令的窥秘渴望之后,再度迸发臆测绯闻。(而密特朗夫人本人则告知《进程》周刊的记者:“我们共处的时光是如此美丽,如此亲密,如此意味深长。”47)事实上,密特朗夫人的到来,不仅为萨帕塔人带来了必需的(当然远非充足的)食物和药品,而且她接受了马科斯的“任务”,护送塔丘司令通过封锁线,前往出席谈判。更重要的是,国际群星莅临、并成为墨西哥传媒的头条新闻,为萨帕塔人提供了新的象征性“人盾”,政府军计划中的军事行动被迫延缓。
这一年的七月,在拉坎顿丛林深处召开的“第一届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国际聚会”,令真实村如同灿烂且密集的星空。6,000余名来自42个国家的客人中,有重量级人物、萨帕塔运动著名的支持者、拉美最重要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享有全球盛誉的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们,当代法国极富创见的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俄国电影制作人鲍威尔·卢冈、突尼斯著名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家、律师、作家吉茜莉·奥里米,等等、等等。
那是极为奇特、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组合,来宾中有各国知名学者,艺术家,各地绿色和平或反核组织,欧洲社会主义团体,无政府主义机构,诸如同性恋等少数群体,大量纪录片制作者,无数摇滚、旁克、嘻哈乐队,巴西工党,无地农民运动,拉丁美洲各国前著名游击领袖,甚至有一个正式古巴代表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国各式的服装服饰、听到全世界的各种语言。一次建造巴别塔的会聚。入夜,又是约翰·罗斯写道:那为烛光所照亮的小学校的晚餐桌,酷似17世纪画家乔治·德·拉·图尔笔下那明暗对比强烈、盈溢着神秘氛围的圣像画48。先于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1999年)、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萨帕塔人率先展示了一次全新的联合:“拥有共同的拒绝、不同的追求(One no,many yeses)”的会聚。类似却不同于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马科斯和萨帕塔人的主张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包容所有世界于其中的世界。
经历了18个月的艰难谈判之后,萨帕塔人与政府谈判代表缔结了《圣安德列斯协议》,承认原住民自治和保有自己文化的权利。但政府却继而宣布否决这一协议。
1996年底,萨帕塔人无视政府禁令,以深受墨西哥民众爱戴、病势沉疴的玛雅原住民女司令拉莫娜为代表,出席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全国原住民代表大会。当载有拉莫娜司令的、民间组织的飞机降落在墨西哥城机场上的时候,以墨西哥自治大学学生为主体的数千人等在那里迎接她,人们高喊着:“我们都是拉莫娜!”拉莫娜强撑病体,在大会作了公开演讲。一入一出,政府军对萨帕塔的政治、军事与文化封锁已支离破碎。
事实上,邀请各界人士汇聚丛林、和平出访、举行大型“民意调查”,是萨帕塔运动的重要斗争策略。在1995年之后,萨帕塔人多次在丛林中、不同的阿瓜斯卡连特斯举行了数度几千人出席的大型国内、国际会聚,1997年,他们派出各部族代表1,111人乘车前往墨西哥城,1999年举行的民调,参与投票的人数多达300万人。而1997年底当蒙面民团野蛮杀害了47名萨帕塔社区的妇女儿童、1998年政府军试图入侵萨帕塔社区之时,市民社会支持的浪潮一次次达到了新的高点。
语词之战,萨帕塔人的“悖论”
事实上,在萨帕塔运动12年的历史当中,只有1994年最初12天的交战记录。如果使用罗斯的修辞,将1994年—1995年称作“言说之枪”的时期,那么,几乎从开篇伊始,萨帕塔运动便同时是“武装的语词”的年代。或者用马科斯的说法,是“我们的语词是我们的武器。”49可以说,萨帕塔运动的12年,是武装斗争的12年,是另类政治实践的12年,同时是语词战争的12年。这正是将萨帕塔运动称为“后现代革命”、“符号学游击战”、“赛伯空间游击战”的含义所在。这也是萨帕塔运动的外在“悖论”之一:一场以持枪蒙面为其特征的武装起义,却以文字语词为其主要且基本的武器;拉美游击战史最新的一页,甚或像来自逝去年代的一阕回声,却十足的“当下”,充满了后现代文化(甚或后现代文化游戏)的印痕。显然,这正是萨帕塔人与马科斯的诸多
“越界”之一,他们以其原创的政治实践,改写了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当代文化逻辑。如果说,这是一场符号学战争、一场后现代革命,这里涌流着五彩拼贴、几近谵妄的文字、语流,那么,这里发生着的,不是弥散或曰“内爆”,而是始终以其所指物——武装的原住民及其历史与现实的苦难——的在场为其充分必要的前提。如果说,马科斯不断以精妙的后现代文体于嬉笑怒骂中解构着种种现代社会的神话,那么,这解构的力度却来自于任何语言游戏都无从解构的现实、苦难、鲜血与生命。不错,马科斯的形象和作为,令今日世界舞台上的诸多政治角色失色,间或令全球波普艺术或行为艺术表演汗颜,那么,这形象与表演,却始终服务于逆转世界潮流的政治尝试与实践。如果用美国记者的说法,将萨帕塔运动——这场以语词为主要的武器的战争,视作马科斯“一个人的战争”50,那么,马科斯之所以能支撑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并不断击中全世界的“眼球”,却无疑因为凸显了他的底景是拉丁美洲鲜血浸润的大地,是他身前无数印第安原住民500年来的抵抗。
可以说,这场语词的战争,几乎在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便已然开始。1994年,马科斯在战争、相持与谈判期间发表的大量公报,有理有力地逐一驳斥着政府传媒机器兜头泼下的种种污水、污名。而自1994—1995年之交始,马科斯的众多公报和信件,便进一步成为墨西哥、也是今日世界奇特而独到的文字、书写形式。这正是萨帕塔运动的又一悖论所在:马科斯的匿名与具名形式。马科斯是无名的,那“名姓”只是一个前赴者的化名,一个或可替代的角色,一个发言人的位置;马科斯又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写作中,在他的文字里,他的风格和语调是如此的别致、原创而无可替代。一如墨西哥著名的女作家、新闻记者和教授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所言:马科斯的抨击者说,切·格瓦拉始终以真面目示人,但我们说,马科斯在他的公报中面世。在其公报中他裸露出的远多于我们直视他的面目。51而伊兰·斯塔文斯则指出:“不错,副司令拥有一支步枪,但他很少用到。
他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开火,投掷公报形式的集束炸弹,他的笔下迸发出文字的洪流..颠覆了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在专制政体下,知难行易’的论断。”52人们似乎必须用一连串彼此矛盾的形容词来尝试界说马科斯的语言风格。诸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系教授J.沃马克便曾写道:“马科斯的公报和访谈是如此的戏谑、尖刻、诗意、专断、滑稽、自恋、辛辣、狡黠、吊书袋、福柯式、魔幻现实主义,有着现代话语与协商语气的完美的个人风格,但这话语与协商不是朝向政府或其他运动,而是通过现代媒体朝向现代公众;其信息不是战争、或和平、或和解,而是无休止的、充满诱惑力的论争。”53而拒绝萨帕塔运动的何塞·考利纳写道:马科斯的文章“是预言性的、玩笑式的、悲凉的、控诉的、政论性的、抒情诗般的、有时还会是粗俗的:那种独白,来自从恰帕斯印第安人口耳相传的故事或诗歌到最庄严抒情的长篇激烈演说、优美的诗歌或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文学;通过某种杂糅着对福柯和阿尔图塞的下意识引用的马克思主义而抵达了德里达,再穿过第三世界复兴的意识形态、现代主义者的本土主义,重现了半葛兰西民间社会”54。
马科斯的公报和书信常常是不同文体、不同风格语调、甚至不同人称叙述间的跳跃。以他那无穷无尽的附言,在大刀阔斧、言辞犀利的政论间是诗意的小故事,在诙谐、滑稽的(通常是萨帕塔人的孩子们的)场景中穿插着安东尼奥老人那沉郁的叙述与玛雅的哲理,在《玻利维亚日记》式的现实书写中闪现着小甲虫杜里托的稚气可掬的身影,在政治经济批判中是诗行和关于“海”的深情的文字,在杜里托和“我”/副司令之间,在“我”和“我的另一个自我”的“对话”间,流转着缠绵又不无滑稽感的自恋、犀利的自嘲。
就像我已然提到过的,马科斯的写作,尤其是杜里托的故事中充满了后现代的戏仿,而且贯穿着极为丰富的互文关系。事实上,在1995年初,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马科斯的萨帕塔公报中充满后现代式缤纷拼贴:他以英文引证莎士比亚,以法文引证波德莱尔、加缪,以原住民语言引证民间的歌吟,在他的书写中,间或出现印度哲人或《孙子兵法》。当然,在他的文字间不断涌现拉美诗人聂鲁达、本尼德蒂和不胜枚举的西班牙语诗人的诗作,同时充满了大众文化文本的旁征博引:墨西哥本土的诸多流行剧集、大众明星、系列电影或电视剧、好莱坞电影与流行歌(诸多论者提到马科斯无疑是个“电影迷”,而且萨帕塔社区也充满了有趣的电影文化:发电车巡回到不同的村落为孩子们放映卡通,为成人放映从欧洲艺术电影到本土流行影片的录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