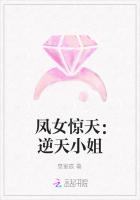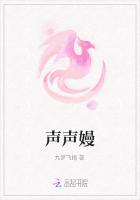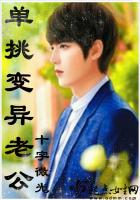例56.且说辗眼已是九月初二日。(第四十三回第527页)
“周按”说:“辗眼是原笔。”列藏本作“辗眼”,词义不可解。甲辰、程甲本作“转眼”,词义就显豁多了。
例57.茗烟道:“这可罢了,荒郊野外,那里有这个,既用这些东西,何不早说,带了来岂不便意。”(第四十三回第528页)
“周按”说:“便意,是原笔。”“便意”根本不成词。庚辰作“便宜”,这才可能是雪芹的原笔。
例58.
①凤姐见推不过,只得嗑了两钟。
②凤姐也难推脱,只得嗑了两口。
③好姐姐们,饶了我吧,我明日再嗑罢。
④我原不该来,不嗑,我们就走。
⑤好姐姐,我嗑就是了。(第四十四回第534页)
这五处,唯戚序本作“嗑”;庚辰本则作“喝”。嗑有三个读音,第一个kè,是常用读音,基本义有:说话,闲谈;用牙齿对咬有壳的或硬的东西;指上下牙齿对碰等等。第二个hé,基本义前两个分别是:闭合;何以,为什么;最后一个义项同“喝”。第三个xiá,意义是笑声。周氏选嗑而弃喝,从意义上讲不能算错。但在今天普通读者认识这个字只知其读音是kè,常用嗑瓜子、唠嗑儿等语,不知其读音hé,义同喝。这样周汝昌弃喝而选嗑就不合适了,套用他的话:喝是原笔,嗑是抄者的笔误。
例59.牛不嗑水强按头?(第四十六回第560页)
唯戚序本作“嗑”;庚辰本作“吃”;蒙府、程甲、列藏本作“喝水”。这再一次说明周汝昌校订时喜欢采用生僻字和冷僻义的嗜好。
例60.这一倍子也跳不出他的手中去,终久要报仇。(第四十六回第563页)
“周按”说:“一倍子,原笔,即一辈子。”原笔说荒唐得没名堂。“倍”字的本义是照原数等加,引申为增益、加倍、更加,通背、悖。又是“陪”的古字,同赔,就是没有同“辈”这个义项。虽然蒙府、列藏本作“倍”,但列藏本在“倍”字旁加竖杠,表示了怀疑;庚辰本径直改“倍”为“辈”,这就说明了问题。
例61.我这一倍子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第四十六回第563页)
这句“一倍子”列藏本在前一例“倍”字旁加竖杠,这里就径直点改为辈字,与庚辰本相同。“皇帝”前有个“宝”字,周氏莫名其妙地删掉这个字,使得全句称谓不统一,读到这里很别扭。
例62.我先走,你随后出来,跟我到下处,咱们提另嗑一夜酒。(第四十七回第572页)
“周按”说:“提另,口语,谓单独,个别的。”庚辰本作“替另喝”,列藏本同庚辰本。《汉语大词典》设词有“替另”,没有“提另”。解释“替另”:另外。《红楼梦》第一百零四回:“贾政回到自己屋内,王夫人等见过,宝玉、贾琏替另拜见。”续书的作者继承雪芹的替另一词,还在续书中继续使用这个词。
例63.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必真的。(第四十八回第581页)
“周按”说:“必真,是原笔。”“必真原笔”说根本不靠谱,庚辰本作“逼真”,是通行的正确用法,雪芹不会例外。
例64.来往的人都咤意。(第四十八回第583页)
“周按”说:“咤意,是原笔。”这也不可信。雪芹自觉创作通俗小说考虑的是让读者都懂得作品,不会用词的冷僻音、义来为难大家。戚序、戚宁本作“诧异”,周氏选择这两个本子的“嗑”,却不采用其中的“诧异”,确实让人诧异!
例65.仔细我们委曲著你。(第四十九回第590页)
“周按”说:“委曲即委屈,本书常混用。‘著’字是原笔。”列藏本作“委曲”;但庚辰本改“曲”作“屈”,“著”也作“着”。一个作家有着稳定的用词习惯,在表达一个意思上不可能混用词汇。委曲的基本义是弯曲;曲折延伸。引申义有:声音抑扬不绝貌;形容文词转折而含蓄;委婉、婉转;周全、调和;辗转周折;隐晦曲折等等。第16个也是最后一个义项才是“受到不应有的待遇或指责,心里难过”,才同“委屈”意义相同。试想想,天才作家曹雪芹怎么会混用这两个词汇呢!
例66.我已竟打发人笼地炕去了,(第四十九回第593页)
“周按”说:“已竟是原笔。”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列藏本作“已竟”,但庚辰本作“已经”。孰优孰劣,孰是误抄,不用我说了。
例67.后面一个媍人,打着青绸油伞。(第四十九回第594页)
“周按”说:“媍,是雪芹原笔,与‘妇’同。”“媍”与“妇”虽同音同义,说“媍”是“雪芹原笔”,只是周氏的一厢情愿,因为庚辰本就作“妇”。雪芹没有喜欢使用怪僻异体字的毛病,“媍人”又没有特别表现力,为啥放着通俗易晓的“妇”字不用偏偏要用“媍”呢!
例68.众人都笑道:“越是粗话越好,你说了,就只管干政事去罢。”(第五十回第597页)
“周按”说:“政事是原笔。谐音调侃,妙甚!”庚辰本作“干正事”;列藏本点“政”为“正”;蒙府、戚序、戚宁本均作“干正经事”。“芦雪广争联即景诗”前,凤姐被诗社隆重聘请担任监社御使,这次联诗又被郑重请来参加,她与姐妹们关系又好,众人为什么要调侃她?况且这只是临机对话,不是书面文章,怎知是“政事”而不是“正事”?
例69.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正是会作诗的起发,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第五十回第597页)
“周按”说:“起发,是原笔。其含义活且富。”甲辰、程甲、列藏三本作“起发”;庚辰本作“起法”;蒙府、戚序、戚宁本也作“起法”。其中正误,显而易见。“起发”是个有固定意义的词,《汉语大词典》有七义:1.犹启发。2.出发。3.征调、发送。4.诈取;捞取。5.犹起赃。6.起棺发丧。7.犹饱满。这个词确实“含义活且富”,但与作诗的“起法”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知识丰富的曹雪芹,怎会出此笑话式错误!
例70.你四妹妹那里煖火,我们到那里瞧瞧他的画儿,赶年可有了?(第五十回第604页)
“周按”说:“煖火,北语口中实音。”只有蒙府本一家作“煖火”。庚辰、列藏等本均作“煖和”。“煖火”与“煖和”音相同,但词义却不同,煖火,指取暖的火;煖和则指温暖,谓不冷也不太热。
例71.王夫人便觉失了膀臂,一个人能有多少精血?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张,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第五十五回第654页)
“周按”说:“精血,即精神同义语。”这完全是无根之谈。在诸多版本中仅梦稿本作“精血”。庚辰、己卯、列藏诸本均作“精神”。周氏取“精血”而弃“精神”语意就不通了。精血指精气和血液,此外无他义。而精神就不同了,有很多意义:1.指人的精气、元神。2.指人的意识。3.犹实质,要旨。4.精力体气。5.形容人或物有生气。6.心神;神志。7.风采神韵。8.精明;机警。9.神通。10.哲学名词。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精血怎能成为精神的同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