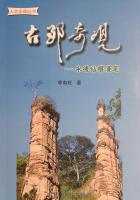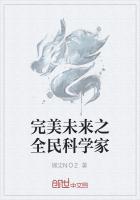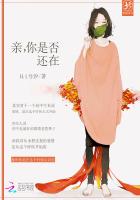例72.那四个女人都上四十往上年纪,穿带之物皆比主人不甚差迟。(第五十六回671页)
“周按”说:“差迟,即差池之义。”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这里仅仅蒙府本作“差迟”;庚辰、列藏等本都作“差别”。差迟与差池在“差错、意外”这个意义上是同义词;但差池有“差劲、不行”意义,则为差迟所没有。故而差迟在句中意思不通,应该是差别之误。周氏本的“穿带”在列藏本中作“穿戴”,“主人”在庚辰本中作“主子”,后者意思更准确些。
例73.女孩儿未出家,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就怎么变出许多的毛病来。(第五十九回第703页)
“周按”说:“出家,即‘出阁’、‘出门子’之义,指女儿外嫁。”这是明目张胆的欺人之谈。“出家”“出嫁”分别有不同的稳定意义。出家指:离开家庭;到寺庙道观里去做僧尼或道士;指出家之人。出嫁则指:女子离开母家与丈夫成婚;遣放宫女出宫嫁入。出家怎能指女儿外嫁?仅列藏本作“出家”;庚辰及其他本均作“出嫁”。
例74.投鼠忌器宝玉情赃判冤决狱平儿情权(第六十一回第718页)
这是第六十一回的回目。庚辰本回目与此相同。一般把前一个“情”字校订为“瞒”,把后一个“情”字校订为“行”,使这个回目成为“投鼠忌器宝玉瞒赃判冤决狱平儿行权”,词义准确明白得多了。蒙府、程甲本即是这个回目。
例75.莲花儿说:“司棋姐姐说了,要碗鸡蛋,顿的嫩嫩的。”(第六十一回第719页)
“周按”说:“顿是原笔。”庚辰本作顿;但是戚序、戚宁本却作“炖”。在《汉语大词典》中“顿”有41个义项,前六个义项分别是:以首叩地;指点头动作;以足跺地;以物触地,把一物猛地下放而碰撞另一物;叩击,敲打;顿仆,跌倒。我们每每看到顿字,常常想到的就是这些意义。只有在第38个义项才是用同“燉”。见了“顿”而能想到它的第38个义项是“燉”,普通读者是难以做到的。在雪芹时代加水用文火煮烂食品常用的词就是“燉”,《红楼梦》第八十七回有“给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汤……叫他们五儿瞅着燉呢”。戚序、戚宁本“炖的嫩嫩的”,“炖”与“燉”是同义词。我想雪芹用的恐怕是“炖”或者“燉”,绝非是“顿”。
例76.若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超近路从这里走。(第六十二回第731页)
“周按”说:“超近即抄近。”己卯本作“超近路”,这肯定不通,所以庚辰本点改“超”为“抄”;蒙府、甲辰本改作“走近路”;列藏本也点“超”为“抄”。“抄近”即走近路;“超近”没有这个意思,却为周汝昌所选留。
例77.深闺有奇女,绝世空珠翠。情痴苦泪多,未惜颜憔悴。哀哉千秋魂,薄命无二致。嗟彼桑间人,好丑非岂额。(第六十四回第758页)
这首诗见于列藏本第六十四回回前。诗后有周按:“既非出于雪芹,亦不类脂砚,词义沉痛而笔致凝重,非闺秀之文可知也。”既然如此,把这首诗选录在曹雪芹书稿的校订本子里就是错误的行为。更好笑的是在原抄本里已经把“岂额”点改为“其类”了,周氏怪癖的毛病不改,偏偏要采用不通的“岂额”:一是意思不通,二是不押韵,读起来非常拗口。
例78.赵姨娘素日深与彩霞契合,爬不得与了贾环,方有个膀臂。(第七十二回第851页)
“爬不得”错得不成词,用这样不通的文句欺弄读者,太不负责任。在庚辰本中点“爬”为“巴”,列藏本正抄作“巴不得”。雪芹原笔作“巴不得与了贾环”难道还有疑问吗?
例79.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看明白了。”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都看明白了。”(第七十四回第873页)
“周按”说:“下人等对探春不敢用翻、查等词,只言看了,是婉词也。”这种肤浅认识是没有读懂探春逼问的表现,不满足探春的要求她是不答应的。所以在庚辰本中凤姐的回答不是“看明白了”,而是“都搜察明白了”。列藏本凤姐的答话则是“都搜查明白了”。周瑞家的等赔笑的回答则分别是“都翻明白了”“都搜明白了”。不这样回答,探春就不会放过她们。所谓的婉词“看”既讲不通,不翻怎么看明白呢?另外情味也不够。
例80.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留下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信住两日,至今日未回,听得此信,爬不得又拐两个女孩子去作活使唤。(第七十七回第916页)
这回列藏本作“爬不得”。但是在列藏本第七十二回有“巴不得与了贾环”之句,应据以改正才好。坚持己见,就是不改“爬不得”,这就是周汝昌的行事风格。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的语言问题太多了。我用甲戌本第一回与周校第一回对勘,发现校订错误就有一百多处,于此可见问题的严重。本文只是就“周按”来谈错别字,其他错讹那就更多了,如果要细说,那得用专著才能完成任务。
在结束本文时还有几句题外话想说:出版方在宣传自己这个本子时说:“这是周先生对十余种古抄本进行了大汇校,恢复了曹雪芹的真笔原文,是迄今为止最为可靠的《红楼梦》版本。”这与实际反差太大了。出版社包装出版这种充斥错别字的低水平的书,是否应对曹雪芹负责?是否应对《红楼梦》负责?它对祖国语言的纯洁究竟起什么作用?责任编辑、特约编辑究竟认真阅读书稿没有?
参考文献
1.曹雪芹著,脂砚斋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2.曹雪芹著,脂砚斋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曹雪芹著,脂砚斋评.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曹雪芹著石头记(列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冯其庸主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第一至第五册)[M].北京:**************,1987—1989.
6.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