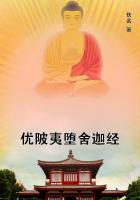尤三姐与尤二姐性格不同,美得也不同。三姐与二姐一样,都在抗争命运。二姐的抗争是安分随时地找一份归宿,寻求一份身外的庇护;三姐更多的是以主动攻击来进行自我保护,她始终有一种危机感,便是姐姐出嫁后,她也没有像二姐那样自以为终身有靠地放心,而是想到“他家现放着个极利害的女人,如今瞒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知道了,岂肯干休?势必有一场大闹。你二人不知谁生谁死,这如何便当作安身乐业的去处?”如果说尤二姐从始至终只扮演一种角色,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那么尤三姐则是在高难度的角色间进行转换。
三姐自视甚高,她说:“咱们金玉一般的人,白叫这两个现世宝沾污了去,也算无能!”这“金玉”一般的人,却没人拿她们当“金玉”,贾家兄弟不过是拿自己姐妹俩当“粉子”取乐,这是三姐认识到的残酷的现实。但三姐不是软弱的二姐,即使现实很无奈,她也要表现自己的才能,用自己的智慧战胜施加给自己的那种力量。但她没有别的资本,她只有把自己豁出去。于是,她顺水推舟地把贾家兄弟赋予的这种不堪的角色接过来,不把自己当持重贞洁的“大家闺秀”,更不把位高权重的贾家兄弟当回事儿了。她嬉笑怒骂,任意耍弄他们,把贾珍们享受的那种暧昧变成明显的挑逗与攻击,把每个人的遮羞布扯下来,使一切都变得赤裸裸的。她的做法出乎他们的意外,使得贾琏首先放弃了,而贾珍尽管不舍,也觉得更有味,可终究被她的那种“轻狂豪爽,目中无人”的气势逼住,不敢怎样了。
尤三姐这么做是在保护自己和姐姐,她使得贾珍他们不敢得寸进尺,心有所忌。一个女孩子把比生命还重要的贞洁豁出去了,而他们这时反倒想到了自己的脸面,他们是有身份的人。不然三姐的命运又能怎样呢?贾珍可能霸占住不放,但三姐却并不甘心作妾,更不甘心给贾珍这样的人做妾。最理解妹妹的还是尤二姐,当贾珍尚且不舍得放三姐嫁人时,二姐对贾琏说,“让他自己闹去;闹的无法,少不得聘他。”
应该说三姐的做法基本达到了目的,可是这些却是用和生命一样珍贵的个人贞洁名声来换取的。她保持着精神的纯洁,并且认为她的这一份纯洁坚贞会赢得真正平等的幸福爱情,这本身就注定了她悲剧的结局。
三姐在大闹一番,终于将贾珍他们逼退后,争得了自己自由选择爱人的权利。她忽然就变得非礼不动、非礼不言起来。她已经扫清了阻挡进入自己纯洁感情世界的外部环境,一心要用自己纯洁的精神和已经不受任何侵扰的身体守护并执著地等待着一份空茫而纯洁的爱情。那个看戏中偶然闯入尤三姐心灵的舞台上的柳湘莲,五年来却戏剧性地成为尤三姐精神的一部分。十几年不清不白的生活必要有一个完满的结局,给人生一个交代,给生命做一注解,不然,来世一遭又为什么呢?
谁都没有想到尤三姐等待的竟然是一贯素性爽侠萍踪浪迹,清高而冷漠的柳湘莲。贾琏想到的是宝玉,连二姐也觉得是。但只一提,便被三姐骂了回去:难到我们姐妹八个也要嫁你们弟兄八个不成?三姐是这浊世中开放的一朵另类的花朵,她看不起世人眼中的富贵荣华,却倾尽全部的生命热情守望一份不知结果的爱情。但是,她对宝玉却没有俗人的成见,独具慧眼在只言片语和行为中看出宝玉的与众不同。
闲聊时,兴儿发议论说到宝玉是一个糊涂没用的人,尤二姐随声附和地说,“我们看他倒好,原来这样。可惜了儿的一个好胎子!”这时尤三姐却反驳道:“姐姐信他胡说……要说糊涂,那些儿糊涂……原来他在女孩儿跟前,不管什么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们不知道。”
在宁府办贾敬的丧事,和尚们做法事时,尤家姐妹站在那里。宝玉却很没眼力劲地挡在别人前面,甚至听任别人的抱怨也不躲避。只有三姐知道,他那是怕那些和尚们的气味熏了这姐妹俩,宁肯自己挡在前面。而在贾母游大观园时曾经说过:“只有两个玉儿可恶,回来喝醉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可知,连贾母也知道宝玉是爱清洁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尤家姐妹面前充当了护花使者。三姐在短暂的人生中,是从不曾得到过来自男人的尊重与爱护的。只此一件小事,就足以让三姐感念。
三姐对宝玉的看法,恐怕连许多身边的人也不及,可谓宝玉的知己。但三姐的梦想,却断送在了宝玉一句无心的话上:“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尤物”二字从宝玉笑嘻嘻的口里说出来,多少带了些不庄重。冷二郎一听,心重又冷下来。宁府的石狮子尚且不干净,何况一对尤物?
爱情没了,希望瞬间破灭。三姐眼前一片空茫,于是,她挥剑结束了她的梦。我所遗憾的是没有看到三姐如何与凤姐斗,当然,也许曹雪芹先生早知道三姐的必败无疑,恐网不破鱼死,倒不如让她为一个情字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