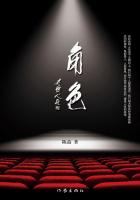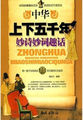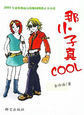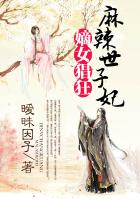刘老老第一次进荣国府是下了决心,鼓了勇气,厚了脸皮要了二十两银子回去。本是冲着原来王家的二姑娘去的,到了荣府只见了王家下一代的凤丫头。凤姐对刘老老完全没印象,神情里透着爱答不理的倨傲,于是让周瑞家的去回王夫人。听明白了缘故,也只是说:“怪道既是一家子,我怎么连影儿也不知道。”然后,凤姐还先抱怨了一番“大有大的难处”的搪塞话,害得刘老老又羞愧又担心了一番,才得到二十两银子,拿回家去过冬。
刘老老二次来情境就大不一样了,首先她不是空手来要东西的,而是带了新鲜蔬菜送礼来了,只从刘老老兴高采烈的话里,便可听出那一份有所回报的喜悦与自得。况是第二次来,诚惶诚恐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走亲戚的亲切与自然——当然,刘老老清楚这亲戚也不能太亲近,所以刘老老把菜放下就准备走。偏偏荣国府为刘老老敞开了大门,老太太听到来了一位乡下老太太,便要留下这个会“说古”的同龄人。整日与小孙子孙女的玩笑,到底有代沟,少些共同语言,何况荣国府的空气不流动,难免滞涩,来个乡下老太太,立马带来一股乡野的新鲜空气。于是,这个连老祖宗也没怎么游览的大观园,便因了刘老老而全部展现出来了。其实这次最大不同在于,刘老老没打算再要银子反而得了很多,不仅有银子,还有东西。在平儿那是半炕的东西,只瓜果之类的就装了满满两口袋,鸳鸯那又得了两包袱。别人只管送东西,只有王夫人想得周到,出手更大方,给了一百两银子,要她“或者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王夫人此时显示了她的慈悲,话里透着体贴与周到。别人的扶贫都是解决一时困难,即时消费,而王夫人的扶贫是给予资金支持,鼓励靠自己发家致富,这也免去了投亲靠友的屈辱。这才是脱贫的长远之道。
王夫人指了两条道:一是经商,一是置地。刘老老一家选择了后者。荣府破败时,刘老老再一次出现。她对病榻上的凤姐表示着感激:我们若不仗着姑奶奶,他的老子娘就饿死了。同时汇报了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今虽说是庄家人苦,家里也挣了好几亩地,又打了一眼井,种些菜蔬瓜果,一年卖的钱也不少,尽够他们嚼吃的了。”
中国传统观念里的等级制度是士农工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学而优则仕,士是首选。贾雨村落魄时也从没有想到去做别的生计,只是卖画筹集路费,等待机会参加科考,然后为官做宰。所以当中秋之夜被甄士隐三更天资助了五十两银子,他五更天便起程赶考去了。经商是被看作下流阶层的。经商考虑的是取利,儒家讲的是济世,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自然君子是不屑于这种直接获利的行业的,但却不反对通过仕途之道达到荣华富贵。司马迁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史学家,他的《史记》中有一篇《货殖列传》,提到了有别于宝钗的“经济之道”,却没有多少人重视这篇文章。穷人是管不了这些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大事情,刘老老看女婿愁眉苦脸就曾出过主意: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终是天子脚下。这长安城中,遍地皆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刘老老这话与现今提倡的借助地域优势发展经济是一个道理,刘老老说这话的意思不是乞讨,想来是指做城里人生意。但刘老老没本钱,这才去大户人家要。一百零八两银子,刘老老还是没做买卖。刘老老的观念里,是“守着多大碗吃多大饭”的安稳,没想过要大富大贵,而祖上也曾做过官的狗儿的观念里大概觉得务农还是比经商更体面一些,于是,买了几亩地,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