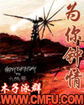《红楼梦》人物的病多是胎里带,与生俱来,病重者为黛玉,其次当为宝钗。黛玉之病病得也如其性格,鲜明而尖利。宝钗之病病得也如其本人,含蓄而又不影响什么。
黛玉初进荣国府时,每个人都看出来了:黛玉有不足之症。到了后来,黛玉病得更是人人皆知。可是宝钗来后,大家看到的是她的品格端方,容貌美丽,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人人都说黛玉不及。宝钗的病,只被周瑞家的发现了。在以后的生活中,谁也没有特别注意宝钗的病。
对于黛玉的病,除了胎里带来是潜伏期,表现形式是弱,只有到了宝玉挨打,黛玉探望,宝玉赠旧帕后,黛玉深感宝玉深情,写下三首爱情诗,脸上泛红,艳比桃花,这时才真正发病。放风筝时,大家说林姑娘的病根也去除了。这自然是指身体上的,五十七回中,紫鹃为试宝玉对黛玉之情,谎说林姑娘要回苏州去了,宝玉听了正在发怔,晴雯找了来,紫鹃说“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这话真是一语双关。但黛玉的病本可不治自癒的,像癞头和尚所说,只要不见外亲,便可平安了此一生。黛玉本就为爱而来,若不见,岂不虚度一生?所以黛玉之病本来能好,但却终于不治。
宝钗的病却与爱无关。她的病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这种病好治,但又不好治。好治是因为病发时,“吃一丸就好了”。不好治是因为去不了病根,反反复复发作,而且“要是吃凡药,是不中用的”。所以,宝钗吃的这种丸药,是一位和尚给的“海上仙方”,叫“冷香丸”。
“冷香丸”的成分非常有趣: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夏天开的白荷花蕊,秋天的白芙蓉蕊,冬天的白梅花蕊,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霜降这日的霜,小雪这日的雪。这些东西除了白色,便是冷寒之物。这些东西显然是一种象征物,白色代表纯洁、高洁,以冷寒高洁之物,克制宝钗的热毒。
宝钗的花名签上写道:“任是无情也动人”,宝玉拿着这根签看了很久,玩味再三,直到性子急躁的湘云劈手夺了去。宝钗的“无情”使她显得冷,她对金钏、尤三姐的死没有表达丝毫的怜惜,甚至连一点好奇都没有,对于有恩于哥哥的柳湘莲的出家薛蟠都哭得眼睛红了,宝钗却不以为然。她的住处也显得冷,一块玲珑巨石挡住了一切。这一切,都说明宝钗已经够冷了,怎么还有热毒当治呢?
作者借宝玉之口多次对男人的功利世俗之心表示不满,把一腔热爱倾注在女儿身上,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红楼梦》中的女儿们是作者理想中的女子,若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薛宝钗当是一个现实中的完人。她的才干,她的聪明,她的学识,她的世事洞明,无不让人叹为观止。但这样一个女子,正如作者对其他人的态度一样,她也是不完美的。而且作者借贾宝玉的眼光看来,她身上沾染着一些世俗的东西,这和黛玉的病是完全不同的。黛玉代表着一种理想追求,但“过洁世同嫌”,这不只是妙玉的“毛病”,而且黛玉身上也有这种倾向,表现在生活中,便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因为这种看上去比较孤僻的行为,不容易被人理解与接受,更使黛玉时时处于紧张的状态,这又激发了本能的敏感。人敏感则承受力就小,承受力小就更敏感,这种敏感有时便处于病态。尤二姐雪肤花肠,受不得众人的揉搓,自己结束了生命。黛玉生活中并没受多少委屈,但那种多愁善感的心思,便是风刀霜剑般地残酷,也注定了生命理想状态的脆弱。宝钗却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世俗之望凡俗之心,热衷于经济之道,以及世故的处世方式。而这对于作者歌颂的女儿的纯洁性来说,无疑是一种瑕疵。宝钗之所以让人更多地看到她的优点,感觉到她的好,是因为她知书达理,学识渊博,天生成一种平和淡雅的性情,虽不像黛玉那般清洁,也算得不俗,因而“先天壮,还不相干”。抵抗能力强,不致完全落到“国贼禄鬼之流”中去。何况宝钗乃是一闺中女子,她再热衷仕途经济也难展宏图大志。而她对人的热肠却能带来温暖,一味说冷是病或热是病都不能概括其全貌。作者对这个人物很珍爱,但她仍然是不完美的,便借“冷香丸”来使这个女子彻底回归到清洁、纯粹与完美上来。
钗黛二人的病,只需记住这两个细节就可看出:
黛玉从苏州回来,宝玉赶紧把北静王所赠的鹡苓香串转送给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
宝玉奉元妃之命作诗,宝钗因贵人不喜“玉”字,提醒他不要用,又提示他改用“蜡”字就好,宝玉这才洞开心意,对宝钗很感激,说:“姐姐真是‘一字师’了!从此只叫你师傅,再不叫姐姐了。”宝钗悄悄笑道:“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