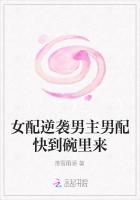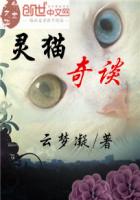对于凡人来说,情与色总是相连的,或相处久了,因情生色;或因色动情,一见钟情。贾宝玉虽是天界而来,到底是顽石本质,况且本就要立意来人世受享一番,对于情与色皆来之不拒,所以小时自谓“绛洞花主”。处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花红柳绿的芳菲世界,宝玉对黛玉却始终真情不变,原因一是黛玉色既极佳,其风流袅娜,使花花公子薛蟠一见之下就酥了半边身子。二是二人相处既久,耳鬓厮磨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过来的,那情丝的生成也非一日之功。这两条既然都占了,别的女孩再好恐也难破门而入。但感情的事有时是瞬间的变化,色色不同,焉知这一色不比那一色更好?情更容易易,此时情非彼时情也。所以,纳兰容若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若说宝玉对别的女孩子只是笼统地想做护花使者,对于艳冠群芳的薛宝钗还是动过感情,这两次感情也没有脱离“情色”二字。
第一次完全是感官上的,属于色的范围。元妃赏下端午节的礼物,宝玉发现自己的和林妹妹的不一样,反倒和宝钗的相同,不禁诧异。黛玉自然领会到其中的意思,只有跟宝玉生气的份儿。可巧这日闲坐时宝玉看到宝钗戴着元妃所赐的香串子,便要看看。宝钗因生得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却把宝玉的注意力给吸引过来了。于是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想“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姑娘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没福”。黛玉已经为这事生气了,宝玉却还没意识到这个膀子是有可能摸一摸的。从这一细节,可知宝玉确实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惦记着黛玉,虽然所有的花都喜欢,但我只取这一枝;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宝玉也算得痴情了。但宝玉还是看呆了。若说没情也不对,宝钗的妩媚风流还是在宝玉心里难以忘怀,他后来写的文章里,就提到了“戕其(宝钗)仙姿”了,可见这色的力量。
第二次属于情的范畴。宝玉挨打后,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来看他。“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宝钗是很少动感情的,这一点宝玉肯定了解,这唯一一次的真情流露却是对着宝玉而来。如此亲切又“大有深意”的话,如何能让本就多情的宝玉不感动呢?宝钗的情恰使她的色更出众,更激发宝玉的爱意。在宝玉看来宝钗日常不见的“那一种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之情,竟难以言语形容,越觉心中感动,将疼痛早已丢在九霄云外去了”。这种止痛功能的功效当真了得,现在医学该当推广应用。
但最终宝玉对宝钗还是不能产生爱情,根本原因在于二人的人生态度。宝玉是“情不情”之人,而宝钗缺少的恰好是情。宝玉对宝钗的喜欢,色占了很大成分。宝玉因生活中种种烦恼,不禁产生灰心之意,他在续《庄子》文中写道:“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在宝玉看来,没有这些美的存在与吸引,就不会产生情意,而没有情意,就没有痛苦。但对于宝钗和黛玉美的看法还是不同的,宝钗是“仙姿”,而黛玉是“灵窍”。仙姿引发的是感观上的美感,“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灵窍却是一种心灵的吸引,“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在这两者的选择中,就像中国的文人一样,对心灵的关注更重。贾宝玉鄙弃仕途经济之道,独钟情女儿世界,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女儿的世界是清洁的、自然的、未被世俗熏染的、纯洁而充满灵性的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中,林黛玉无疑是最具有女儿性的,她的身上带有天然的神性与诗性,虽然弱,却充满着生命热情,她的天真烂漫,她的心无渣滓,她或喜或怒或痴或嗔时的举手投足,都出自本心而毫不做作。这样一种真趣,又怎能不让本就厌恶男人身上那种世俗功利之心的宝玉喜欢呢?宝玉不通世务,却丝毫不缺少对女孩那种相当高的鉴赏力。即使黛玉小性,那也掩不住她发自生命本身的那种天然的光芒。宝钗虽然给许多人带来了温暖,但她的行为举止总让人觉得缺少了点女孩的天真,那种成熟超越了青春。正是这种超越,应合了世俗的道德标准,却远离了天性。这让宝玉很失望:“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也因此,那种转瞬即逝的喜爱的光芒无法成为照彻宝玉的灵魂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