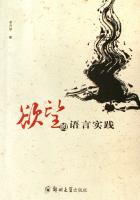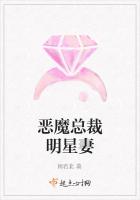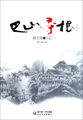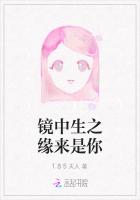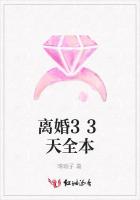焦大在贾家的资格最老,论功劳也最大。是他把主子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背出来也不一定能活下来,问题是他还把仅有的水和粮食给主子吃喝,而他自己却喝马尿。后来的下人再没有过那样的机会,也没有过那样忠心耿耿舍生忘死的行为。这也是焦大颇引以为豪的事。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被追杀,只好逃到别的国家避难。日暮途穷之际,人的最重要、最迫切的愿望总是与那个最原始的生存需求有关,种种的理想与抱负全变成了对一餐一饭的奢求。重耳饿得两眼发花之时,大概人肉也是吃得的。于是,跟他一起出逃吃苦受累的介子推便贡献了自己的一块肉。后来重耳经历重重磨难回到晋国,终于执掌了国家大权,跟随他的人一律论功行赏,却独独把吃了人家肉的介子推给忘记了。等重耳被人提醒想起来的时候,介子推早已心灰意冷带着老母到绵山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去了。后来的事情基本上就家喻户晓了,因为有个“寒食节”据说就是纪念这位先生的,主要原因是重耳放火烧山想逼介子推出来,结果就把介子推给烧死了。
这像是一个寓言,那些老实巴交太过忠心而又不喜欢张扬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人。焦大在贾府一直混得不怎么样,直到贾家孙子重孙子辈的人当政,焦大以其七老八十的年纪,竟然还在贾府当最低级的差,被赖二总管管着,而且那帮势利小人竟然还欺软怕硬,派这样一个老人夜里送秦钟回家,怎么说也是欺负人。
想当初焦大是何等一个刚强的汉子,死人堆里逃出来的啊,跷起一条腿都比别人头高些。现在连自己都把自己归在了“软”之列,听了让人心寒。贾家的人不报恩,似乎从他们的主子那里就传下来了,不然何不让焦大退养呢?那赖嬷嬷不过是当过奶妈,贾家人吃过她的奶,自己养老退休,她的子孙还都进入了贾府的管理层,到贾家串个门,随便替人说句话,凤姐还要卖她一个人情,放过了周瑞家的不争气的儿子。不仅如此,她还有了自己带小花园的房子,在自己家也老封君似的被子孙家人侍奉着,她的孙子从小也是锦衣玉食,花的银子也够打一个银人了,长大了,还接受了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当了一县父母官,生活可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是焦大,贾家人怎么能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呢?怎么焦大就混到这么不入流的地步呢?
焦大当初实在该借着那点主子还没忘恩情的热乎劲跟贾家搞好关系,但焦大也许因为自己死里逃生,比起战场上死的战友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人便变得没有那么多欲望了,有吃有喝有住有活干就心满意足了。但后来我又想,以尤氏、贾蓉的话来看,连贾珍都让他三分,可见也并没有完全忘记他的功劳。那么,也许当初焦大还是被提拔过的,可惜焦大不能与时俱进,总是拿战争年代的那点事来约束别人,教育别人,使得大家都对他挺反感,而他自己虽然逞之一时之勇,救了主子,却没有文化,又不学习新知识、积极要求进步,结果不能胜任管理工作,于是只好让他继续当差,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焦大最大的失误可能在于太认真,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太把自己功劳夸大,以至于模糊了主子与奴才的那种分明的界线,以为没有自己最初救出的“母鸡”,哪会有后来鸡生蛋,蛋生鸡,这么繁荣昌盛的后代呢?他的这种观念带有片面性,若在主子们看来,可能的观点是:如果主子不活着,他何以安生呢?甄家败落了,一身功夫勇力十足的包勇被主子格外看顾,推荐到了贾家当差安身。这便是赖嬷嬷的想法与高见,人家虽然奉献了奶,可是知道没有自己的奉献,她自己的孩子也没饭吃,于是倒是她感恩贾家赏了一碗饭吃。她就自始至终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以功臣自居。这一谦卑,便引得贾家上上下下人等的好感,来了,赏把椅子坐,周围也围着一帮人说笑,觉得自己到底荣耀,不像焦大把人家的老底都搬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英雄也有走麦城的羞耻,惹得自己到老了还是孤寡一人,没人待见。
不过,焦大骂归骂,那骂可是为了贾家好。焦大虽然过过最艰苦的岁月,可也经过贾家最繁华的时候,到了现在眼睁睁看贾家走下坡路,那份心里的着急竟比主子还切,无论如何做不到冷眼旁观,更做不到一味歌功颂德,所以,鲁迅先生说,这焦大倒是贾府里的屈原。当然,焦大远不如屈原,屈原的一腔忧愤化作了锦绣文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精神至洁者,被人顶礼膜拜,死后荣耀也算光芒四射。而焦大的忧愤变做了“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的人身攻击,且别说他攻击的是主子,就是普通人也会闹到法庭上去。连小丫头坠儿都知道“谁管谁的筋疼”的道理,焦大一辈子愣没弄明白。管了,焦大就完成了一个从主动喝马尿到被动被灌一嘴马粪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