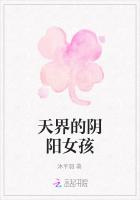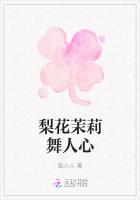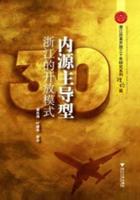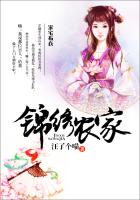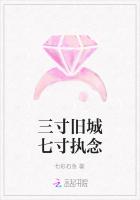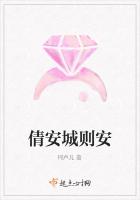曰﹕老、庄、释以其所谓「真宰」「真空」者为「完全自足」,然不能谓天下之人有善而无恶,有智而无愚也,因举善与智而毁訾之。老氏云:「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又云:「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褔。」又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彼盖以无欲而静,则超乎善恶之上,智乃不如愚,故直云「绝学」,又(生)〔主〕「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此一说也。荀子以礼义生于圣心,常人学然后能明于礼义,若顺其自然,则生争夺。弗学而能,乃属之性;学而后能,不得属之性,故谓性恶。而其于孟子言性善也辩之曰:「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义矣。」此又一说也。荀子习闻当时杂乎老、庄、告子之说者废学毁礼义,而不达孟子性善之旨,以礼义为圣人教天下制其性,使不至争夺,而不知礼义之所由名。老、庄、告子及后之释氏,乃言如荀子所谓「去圣王,息礼义」耳。程子、朱子谓气禀之外,天与之以理,非生知安行之圣人,未有不污坏其受于天之理者也,学而后此理渐明,复其初之所受。是天下之人,虽有所受于天之理,而皆不殊于无有,此又一说也。今富者遗其子粟千钟,贫者无升斗之遗;贫者之子取之宫中无有,因日以其力致升斗之粟;富者之子亦必如彼之日以其力致之,而曰所致者即其宫中者也,说必不可通,故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如程子云「敬以治之,使复如旧」,而不及学;朱子于中庸「致中和」,犹以为「戒惧慎独」。】陆子静、王文成诸人,推本老、庄、释氏之所谓「真宰」「真空」者,以为即全乎圣智仁义,即全乎理,【陆子静云﹕「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何有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刚强毅。」王文成云:「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妍媸之来,随物现形,而明镜曾无所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以)〔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无所住』处。」】此又一说也。程子、朱子、就老、庄、释氏所指者,转其说以言夫理,非援儒而入释,误以释氏之言杂人于儒耳;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就老、庄、释氏所指者,即以理实之,是乃援儒以入于释者也。试以人之形体与人之德性比而论之,形体始乎幼小,终乎长大;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其形体之长大也,资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初」;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人物以类区分,而人所禀受,其气清明,异于禽兽之不可开通。然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老、庄、释氏谓有生皆同,故主于去****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扩充之。在老、庄、释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毁訾仁义以伸其说。荀子谓常人之性,学然后知礼义,其说亦足以伸。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同于老、庄、释氏,而改其毁訾仁义者,以为自然全乎仁义,巧于伸其说者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为天与我,犹荀子尊礼义以为圣人与我也。谓理为形气所污坏,是圣人而下形气皆大不美,即荀子性恶之说也;而其所谓理,别为凑泊附着之一物,犹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之凑泊附着于形体也。理既完全自足,难于言学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气为二本而咎形气。盖其说杂糅傅合而成,令学者眩惑其中,虽六经、孔、孟之言具在,咸习非胜是,不复求通。呜呼,吾何敢默而息乎!
问:程伯子之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见叔子所撰行状。而朱子年四十内外,犹驰心空妙,其后有答汪尚书书,言「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而一二年来,心独有所自安,虽未能即有诸己,然欲复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虽从事释氏甚久,然终能觉其非矣,而又未合于六经、孔、孟,则其学何学欤?
曰:程子、朱子其出入于老、释,皆以求道也,使见其道为是,虽人以为非而不顾。其初非背六经、孔、孟而信彼也,于此不得其解,而见彼之捐弃物欲,返观内照,近于切己体察,为之,亦能使思虑渐清,因而冀得之为衡(鉴)事物之本。然极其致,所谓「明心见性」、「还其神之本体」者,即本体得矣,以为如此便足,无欠阙矣,实动辄差谬。在老、庄、释氏固不论差谬与否,而程子、朱子求道之心,久之知其不可恃以衡鉴事物,故终谓其非也。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老氏言「致虚极,守静笃」,言「道法自然」,释氏亦不出此,皆起于自私,使其神离形体而长存。【老氏言「长生久视」,以死为「返其真」;所谓长生者,形化而神长存也;释氏言「不生不减」;所谓不生者,不受形而生也;不减者,即其神长存也。】其所谓性,所谓道,专主所谓神者为言。邵子云:「道与一,神之强名也。」又云:「神无方而性有质。」又云:「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人之神即天地之神。」合其言观之,得于老庄最深。所谓道者,指天地之「神无方」也;所谓性者,指人之「(神)〔性〕有质」也,故曰「道之形体」。邵子又云:「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此显指神宅于心,故曰「心者,性之郛郭」。邵子又云:「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故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也」。此显指神乘乎气而资气以养。【王文成云﹕「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立说亦同。又即导善家所云「神之炯炯而不昧者为性,气之缊絪而不息者为命」。】朱子于其指神为道、指神为性者,若转以言夫理。张子云:「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知觉,有心之名。」其所谓虚,六经、孔、孟无是言也。张子又云:「神者,太虚妙应之目。」又云:「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又云:「神,天德;化,天道。」是其曰虚曰天,不离乎所谓神者。彼老、庄、释氏之自贵其神,亦以为妙应,为冲虚,为足乎天德矣。【如云﹕「性周法界,净智圆妙,体自空寂。」】张子又云:「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斯言也,盖得之矣。试验诸人物,耳目百体,会归于心;心者,合一不测之神也。天地间百物生生,无非推本阴阳。易曰:「精气为物。」曾子曰:「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因其神灵,故不徒曰气而称之曰精气。老、庄、释氏之谬,乃于此岐而分之。内其神而外形体,徒以形体为传舍,以举凡血气之欲、君臣之义,父子昆弟夫妇之亲,悉起于有形体以后,而神至虚静,无欲无为。在老、庄、释氏徒见于自然,故以神为已足。程子、朱子见于六经、孔、孟之言理义,归于必然不可易,非老、庄、释氏所能及,因尊之以当其所谓神者为生阳生阴之本,而别于阴阳;为人物之性,而别于气质;反指孔、孟所谓道者非道,所谓性者非性。独张子之说,可以分别录之,言「由气化,有道之名」,言「化,天道」,言「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此数语者,圣人复起,无以易也。张子见于必然之为理,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诚如是言,不以理为别如一物,于六经、孔、孟近矣。就天地言之,化,其生生也;神,其主宰也,不可歧而分也。故言化则赅神,言神亦赅化;由化以知神,由化与衶以知德;德也者,天地之中正也。就人言之,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虽自圣人而下,明昧各殊,皆可学以牖其昧而进于明。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性专属之神,则视形体为假合;以性专属之理,则苟非生知之圣人,不得咎其气质,皆二本故也。老、庄、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此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朱子答吕子约书曰:「阴阳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万象纷罗者也。是数者各有当然之理,即所谓道也,当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无朕者也。」然则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皆仅及事物而即谓之道,岂圣贤之立言,不若朱子言之辨析欤?圣人顺其血气之欲,则为相生养之道,于是视人犹己,则忠;以己推之,则恕;忧乐于人,则仁;出于正,不出于邪,则义;恭敬不侮慢,则礼;无差谬之失,则智;曰忠恕,曰仁义礼智,岂有他哉?常人之欲,纵之至于邪僻,至于争夺作乱;圣人之欲,无非懿德。欲同也,善不善之殊致若此。欲者,血气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悦理义者,未能尽得理合义耳。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夫人之生也,血气心知而已矣。老、庄、释氏见常人任其血气之自然之不可,而静以养其心知之自然;于心知之自然谓之性,血气之自然谓之欲,说虽巧变,要不过分血气心知为二本。荀子见常人之心知,而以礼义为圣心:见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进以礼义之必然;于血气心知之自然谓之性,于礼义之必然谓之教;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矣,而不得礼义之本。程子、朱子见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进以理之必然;于血气心知之自然谓之气质,于理之必然谓之性,亦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矣,而更增一本。分血气心知为二本者,程子斥之曰「异端本心」,而其增一本也,则曰「吾儒本天。」如其说,是心之为心,人也,非天也;性之为性,天也,非人也。以天别于人,实以性为别于人也。人之为人,性之为性,判若彼此,自程子、朱子始,告子言「以人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孟子必辨之,为其戕贼一物而为之也,况判若彼此,岂有不戕贼者哉!盖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其学非出于荀子,而偶与荀子合,故彼以为恶者,此亦咎之;彼以为出于圣人者,此以为出于天。出于天与出于圣人岂有异乎!天下惟一本,无所外。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有血气心知,则发乎血气之知自然者,明之尽,使无几微之失,斯无往非仁义,一本然也。苟岐而二之,未有不外其一者。六经、孔、孟而下,有荀子矣,有老、庄.释氏矣,然六经、孔,孟之道犹在也。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
孟子字羲疏证卷中
天道四条
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称。【诗载驰:「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毛传云:「行,道也。」竹竿﹕「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郑笺云:「行,道也。」】举阴阳则赅五行,阴阳各具五行也;举五行即赅阴阳,五行各有阴阳也。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言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有实体,故可分;惟分也,故不齐。古人言性惟本于天道如是。
问: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子云:「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止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后儒言道,多得之此。朱子云:「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谓也。」朱子此言,以道之称惟理足以当之。今但曰「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乃程、朱所目为形而下者;其说据易之言以为言,是以学者信之。然则易之解可得闻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