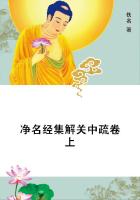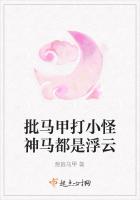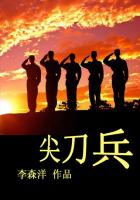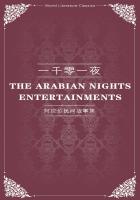《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歧《孟子题词》云:“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问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余按:谓《孟子》一书为公孙丑、万章所纂述者,近是;谓孟子与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则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於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如梁惠王、襄王、齐宣王、鲁平公、邹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称其谥,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日子,三也。细玩此书,盖孟子之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今正之。
孟子门人之功
按:孟子门人尚多,然多无事迹可纪。独乐正子,孟子屡称之,又尝荐孟子於鲁平公。至於问答之言则万章、公孙丑为多,故说者以此书为二子所撰述;《史记》虽但称万章,然既云“之徒”则固已括之矣。盖孟子之见尊信於当时,乐正子或不为无功,而其言之传於後世则二子实有微劳焉。是皆不可没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附记孟子弟子
称子者三人: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
按:乐正子之贤见於答公孙丑、浩生不害之问,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辩”、“性善”之间其所关者亦钜,“饮汤饮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既屋庐子之‘得间’,亦留心学问者。皆高第弟子也。
称名者三人:万章、公孙丑、充虞。
万章、公孙丑问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备述之矣。亢虞问答虽少,然“去齐”之问见孟子救世之苦心,“止赢”之问见人子爱亲之至情,亦卓卓不群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或称子或称名者二人:陈臻亦称陈子,徐辟亦称徐子。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见殊少。然“何如则仕”之问乃圣贤去就之大节,“兼金”之问亦因以见辞受之不苟。盖皆乐正、万章诸人之次也。
不知果为弟子与否者四人:陈代、彭更、咸丘蒙、桃应。
此四人,《集注》皆以为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问,他无所见,未敢决其必为弟子也。故附次於诸弟子之後。
附《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辐,粲然靡所不载。”(赵岐《孟子题词》)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正》(此似《外》四篇之名,文字似有讹误)。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仿而之者也。”(同上)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後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
按:《汉书》刘歆九种(颉刚按:“九种”既《六艺略》)《孟子》有十一卷,则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赵氏乃独能分别其真伪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如一,其功大矣。故今特表之。惟谓孟子“耻没世而无闻”,自撰此书,尚未尽合。阅者不以噎废食可也。
附韩文公称述孟子三则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原道》)
“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与孟尚书书》)
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某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太原王埙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埙秀才序》)
按:孟子在战国时,人视之与诸子等耳。汉兴,始立於学官,然亦不久遂废,人亦不过以传记视之耳。自韩子出,极力推崇孟子,其书始大著於世。至宋诺儒,遂以此七篇与诸经《论语》并重,皆自韩子之发之也。非孟子则孔子之道不详,非韩子则孟子之书不著,故今附录此三则於《孟子事实录》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附论孟子性善之旨
论性六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孔、孟之论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恶之说,扬子始有善恶混之说。逮唐韩子,乃合而折其衷,谓人性有三品,善与恶皆有之;孟子之与荀、扬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异其名,谓有理义之性,有气质之性;孔子所谓“相近”,兼气质而言之;孟子则专以理义言性,故谓之“善”也。
人性兼理义及气质而成
余谓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义,兼气质而成,不容分以为二。孟子之所谓性,既孔子之所谓性;但孟子之时异端并出,皆以性为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说辞而辟之非舆孔子为两义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声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纯乎理义,又何“忍”焉? 孟子之於性,何尝不兼气质而言之乎!盖孟子所谓性善,特统言之;若析言之,则善之中亦有深浅醇漓之分焉,非兼气质而言遂不得为善也。故《传》曰“纯粹至善者也”,《记》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则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犹未底乎纯也。故性虽同一善而不能无异焉,岂惟三品,盖十品有不能尽者。然谓之为恶则不可。譬之人参性补,肉桂之性能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谓其力有厚薄则有之矣。若谓人参性泻,肉桂性寒,则无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谓性为善,诚然无可疑者,韩子不必驳而程子亦不必曲为解也。
越椒、食我之性恶出於附会
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预知其当灭宗,此自好事者附会之词耳。《春秋传》中此类甚多:陈敬仲之生也预知其必有齐,叔孙豹之生也预知其为竖牛所乱,亦将尽以为实事乎!况食我初未尝为恶,但以国乱无政,大臣黩货,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时,遂至食我为所累耳。据此遂谓食我性恶,误矣。据此以驳孟子性善之论,则尤误之甚也。
评韩、程之论
大抵韩子、程子之论,其於性皆实有所见而措语皆不能无疵。谓有理义之性,有气质之性,何若谓有性之理义,有性之气质,不分性而二之之为善也!谓上焉者善,下焉者恶,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为得宜也!学者当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说为疑也。至如荀、扬之论,则不过务新尚怪,苟求自异,君子所不屑道,亦无庸深辨也。
附辨羊舌食我事
又按:《传》所载羊舌食我之事甚属可疑。夏徵舒以宣十年弑陈灵,夏姬之齿长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馀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异事也已。羊舌职以襄三年卒,其子伯华已为祁奚所知,嗣父为中军尉,而叔向复有弟叔虎、叔罴、叔鱼,则叔向之齿亦长矣,故《晋语》有叔向为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应至是始娶;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计之,平公既长,亦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强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颇远,疑即叔虎之事而传之者异词,或以为叔鱼,或以为食我,作书者遂取而兼载之耳。如正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却至亦从郑伯;子产欲毁游氏之庙而中止,一在葬简公时,一在为搜除时也。传记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恐未可尽以为实也。而‘母多庶鲜,惩舅氏’之语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贤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胜通室宁当不问!不过晋侯信谗,荀跞纳贿,遂至於贾祸耳。观叔游所言“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无道立矣,子惧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为非也。况食我自祖父以来与祁氏三世同官,相亲相近乃事之常,岂得谓之“助乱”!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难。”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贾祸也。以叔向之贤犹几死於栾盈之难,况盈与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将使人皆疏远方正之士,夤缘权势主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 吾每读书至此,未尝不叹後人莫有肯为食我辨其诬者,故今因论韩子《原性》而附辨之。《左传》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附读《孟子》馀说一则
孟子曰:“居(《中庸》作‘在’)下位而(《中庸》无此字)不获於(《中庸》作‘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获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友’上有‘朋’字)。弗(《中庸》作‘不’)获於(《中庸》作‘乎’)上矣。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朋友’)有道;事亲弗悦(《中庸》作,‘不顺乎亲’)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乎朋友夫’)。悦亲(《中庸》作‘顺手亲’)有道;反(《中庸》‘反’下有‘诸’字)身不诚,不悦於(《中庸》作‘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中庸》作‘乎’)身矣。是故(《中庸》无些二字)诚者,天之道也;思诚(《中庸》作‘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交至此止)。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中庸》袭《孟子》之证
此章文又见於《中庸》,与此大同小异。“居”之作“在”,盖因一时语言之异,如《论语》之“斯”,《大学》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实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友”之加“朋”,文亦可省。然皆无足为大得失也。惟“不顺乎亲”语未免大重;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岂但不信於友而已!“事亲勿悦”,但不为亲所喜悦耳,措语较有分寸。“诚”者,理也,德也,故云“思诚者”“诚之者”则以诚为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诚能动人,故由“获上”,“信友”,“悦亲”递近而归本於“诚身”,然後以至诚未有不动总结之,又以不诚之不动反结之,首尾呼应,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归本於诚身以开下文“不思不勉,择善固执”之意,意不在於动人,故删其後两句。然则是《中庸》袭《孟子》,非《孟子》袭《中庸》,明矣。至於虚字互异,本不足为轻重,然“获上”、“信友”、“悦亲”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诚身”则不可用“於”字,故变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获上”、“信友”、“悦亲”、“诚身”,皆已见於上文,故助语用“矣”字,“治民”,上文无之,用“也”字为得之。“不获於上”系转语,故用一“而”字;“反身”则不必多一“诸”字也。“是故”二字紧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当删去。细玩此章文义,《中庸》之不及《孟子》显然可见。若之何先儒犹以为孟子述《中庸》之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