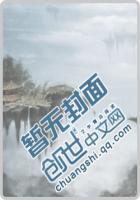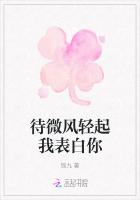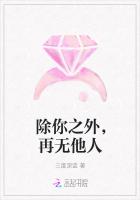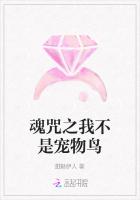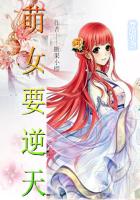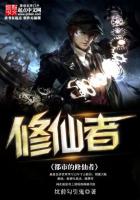第1节
发了三天避孕套,胡梦是和王志坚一人赚了三百五十元,本来是三百二的,工头看他们做得不错,又给加了三十块。王志坚拿到钱的第二天,就买了车票去青岛,他从同学那儿得到消息,薇薇今年有实习,不回家过年了,王志坚绝望了半个晚上,早晨一起来就直奔北京站。
宿舍里只剩下胡梦是一个人。他蜷在被窝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看着看着想起了苏帘儿,心想,怎么这么多天,她也没打一个电话来呢?难道回到家就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了?不对,不但没有苏帘儿的电话,好像这些天没有任何一个电话,他跳起来,到电话机那儿去看。老天,原来电话线不知是谁收拾东西的时候给弄坏了,就算是有电话也打不进来。胡梦是赶紧接上,又到楼下打了一下,通了。之后也无心看书,盯着电话,等着有人打过来,哪怕不是苏帘儿的也行,哪怕是小腊、蔡军都可以。原来屋子里住八个人,现在就他自己,不免显得空落落。更重要的是,胡梦是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到底是回家还是不回家?眼看已经腊月二十几了,就算要回家,也只能买到二十二、二十三的车票——还得运气好。如果不回家,自己真就一个人在学校过年吗?他计算了一下,认识的同学留在学校的男生竟然一个也没有,女生那儿,他曾见过黄淑英和李莉,其他的也没有了。
说起黄淑英,胡梦是感到好奇,他觉得黄淑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他看来,黄淑英都是被那个红衣女子——他指的是欧阳紫荆——给改变的。他自然早就听说过欧阳紫荆和何凤兮的事情,师生恋,即便不是严格的师生恋,也是标准的婚外恋,在中文系的老师里面并不少见。这些年,就他们所知道名字的,离婚后娶了学生或者没离婚就和学生搞在一起的也有三四个了。这算什么事情呢?才子总要爱佳人吗?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四五十岁的这一代学者,刚刚进入大学教书的时候社会上还讲究论资排辈,婚恋上也主要靠相亲结合,自由恋爱并不是那么广泛,而娶的那些人未必就是合意的。随着社会日渐开放,随着他们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更随着一拨拨的女学生更加实际,愿意靠嫁人这条捷径免去自己多年的奋斗之苦,他们面临的诱惑自然就更多了。中文系的教授们,谁不是或多或少有点儿多愁善感,有点儿小情趣,有点儿渴望红颜知己伴酒抒怀呢?更不消说自己的老婆在岁月和生活的摧残下已经人老珠黄,即便是肯下血本去保养自己,奈何一个贫下中农的底子,再怎么装大地主,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每日对着柴米油盐的糟糠之妻,很快也就有了蠢蠢欲动的心思,这时候恰好有青春年少抑或貌美抑或温柔的女学生来请教问题,一次抵制,两次拒绝,三次回避,四次五次六次之后呢?贼心既起,贼胆就会越来越大,贼出来,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就这样,不少中文系的老师落水了,落下去才发现,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水里的日子都是不好过的。何凤兮就是这么一例吧。
可话又说回来,倘若这些教授和他们的老婆之间真没有爱情了呢?孩子大了,父母没了,只剩下两个人整日面对面生活,一个锅里抡勺子,可就是说不上话,想不分也难。而从那些女学生那里,他们又确实找到了年轻时未曾体验过的爱情激情,就算年纪差距大了些,可四十多岁的成功男人,怎么看不都像树上熟透了摇摇欲坠的苹果?关键就看他们过不过得了自己这一关,过得了,一切事情做起来都觉得是理所当然;过不了,做什么都是贼,亏心。
胡梦是听说过何凤兮的事情,也知道他不敢得罪自己的老婆和岳父,没有他们,他在学术圈里不可能这么几年混到这个地位。他原来不过是个中学老师,考硕士上来,毕业就留校,现在马上要评教授,这条路不能说走得不顺,也不能说他不努力,但是没有他老婆和岳父,他一个硕士是进不了这所全国名牌大学的。他和欧阳紫荆搞在一起,学生之间说什么的都有。有意思的是,男同学大都觉得何凤兮理亏,不该搞婚外情,女同学却觉得他在追求自己的爱情,没什么不对的。她们大概都潜意识里把自己放在了欧阳紫荆的位置上,从而对何凤兮多了一分理解,很少有人想将来的某一天,自己扮演的可能是何凤兮老婆的角色。
让胡梦是他们不解的是,看欧阳紫荆,人长得漂亮,家境似乎也不错,好像没有理由要走这条路,不知道她动机何在,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上天注定。
任脑子信马由缰地胡跑了一气,胡梦是感到肚子饿,正要出去吃个蛋炒饭,电话响了,他赶紧去接。这回是苏帘儿。
“你们宿舍电话怎么回事?我打了一天了都在占线,”苏帘儿说,“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情。”
“电话线坏了,我一直没发现。我没事,你在家里好吗?”
“嗯,就是冷,家里阴天,没暖气,阴冷阴冷的,晚上睡觉很难受。”
“你买个热水袋,睡觉时装上热水,就暖和了。”
“有热水袋。你买票了吗?还回不回家?”
苏帘儿这么一问,胡梦是才想起自己还没决定回不回家,就说:“还没想好。”
“学校还有人吗?”
“没什么人了。”
“那你也回家吧,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年多孤单啊。我可不想大年三十的时候你哭哭啼啼地给我打电话,嘿。”
“怎么会呢!”
“你赶紧去买票,实在排不到,就找票贩子买。”
“好。”
“你要是……”
“什么?”
“你要是钱不够的话,我给你汇一些过去。”
“够的,我和王志坚去发了几天……传单,挣了点儿钱。”
“梦是,我……想你。”
“嗯。”
你想不想我?
“嗯。”
“你老嗯什么,你这人很没劲,我挂啦,我爸回来了。”
苏帘儿挂了电话,胡梦是还愣在那里。他其实很想苏帘儿,但不想表露出来,他怕一说出来自己会感伤,电话里卿卿我我,可放下电话就是自己一个人。但苏帘儿生气,也让他很不好受,他以前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在电话里讲话,和面对面完全不一样,你看不见对方的表情,猜不透她的真实意思。
第2节
既然这样,还是得买票回家。胡梦是先到学校附近的订票点去,远处一看,排队的人并不多,等排到了,一问才知道,人不多,是因为票卖完了。胡梦是决定第二天到北京西站去买票,凌晨就去。没决定回家的时候,不着急,一决定了反而觉得是非回去不可的。想着明天起早去买票,胡梦是也睡不踏实,就卧在床上看宿舍里那台14英寸的电视机,电视上到处都是大红大紫的新春广告。各类男女明星在上面搔首弄姿恭贺春节的到来。
晚上12点,胡梦是穿好衣服出门。冬日的夜晚没有风,但空气中都是冷,这种冷几秒钟就能穿透衣服和皮肤,直达骨髓,胡梦是的棉服已经穿了两年了,本来就不是什么好料子,现在越发不禁冻。但他现在没有钱再买一件好大衣,只能穿这个,为了暖和些,他小跑了起来,冰冷的空气被他大口大口地吸进肺里,竟然能尝到一股甜甜的味道。道路是安静的,连车也少见,只有昏黄的路灯十几米一个地站在那儿。大多数店铺也都关了门,最后一班公交早就发出了。
胡梦是终于等到一辆出租车,司机疲惫不堪。
到了西站,胡梦是本以为自己来得算早的了,可那儿已然是人山人海。急着回家过年的人们背着行李站在寒冷的冬夜里,排队,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地上铺着好多被子,被子里是睡梦中的一些孩子,他们的母亲不停地掖着被角,焦急地望向自己排队的丈夫。
胡梦是颓然地都想退回去了。但既然来了,总要排一排,比较了半天终于觉得其中一条要稍微短一些,排在了队尾。他的沮丧很快就有了缓解,因为随着天色见亮,后面的人越来越多,他在整个队伍中的位置似乎越来越靠前,看着后面的人,心里稍微平衡了。胡梦是早已经被冻透,还憋着一泡尿,可是他不能离队,一走掉便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又过了好一会儿,旁边的一个人突然问:“你是学生?”
胡梦是说是,嘴巴都有些结巴了。
“学生有学生窗口啊,干吗在这儿排着,那儿的人少。”那人说。
胡梦是大吃一惊,原来有学生窗口的,他赶紧打听了地方,磕磕绊绊地跑过去,是在车站的南边几个窗口,人果然要少些,但因为来得太晚了,也少不到哪儿去。但这儿的好处是,排队的人以学生为多,相对比较守秩序,不会像其他队伍那样挤来挤去,随便插队。
几个小时后,眼看广场上的大钟就要到8点了,人群开始蠢蠢欲动,睡觉的起来了,分散的聚拢了,互相开始商量着哪一趟车的什么座位,如果这趟买不到用什么替代,等等。胡梦是跺着早已麻木的双脚,希望即将随黎明一起到来,8点开始放票,尽管前面排着近百人,还是觉得希望离自己越来越近。
又过了一会儿,他再次看大钟,依然是8点差10分,又过了几分钟,他再看,还是7点50。这钟可能坏了,胡梦是想,突然人群开始鼓噪起来,并且伴随着越来越猛烈的拥挤,他不自觉地就向前涌去,如果不使出全身的力气,马上就会被挤出队伍。
放票啦,有人喊。
放票啦,更多人喊。
胡梦是再次看向大钟,他惊呆了,揉了揉眼睛,没错,指针清楚地指向8点15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仿佛时空穿梭一样,但他清楚,刚才过去的时间绝对没有25分钟。紧接着,排在最前面的人已经拿到了票,高声叫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亲友,欢天喜地如抢得黄金一般。很快,又有人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也有人骂骂咧咧:******,我排到前二十名,怎么都没票了呢?几分钟就卖完了?然后有人说,肯定是车站搞鬼。
这时,队伍外的一群人开始小声地挨个问:“要票吗?要票吗?”
“都有哪儿的?”
“哪儿的都有,你要哪儿的?”
“票贩子。”有人喊。
“******,肯定是铁路的人内部搞鬼。”另一个咒骂道。
但很快就有人跟着票贩子走了。
胡梦是绝望地感到,自己是不可能买到回家的车票了,他脑海里还想着大钟少去的25分钟。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时间为何平白无故地出现了空当,胡梦是已经被挤出了队伍。
胡梦是站在那儿,等票贩子上来搭讪,可半天也没人过来,他只好四处走,竟然还有几个人把他当成是票贩子。后来在进站口附近,终于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瘦瘦的小男孩过来,问:“大哥,找票?”
为了显得成熟一点,胡梦是点点头,没说话。
“跟我走。”男孩说。
胡梦是跟着他出了车站广场,绕进了附近的一个小胡同,心里有点儿打鼓,不会是抢劫的吧?但来到这儿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好在马上就到了一栋小楼,门口挂着大帆布帘。
“进来吧。”男孩说。
胡梦是跟着进去,楼道很黑,但能看清大体的模样,他们进了其中的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一个满脸褶子的中年人,桌上摆满了车票,大概有几百张的样子。
“到哪儿?”中年人问。
“到哪儿?”男孩重复中年人的话。
中年人突然站起来就给男孩一个嘴巴,吓了胡梦是一大跳:“瓜娃子,连到哪儿都没问清楚,就把人领来了?你找死啊,要是警察怎么办?”
“我到赤峰。”胡梦是赶紧答话。
“赤峰?一百五。”
“一百五?这么贵,原价才五十多。”
“爱要不要,有的是人买,大腊月的,谁不想回家过年呀。”
“能便宜点吗?”胡梦是晓得价钱谈不下来,但还是要挣扎一下。
“走人走人,别耽误我做生意。”那人挥手。
“那……给我拿一张腊月二十二的吧。”胡梦是挣扎不动了。
“钱。”
胡梦是递过钱去,车票比自己预想的贵很多,但也只能如此,越到这时候,想回去的愿望也就越强烈。
“你运气好,最后一张了。”中年人接过钱去说。
“这票……”胡梦是接过来,犹豫着问,“不会有问题吧?”
“问题?兄弟,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这儿多少年的买卖了,从我们手里,送走回家过年的人没有一千万,也有八百万了。没有我们,中国每年能运送好几亿人?这票刚从站里出来的,油墨还没干呢。”
胡梦是拿着票绕出来,心里还是不放心,就想找人对对票,但谁又放心把票给他呢?后来他想到一个主意,到出站口去捡废票,一项一项和自己的对照了,好像差不多。就在他要把票装起来的时候,一只手抓住了他,“跟我走。”那人说。走到一个角落,那人放开他,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没干什么。”胡梦是说。
“从地上捡票干什么?你的票呢?拿来我看看。”
胡梦是把票递过去,那人仔细看了看,还给他,说:“身份证。”
胡梦是又给他身份证。
“学生?”
“嗯。”
“学生证拿出来我看看。”
胡梦是赶紧掏出来,那人看了看,说:“都什么时候了,怎么才回家。”
“我找了个假期兼职,才做完。”胡梦是说。
“好了,你走吧。”那人理了一下头上的帽子。
胡梦是才敢走,心里突突直跳,敢情这个人是便衣,把胡梦是当捡票做假票的的票贩子了。幸好自己今天证件带的齐全,否则搞不好得进去带一半天了。
坐上公交车,身体里一直从里到外的冷,衣服裹得再紧也没用。
回到宿舍,赶紧喝了两大杯热水,但还是着凉了,不停地打喷嚏。
好在有票,胡梦是想,后天就回家过年,我要回家了,吃老妈包的饺子干的面条,把炉子烧的旺旺的,过年。
现在,苏帘儿在干吗呢?他又想,她会不会在想我呢?她有没有和她爸妈透露那么一点有关我的消息?她会见到很多高中同学吧,那里面,有没有暗恋她的人?或者就是她的前男友?帘儿啊帘儿,我在北京,你在南京,南辕北辙一样的遥远,守株待兔般的期望。
然后,他就睡着了……
第3节
在胡梦是想念苏帘儿的那一刻,苏帘儿没有在想他,而是窝在松软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一个戴眼镜的40岁左右的男人,正眉飞色舞地做讲座。苏帘儿很是吃惊,因为这个人是中文系的老师江谷城。在电视屏幕上看起来,江谷城有些不一样了,平时学校里的他,也是西装笔挺的,但总是很严肃,没现在这么活泼,甚至有点儿幽默。他正在讲中国古诗词,虽然他的专长不在这儿。苏帘儿本能地看了看电视台标,是一个地方电视台,不是出了于丹和易中天的中央10。
镜头偶尔会给到台下坐着的观众,组成还是很丰富的,但至少有一半看起来都是本科学生。苏帘儿开始喊她妈:“快来看,我们老师。”
她妈端着杯子过来,瞅了两眼,说:“这个人挺能说啊,眼睛都不看草稿。”
苏帘儿说:“他在学校可不是这样的,铁面判官,四大名捕之一,心胸狭窄,我们都恨死他了。”
她妈说:“你怎么这么说老师?老师管的严点,是为你们好。”
苏帘儿:“不是我说的,同学老师都这么说。”
她妈说:“去洗把脸去,早晨起来,连脸都不洗了,将来谁敢娶你。”
苏帘儿起身,抱着她妈:“总有人娶,嘿嘿,你放心,剩不下。”
她妈的身体被苏帘儿摇动了,手里的杯子摇晃着,她努力控制着不让水洒出来。
很快,四面八方的同学都看到了上电视的江谷城,包括中文系的讲师隋然。隋然是在电器城看到的,当时他正和老婆语如买液晶电视,他们才搬到新房子不久,家电还没配齐,因为付首付加装修,不但把两面老人啃个精光,自己更是除了生活费一点儿钱都没有了。还好年末隋然报了一万多块钱的课题费,而她老婆终于拿到了公司的年终奖,还了关系不牢靠的朋友一些钱,赶紧出来添置东西。挑了半天,不是嫌贵,就是觉得太小,两人为此意见始终难统一。
“隋然,这不是你领导吗?”从大中到了国美三层,老婆语如说。
隋然抬眼看去,有几台电视里都是江谷城的大背头,清晰得连眼角的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
“是江老师,他也去做讲座了,没听说呀。”
“你看看人家,也才四十岁吧,教授博导,中文系主任,现在又和媒体搞得这么好。你都三十二了,连副教授还没评上呢。”
“年代不同了。我们现在评个职称,你知道有多难?正经八百地发篇论文都不容易,现在核心期刊,全不看论文质量,要么看面子,要么看钱。”
“那你就让你导师给推荐一下,他那么大牌,杂志肯定卖他面子。”
“我想凭自己的实力发。”
“你有什么实力?一没名,二没钱,光会看书写字能顶什么用啊?”
“赶紧挑电视吧,懒得和你说。”
最后,电视也没有买成,两人还闹得很不愉快。
晚上隋然洗完澡,难得地在电脑上下载了一个电影看,语如拿个优盘过来,说:“把你没发表的、比较好的论文拷给我。”
“你干吗?”隋然问。
“我有个同事的老公,听说是在《文学评论》当编辑的,让他给看看,说不定能发表。”
“我不想欠人家人情。”
你就拷给我吧,要欠人情也是我欠。
隋然拗不过她,只能考了三篇文章给语如,说:“随便给人家看看就得了,别说得低声下气,毁了我的名声。”
隋然很快忘了这事,然后春节近了,到处提前拜年、聚会,一通忙乱,和往年基本一样。最大的不同就是,江谷城真的成了名人。本来好多人都以为,在一个地方电视台搞电视讲座,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但江谷城口才好,出语很麻辣,虽然专业不是做古典文学的,却对当下的古典文学热意见颇多,讲着讲着就拎出一个某某来消遣批评一番。如此一来,想不热闹都难。更何况现在的媒体嗅觉都是超前灵敏,很快就闻到了这里面的新闻腥味,一哄而上,各自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点热炒一番。什么“教授讲座痛批古典文学研究界”,什么“古典文学被江谷城判死刑”之类的标题都出来了。更何况,江谷城一直等着这样的机会,频频接受各种媒体采访,趁热打铁,一夜之间俨然成了文化名人。媒体宣传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炒越热,越热越炒,江谷城已经热到要煳了。
第4节
黄淑英从亮马桥的昆仑饭店走出来,直接打车到西单。她前两天看中一件毛衣,可惜号都不合适,店主说今天到货,她要第一时间赶过去。临近春节,到处都在打折促销,其实就是把价格暗中提高,再以打折的名义降下来。黄淑英看中的那件橘黄色毛衣,原价两千,满一千减四百,她只需一千二就能买下来,是牌子。前一段,李莉也带她去过秀水街,一大街的假名牌,以假乱真,但挑来挑去,黄淑英一件都没买。
“要买就买真的,哪怕是打折的,买水货多掉价。”
果然,此后她认准的牌子都只去专卖店,一个挎包七八百,一双鞋子一千多,她自己的钱都花在这个上面了。后来连李莉也觉得可怕,劝她说辛苦赚来的钱,别大手大脚花完了,存下一些吧。却遭到黄淑英一顿抢白:“虽说你把我领进门的,现在你可落伍了,你不知道那些老外,瞧不起我们,要是再不穿得时髦点儿,就更不好做了,花大钱,是为了赚更大的钱。”
我的意思是你得低调点儿,马上要开学了,你这么张扬,搞不好要出事情的,让学校知道了,咱们都得倒霉。李莉说。
黄淑英将一件文胸扔到垃圾桶:“怕什么,难道看不得别人穿得好点儿吗?燕子她们还不是每天花枝招展的,难道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就不行,天生我们就只能穿金五星的批发货、擦大宝美容霜?我偏偏不信,现在我能穿什么,能用什么,就都要用到。我前十八九年都白活了。”
“淑英,这种事情,只能偶尔为之,难道你真以为那些老外会娶你?他们不过是说着玩的,我认识那么多人了,没有一个嫁得成的。再说,过些年,老了,不好看了,你靠什么生活?”
“哈,今朝有酒今朝醉。”黄淑英喊了一句。
其实,黄淑英的矛盾和挣扎,比李莉所看到的还要激烈得多,但她一方面不想表现在她面前,另一方面又因为潜在的危机感而想用物质麻醉自己。内心深处,她有着一种深刻的负罪感,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世俗所不容的,更是父母和亲戚朋友所接受不了的呢?但同时她又无力拒绝那些漂亮的衣服、可口的食物,尤其是那些男人半真半假的赞美和女人嫉妒的诱惑,只有在那种时候,她才感到自己是实在的,是这个庞大城市的主人。
她偶尔也会想起自己刚上大学时所发下的宏愿,要读硕士读博士,要做研究搞学问,要写出伟大的著作来,念及这些,总有恍若隔世之感。
“如果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多漂亮衣服,好玩的东西,”她想,“我或许就能向着自己的理想去努力了,可是这扇门一向我打开,就再也不想关上它,花花世界谁不爱呢?”
她意识中最需要回避的,是那个乡下的家和家里的人,她甚至不忍心想起三间土坯房,被炊烟熏黑的门窗,裂开缝的玻璃,低矮的土墙——就是这些土墙,在童年时看起来无比的高大,觉得自己永远也翻不过去的样子,可现在,一迈腿就能跨过——满地的鸡粪、仓房里的米口袋、地窖里的土豆,自然还有屋子里又黑又瘦的父亲和头发花白的母亲。她现在最可欣慰的,是能够每个月给家里和弟弟妹妹邮去一些钱,让他们吃饱穿暖。虽然她收入很多,但不敢往家里汇太多,怕他们怀疑。而这样赚来的钱她又不愿意存起来,看着它们,她会感到痛苦,只有把它们花了,才会舒服。她辛苦去赚这些钱,然后像报复这种“辛苦”似的把它们挥霍掉。
让李莉一闹,黄淑英的情绪低落极了,她去楼下打了个电话,告诉今晚约的人,她身体不舒服,去不了了。对方不依不饶,问:“黄小姐,是哪里不舒服?你怎么能失约呢?”
黄淑英听着他生硬的汉语就感到别扭,喊了一嗓子:“我大姨妈来了,行了吧?”
“哦,原来是你的亲人来了。”对方表示了恍然大悟的理解。
黄淑英不禁失笑,老外听不懂大姨妈什么意思:“是,我们家亲戚,每个月都来。”
黄淑英早买了手机,但她从不用自己的手机给这些人打电话,她区隔的很清楚,走出酒吧和酒店,她仍是原来的黄淑英。对她来说,那个流连于夜生活和不同男人之间的人,只是她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她小心翼翼地,用尽各种办法,不让这两种角色混淆。在很大程度上,她做到了。
天空阴沉,但气温并不太低,她裹着毛衫也没觉得冷,默然了几秒,又拨通了欧阳紫荆的号。她早已经到家,但两人一直没联系。欧阳紫荆走之前那几天,两人似乎没什么话可说,仿佛心里各藏着一个秘密,不敢让对方知道一样。
电话通了,传过来欧阳紫荆清脆的声音:“是谁?”
“我,”黄淑英说,“在家怎么样?”
“淑英,我挺好的,放松身心,你呢?你真不回家过年了?”
“不回了。”
两人沉默了一下,黄淑英接着说:“我前天看见何凤兮老师了。”
又是沉默,然后欧阳紫荆说:“他,怎么样?你在哪儿看见的?”
“我去系里交寒假留校学生统计表,在楼道里碰见他,挺颓废的,看起来。”
“哦,他就那样。”
“我和他聊了几句,他好像在忙课题的事情,家里就一个人。”
“哦。”
“你回去后没和何老师联系过?”
“没有,事挺多的。”
“据说成绩3月份出来。”
“我知道,我……进入复试了。”
“祝贺你,是何老师告诉你的吧?”
“是。”
“你打算怎么办?听说他老婆过完年就回来。”
“好合好散呗。”
“就这么容易?”
“还能怎么样?我又不想嫁给他,他也不能娶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也好。对了,我前几天买了一个进口的皮包,很好看。”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教汉语啊,我不是说过吗?”
“别骗我了,教汉语一个月才赚多少钱,还不及你花的零头。”
“反正不是偷的抢的。”
“淑英,你可不能学坏,你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朋友。”
“好了,天有点儿冷,我得回去了。”
“有钱别乱花,还不如存起来。”那个最初把她领进门的人,告诉她不要乱花钱。
“嗯,拜拜。”
“拜拜。”
黄淑英回去,趴在被窝里呜呜哭了一会儿,她没想到自己还是这么在乎欧阳紫荆的话。
“你可不能学坏。”她说。
她不让我学坏,她说我是她在北京唯一的朋友,黄淑英想,可我已经下水了,无论怎么上来,鞋都是湿的。心烦躁,就去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看,是莫泊桑的小说集,一翻就翻到《羊脂球》。我还不如生在战争年代呢,她又想。看了一会儿,读到羊脂球要被人侮辱的时候,黄淑英觉得胸闷气短。或许,爱情,是能够拯救我的吧?我需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我要找一个只在乎我的人,就好了吧。可是,还得读书,期末的考试还有两科成绩没出来,也不知道都过了没有。不管怎么样,也得把大学念完。
第5节
两天后,黄淑英偶然从一个老师那里听到,她的外国文学史,得了全年级的最高分,但小腊不及格,她还记得那次课堂上的事情。这让黄淑英很高兴,她就是想考个好成绩,只有这样,别人才不会过多关注自己穿了什么样的衣服鞋子。
这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黄淑英他弟从镇上打过电话来,说她邮的钱和东西都收到了,说过年的东西也准备得差不多了,说爸妈我们都很想姐姐,说让她找个地方好好吃个年夜饭,说家里一切都好她不用惦记,说多休息休息别太累着……两人聊了十多分钟,弟弟几次示意姐姐电话费很贵他要挂了,黄淑英都不舍,她其实是想家的。
但电话终于还是挂掉了。临结束,弟弟说漏了嘴,说父亲腿摔坏了,一直躺着呢,至少得正月才能下地。这回黄淑英挂断了电话,她听不下去,怕自己对着弟弟哭出来。她以为,自己寄些钱回去,他们就能过一个好年,哪想到爸爸又摔了腿,而这时,她本应该回家帮母亲的,可她没有。
打开电视,新闻上正播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暴雪,大风降温。她突然想到弟弟从镇上回家的一路:一个小人,穿着棉衣,带着皮帽子,顶风冒雪往回走……想着想着,眼泪又不知不觉流出来。
“我以为一切都变好了,可好像什么都没变。”
黄淑英有点绝望地感到,她让家里过一个和美的新年,并没有让她感到真的快乐。她一次又一次地设想过,父母和弟弟如果知道这钱的来路,他们会愤怒、痛苦、咒骂、争吵、哭泣,怎么都有可能,就是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理解。这是她心里的一块石头,并不真的存在,可是它的重量,却时时刻刻压得她呼吸困难。
可是……她转而又想到,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了,我无法过从前的日子了。这就像一个饿极了的人,有机会吃到美味佳肴,你让他再去吃糠咽菜,他做不到了。
黄淑英在学校过了年,吃到了饺子,也看够了烟花。
年三十那天晚上,欧阳紫荆和她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她说她在家里,竟然想念北京,想黄淑英,也想何凤兮。黄淑英说,那你赶快回来吧。欧阳紫荆却说不要,她家里不会同意的。她从电话里听到了南京的烟花爆炸的声响,她也从电话里听到了北京烟花爆炸的声响,一条不知道有多长的电话线,把两个身处异地的孤独的人,紧紧地联系起来。这不是一种互相取暖,反倒是让彼此更冷,冷到彻骨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
有一些话,她们一直欲言又止,但又一个字都没说出来。不说出来好,它们会在心里烂掉,化成滋养强大小宇宙的肥料。
挂了电话,黄淑英痛哭一场。不是哭孤身一人守夜,也不是哭那难以拒绝的堕落,甚至,都不是哭她对欧阳紫荆那奇异的爱恋,她之所以哭,是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灵魂里的空。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填不满的,空得心慌意乱。黄淑英一夜未睡,盯着电视机但什么也没看进去,知道新一年的太阳升起来。
看着那惨白的新一年的朝阳,她想,你每天都会升起,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