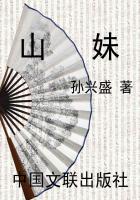屁蛋儿开导夏侯特:“你想要开诊断书,可你没有病啊。--没病就得造假。
“在医院里造假,可不容易了。就算你认识大夫,可还得找不少人,--因为大夫开诊断得有凭据。开内科的诊断,得有化验单、心电图纸。开外科的诊断,得有X光片子。开张诊断书,得一个科、一个科的拜。少拜一个科,你就过不了关。
“可是要找把爷,就不用费这么多的事了。人家一条线的人都连着呢。这叫作‘流水线作业’。你懂不懂?”
屁蛋儿向周围扫了一眼后,压低了声音:“再说,‘吃饭防噎,走路防跌’。万一这诊断书让人家看出来毛病,就得复查。查漏了馅,那可就砸锅了!开诊断容易,对付复查的难。谁能知道人家什么时侯、在那家医院复查你的病?
“人家把爷的耳朵灵,眼界宽。但凡要有个丁点风吹草动,人家老把爷先知道。老把爷吃这碗饭都多少年了,从来没有翻过船。--把握!”
“行,行!”夏侯特连连点头同意,问:“请你们这位把爷帮忙,得花多少钱?”
屁蛋儿听后笑着摇摇头说:“留着你的钱吧,人家把爷不能要你的钱。--你是外人,人家老把爷从来不吃外食儿。”
“嗯?”夏侯特看了屁蛋儿一眼,说:“这我就不明白啦。他不要钱,--难道说,你们这位把爷能发善心,白帮着忙活?”
屁蛋儿的眼睛盯着夏侯特的瞳孔,用低低的声音说:“把爷不要你的钱。他要你的血”。
“啊?什么?”夏侯特瞪着屁蛋儿,惊问:“你把话说明白?难道说,你们这个把爷是个青面獠牙、吃人肉、喝人血的妖魔鬼怪?
“你是不是发高烧烧糊涂了?怎么晴天白日的说梦话呢?”
屁蛋儿解释说:“外人的事,把爷不能管。要想请他帮这个忙,你就得‘见血’,--入挑线的这个门。拜了门子后,你就是自己人了。把爷为你办事才能放心。”
“见血?”夏侯特问:“见血是什么意思?怎么听着这么吓人呢?难道说,还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屁蛋儿说:“见血,就是你得抽出几管子血来卖。”
夏侯特说:“你都把我给说糊涂了。--你们这个把爷挺怪呀!给他钱,他不要。却偏偏的要我的卖血钱。这真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怪人、怪事都有’”。
屁蛋说:“不,你误解了。
“老把爷这个人的为人,我知道--仗义!你的卖血钱,他肯定不能要。他会把这笔钱用来请病院的人,帮你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的。”
“行。”夏侯特点头,“为了返城,我豁出来了。出回血,值!
“权且当交社会大学的学费了。--高尔基的《大学》,这回我算是毕业了。”夏侯特怅然、无奈的嘘了口长气,百感交集了。
夏侯特想了想,不放心,又问:“往后,你们这个把爷能不能用输血、卖血这件事情,抓我的把柄、辖持我?逼我干坏事!”
屁蛋儿说:“这你不用担心。卖血换诊断书的事,是件两相情愿的事情。往后咱们谁都不愿意露它。既然你不放心,我就先小人、后君子,和你把话说明白-- “输血后,你不吃挑线这碗饭,把爷不能找你。--因为你不是挑线这门子的人。你不向外宣扬这件事,把爷也不会找你。--因为你没有向外摊挑线这件事情,把爷和你井水不犯河水。
“什么时侯你把挑线这件事情摊了,把爷就该找你了。既使老把爷死后,只要你露了这件事情,下个辈份的人也饶不了你。这叫作规距,明白吗?不能坏了规距!”说明白后,屁蛋儿打保票:
“至于别的,你多虑了。把爷的人手多的是,不缺你,信不着你!”
夏侯特说:“行,咱们都守口如瓶,谁都甭坏了规距。”
夏侯特把自己的茶杯拿起与屁蛋儿的茶杯碰了一下,说:“狄哥,咱俩今天就算是说定了,按着你谋划的办。你估摸着,把爷能帮这个忙吗?”
屁蛋儿拍着胸脯打保票:“这你放心。就凭我,头一回求把爷,他还不至于驳我的面子。”
夏侯特伸手喊:“结账!”
屁蛋儿见了,亮了句场面上的话:“夏侯儿,你今天的这桌酒是为了你自己的事,我就不跟你假客气了。
“--往后咱俩再见面,会的时侯我请。”
第二天夏侯特与屁蛋儿来到医院的时侯,是下午的患者诊病高潮之后。化验室外的长椅上,已没有等候化验的患者了。只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还有一个孤零零的人守候在阴影中。屁蛋儿的下颏朝其人的方向抬了抬,向夏侯特递了个眼色。夏侯特明白:此君便是把爷。
屁蛋儿快走了几步到长椅前,向长椅上坐着的人介绍夏侯特:“把爷,我早上跟您老说的人,领来了。--就是他。”
夏侯特走到近前,向把爷打量了一眼。见把爷低垂着头,穿着一套说黑不黑、说灰不灰的衣服,将自己的身体与墙暗角中的阴影几乎融为一体。把爷抬起头来看夏侯特的时侯,他那张戏台上曹操一样白白的脸,给夏侯特留下了夜空中惨月般的阴冷印象。
把爷听了屁蛋儿的介绍,抬头将似同瞌睡的眼睛睁开,向夏侯特迅速的扫了一瞥。夏侯特觉得把爷的眼睛如吐信的毒蛇,突然向他射来道摄人魂魄、闪电般的寒光。--心,因惊恐而抖了抖。然后,把爷伸手与夏后特握了一下手。夏侯特觉得从把爷鹰隼利爪般的瘦骨楞楞的手中猛然传来股力量,如铁钳要捏碎他的掌骨一般。--心,因疼痛而抽搐了一下。这股劲力,如急驶火车带来的疾风,来的突然,去的也快,--拂了一下夏侯特的身体即逝,马上便消失得丝毫力度皆无。随之,把爷与夏侯特相握的手,变得柔若无骨、妇人般的绵软。
握手后,把爷的脸上显出一副慈眉善目的和气相。他眼睛看着地面,病人低吟般的轻轻说了声:“行。”
说完,把爷开始高声咳嗽。咳声中,走廊一侧的女便所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个黑衣美妇人。她经过夏侯特身边的时侯,用心的盯了他一眼。然后,黑衣妇人向远处的内科门诊室走去。
去了片刻后,黑衣妇人拿回来张纸单子。她将手中的纸单向上扬举了一下,对屁蛋儿说:“走吧。”屁蛋儿应声向夏侯特努嘴示意了一下,夏侯特随着从长椅上站起来,跟在婀娜碎步的黑衣妇人后面走向化验室。
临行前,夏侯特留意了把爷一眼。只见老把爷双目微合、全神入定、悄无声息,如参禅礼佛一般。仿佛他老人家与这些世上的红尘俗事没有半点的因缘。
夏侯特俩人随着黑衣妇人来到了化验室。交了单子后,穿白大褂的人为夏侯特验了血型、作了血常规。
出化验室后,夏侯特再次向走廊尽头的暗角阴影处望去:早已人去影空,哪还有把爷他老人家的影子?只有墙角暗处的那团阴影,令夏侯特想起把爷与之近似的衣服颜色。
他们在化验室外的长椅上等了一会儿后,听到化验室里面的人大声说:“结果出来了。化验的,取化验结果!”黑衣妇人听后,起身疾步走向化验室。她出化验室后,对屁蛋儿、夏侯特高声说:“没事儿,走吧。”
黑衣妇人领着他们来到血库的採血室。接单子后,女白大褂看了眼夏侯特的胳膊。问:“没有针眼,是头回给血么?”夏侯特点了点头。
女白大褂转头问黑衣妇人:“头回抽,这量是不是有点太大啦?”黑衣妇人说:“身体好,行!”说着,她将双眼微合眯缝了一下,暗示採血室的女白大褂:“没事儿!”
採血室的女白大褂接受了黑衣妇人带来的把爷担保的“保险”后,不再说别的话,将带有橡胶管的针头扎进了夏侯特的血管中。
夏侯特亲眼看着殷红的鲜血从自己的血管中汩汩流出,不知道是心理因素使然,还是生理的因素所致,开始心跳加速,额头上沁出了细小的汗珠。他感到自己身体内储存的力量被外吸,身体逐渐被抽得虚空;仿佛体内的支持体在崩溃,身体在渐渐的向下瘫萎。随着体内的血液输出量的逐渐增多,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夏侯特知道:自己的肉体、精神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确实要挺不住了!--心被提到了嗓子眼中。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女採血人员将带橡胶管的大号针头从夏侯特的血管中拔出。夏侯特总算松了一口气,将悬着的这颗心放了下去。
屁蛋儿搀着夏侯特离开採血室时,听到后面黑衣妇人在向採血的女白大褂炫耀:“绝对纯!--连水都没喝”。夏侯特虽然没有听懂她话中的含义,但明白是因为自己不懂行而吃了亏,被人家捡便宜卖乖了。心不觉颤栗了一下,想:“狗咬病鸭子啊!”
夏侯特被屁蛋儿搀扶到了走廊中的长椅上,就势躺了下去。他觉得身体软软的,一点力气也没有,甚至连呼吸都感觉吃力了。屁蛋儿从衣服兜里面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几块水果糖。屁蛋儿将水果糖放到夏侯特的嘴中,说:“你在这躺着别动,慢慢含着糖块儿,过一会儿就好了。--没事儿。”
夏侯特正躺着,看见黑衣妇人从採血室走了出来。她将一张纸递与屁蛋儿,说:“给你办妥当了,你们自己拿到医务科盖戳去吧。”
屁蛋儿接过那张纸来看了一眼,对黑衣妇人道了声:“谢谢了!”
黑衣妇人听到感谢后“嘿嘿”低声笑了。她看了眼瘫软在走廊长椅上的夏侯特,扔下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谢我?呵!”留下了令人着迷、疑或的笑声后,她迈着婀娜多姿的小碎步,笑着走了。
屁蛋儿将这张纸送到夏侯特的面前,说:“拿来了,你自己看看吧”。夏侯特伸手接过这纸来只看了一眼,便擦了把泪、将嘴角咧开了,露出了一个带着泪的笑脸。这张纸,正是夏侯特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诊断书!
这张笑脸,虽然是由眼泪陪伴着的。这张笑脸,虽然脱胎于痛苦。但这张带泪的笑脸,此时出现在瘫软于长椅的夏侯特脸上,竟然显得那么灿烂!竟然是那么无法比拟的珍贵!
屁蛋儿看着自己的成绩,--诊断书带来的夏侯特伴着泪滴的笑脸。虽然看它时,因命运带给他们这一代的无奈而心里很苦涩。但他还是认为:自己创造的这张带泪的笑脸很美!美到无法形容、无法逾越的程度。--幸福脱胎于痛苦,美丽缘于丑陋的陪衬。
夏侯特看到诊断书后,不知道是诊断书带来的喜悦将精神化为了物质力量,还是水果糖补充了体能。他觉得体内又有青春的血液在涌动,又有无数的力量在积聚。夏侯特手扶屁蛋儿,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长椅上慢慢的坐了起来。
夜里,夏侯特作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血管里的血不停的向外涌泻,流得到处都是红色,成为了血的红色海洋。红色血液喷溅到医院的白色墙面上,凝固了,变黑了,形成为一个个斗大的字。
这些字,就是诊断书的内容。
夏侯特正在阅读诊断书的内容,诊断书突然从墙面上落了下来。恰巧,刮来阵狂风,将诊断书抛掷到了空中。诊断书向高处、远处飘去。
诊断书在天上飘啊、飘啊。夏侯特在下面追呀、跑啊。他伸手、跳脚、蹿高,却怎么也够不着诊断书。有几次,蹦起来的他,眼看伸手就要摸到诊断书的边缘了,诊断书却开玩笑般的又从他的手边飞走了。
夏侯特在下边追呀、追呀。跑着、跑着,他突然摔了一跤。这一跤,将夏侯特摔醒了。他感到头部好象在往外冒凉风,用手摸了把额头,满头的冷汗。夏侯特急忙找诊断书,诊断书还在。他放心了,笑了。夏侯特翻了个身后,又睡了。这回,他睡安稳了。
伴着病返诊断书的夏侯特睡觉时,脸上带着微笑,--掺着哭相的笑;眼角挂着泪水,--喜悦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