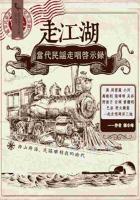老独的老屋很清静了,老独独自弹琴,琴音在老屋里缭绕,清朗而干净。这是老独听着的琴音,外人听到的琴音是凉滋滋的,自老独在老建灵前弹了扬琴后,他的琴音就带了一层避也避不开的凉意。有人说是灰色的,像缺了日头的天,有人说是白色的,像祠堂里为灵魂挂起的白帐布。
没人来听老独弹琴了,愈是老辈愈不想来,琴音一起,他们就感觉白帐布在眼前晃,晃得人发昏。老独的琴曲是弹给老建听的,老建在坟里远远用二胡和着。
就是不听琴,在路上见了老独,他们老迈的步子也变得急切,朝老独意思性地点点头,匆匆而过。
老独进了老屋就关门,关窗,然后弹琴。有时,整半天的时间,屋里的琴音一直没断,偶尔稍歇一会,琴音再次响起。有些是当年潮剧唱段的配曲,更多的是外人没听过的曲子。潮剧唱段的曲子还好些,老独一弹那些无人听过的曲子,听到的人便说,这是什么东西,掏心掏肺,要把日子挖光了一样。他们听不下去。
那天早上,老独进了老屋后,琴声一直响到人家午饭后。曲子往下落,缓到让人误认为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又往上爬,愈来愈用心,愈来愈有力。
啪啦一声,老独背对着的后窗碎了,一颗拳头大的石头穿破玻璃撞进来。屋里砰的一声巨响,是什么摔在地上的声音。然后是纹丝不动的静,屋外和屋内同样无声无息。
接下去的半天就一直静下去。
那天,老独是黄昏时开的门,门外没人。老独知道,自己身上沾满成团的目光,都在暗处。老独一步一步走回“下三虎”,他的步子有点歪斜,走的时候,肩背有些往前缩,下巴往下垂,像脖子上挂着重物。
老独还是天天去老屋,还是关门,关窗——包括失去玻璃的后窗。没有琴音了,老屋整天静着。老独一家搬走这些年,老屋一直静着,没人觉着静。可都觉得这两天静得有些怪异。老独倒还是出门的,三餐时间一到,屋门就打开,老独走出来,表情淡然,目光淡然。有时卷着纸烟,有时掏着烟丝。
孩子们的好奇被静撩拨得厉害。那天,他们用肩膀把伙伴托高,去扒老屋的后窗。第一个上去的孩子往窗里看了一眼,身子猛地一木,然后摔下来。他们被自己的惊叫声吓住了,哗啦啦四下散开。扒窗看见屋里的孩子双腿有片刻是僵硬的,他扶着墙,张着嘴嚷不出声。最后才跌跌撞撞朝伙伴们扑去。
“他在做什么?”孩子们围拢过去。
“在弹琴,那个老独在弹琴。”
“骗人,一点琴声都没有。”
“不信,你们自己看。”
“等等,我们刚刚弄出声音,他听到了,可能会不弹了。一会再看。”
半晌后,孩子们慢慢围过去。另一个孩子站在伙伴肩上,慢慢往上提身子。扒到窗口那一瞬,他的身子也猛地一木,但他双手抓紧了窗沿,腿脚晃了晃,没有摔下来。他看了好一会,慢慢往下滑,也张大了嘴巴,看住伙伴,脸上纷飞着不可思议的表情。
一个过路的大人揪住要往上爬的另一个孩子。孩子指指窗口:“看里面。”
扒过窗口的孩子低声说:“在弹琴。”一双手胡乱挥舞。
大人搬来两块土砖,站上去,往窗口望。看到里面的那瞬,他就一动不动了,像条藤一样半吊在墙上。
老独在弹琴,侧对窗口坐着,手掂琴竹。没看到扬琴,老独手里的琴竹就那样敲打着空气,眼皮眯着,胳膊带着琴竹或急或缓,或起或落,胳膊带着头脸,或点或摇。大人闪开头,日光从窗口进去,落了老独满身,他掂了琴竹起落的手和摇点的头落在地上的影子夸张地变形着。
大人把脸扒在窗沿上,地上的影子遮去了一半,老独身上也暗了一半,但老独没察觉,寂静的琴音在他周身缭绕,化成烟雾一样的东西,他整个人变得模糊不清。
大人默默下来。
一个孩子抬起脸,满眼恐慌:“老独疯了。”
“耍去,都去耍。”大人说,默默走开。
都默默的,但窗口后的秘密都知道了。秋红又去小卖店挂了一次电话。
大乌伯和老四叔去敲过老屋的门,敲了好半天,老独才开门,脸上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表情遗失在某个地方了。他看着大乌伯和老四叔,目光没在他们身上。
大乌伯说:“来喝茶。”
老四叔去推开了一半的门。
老独啊了一声,说:“喝茶,进来。”
大乌伯和老四叔进了门就四处看,在屋里四处走,看不到老独的扬琴。两只琴竹放在椅子上,静静躺在窗边的日光里。
老四叔想了想,问:“老独,扬琴哪?”
“坏了。”老独说。
再说,老独就不开口了,只是沏茶,只是卷烟。
阿锐回来了,回来就去敲老屋的门。
老独说:“工程结束了?不是说这次是大工程?”
“工程做着,还得两个月。”阿锐盯住老独看,眼神过分的专注。
老独说:“那你回来做什么?不好好管紧工程。”
“阿爸,你和我出去走走吧,一辈子没出门走过。”阿锐说。
“我出去做什么。”老独缩了缩身子,“我在家里好好的。”
阿锐笑了:“不用做什么,就看看外头的世界,包管看得你眼花。反而闲着也是闲着。”
老独有些生气了:“阿锐,你扔了工程回来,这是做什么?”
“工程上了轨道,走开几天没事的。我带你出去,有时间陪你四处走走,大半辈子了。我让阿妈也去。”
老独低头卷烟。
“阿爸,我现在做活的城市是旅游城市,景色比电视上还好看。就是我包下的工程,也是一个园林的一部分,工地都有花花草草的。”
老独说:“我好好的,你做什么。”
阿锐低下头。
老独想叹气,终把那声叹含在喉头,只喃喃说:“你们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