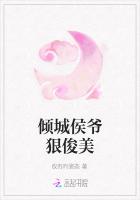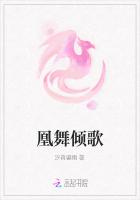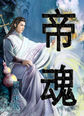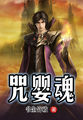当2002年陈露在《超级访问》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淡然。“1997年的花样锦标赛,也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可能在你生命中也是记忆比较深的一次,你得了25名。”
李静见机将话锋一转。“那是最让我伤心的时候了。”
陈露说。1997年,陈露遇到了低谷。伤痛的困扰加上与教练的矛盾,让本就繁重的训练变得异常艰辛。大年三十的晚上,她站在漫天的大雪中,期望能有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把她拉到机场,让她回家。可两个小时过去了,始终没有一辆车能为她停下来。她终于哭了,很彻底地把眼泪流了出来,直到一辆出租车停在她的身边,司机看着泪眼婆娑的她说,我送你,我送你!只是彼时陈露的眼泪已经关不住了,她就这么哭了一路,直到登上飞机,眼泪也还是不停地流。然而在飞机快降落的一瞬间,她立刻不哭了。她说,“我要以一个笑脸迎接家人。”
李静很能理解这个女人。女人与眼泪的关系很密切,但并非天生的朋友。资金欠缺,艰难运营,团队建设,节目改版,种种难题,常常会像沉重的巨石压于心头,无以疏解的时候,李静常常在车中播放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往前一步是人生,退后一步是黄昏,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歌声中,眼泪簌簌往下掉。她索性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放声大哭起来,一直哭到家门口,抹干眼泪,没事儿人一样地进了家门。或许对于她们,陈露或李静,唯有夜晚,密闭的车厢,以及身后一片绚烂的城市,才足以令自己流泪。而唯有学会克制泪水,才足以展现那份孤注一掷的美丽吧。所以,当1998年陈露再一次站在冬奥会的舞台上,并以一段《梁祝》获得铜牌时,她已经向世人做出了最好的说明:冠军可以是不同的人,但冰上蝴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你是一个英雄。”
李静很少在节目中如此评价一位嘉宾。“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喜欢,你决心要去做,你就坚持到底,对你的人生充满希望,你会成功。”
这是陈露在那一期“超访”结尾处说的话。成功了吗?2001年,“超访”被安排在北京台每周六的下午播出,只有30分钟。到了2002年,台里主动把节目时长放到了50分钟,并且挪到了周末晚间的黄金时间播出。这算不算是一种成功呢?“算的吧。”
李静和戴军非常明白彼此心中在想些什么。节目的影响力在扩大,运营却一直没有走出亏损。“成功”果然是一个很狡猾的东西,当失望越陷越深时,希望却又在渐渐逼近,于是在半明半暗间自我不断被催促着:“想要被认可”,想要破壳而出,就要顶破那层最厚最大的壳。李静顶破第一层壳花了1年的时间。她说,那一年她很羡慕戴军。因为戴军敢在节目中讲笑话。可她不行,她怕嘉宾不笑。7年国家电视台的主持经历让她无法找到一种属于《超级访问》的语感。对于每个人而言,改变并不容易。你一直想要跳脱出的那种人生情境,也正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你所适应,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7天足够养成一个习惯了,何况7年。所以,每当李静将一大堆华丽的台词念完后,她总是第一个陷入困扰。台本上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环节,她都好好地完成了,却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在与嘉宾对话,只是问答。而彼时的戴军却全然是另一种状态,放肆调侃,插科打诨,两个字,就是松弛。戴军将这种“松弛”解释为“异于常人的经历,练就异于常人的能力”。从漂泊深圳的打工者,到看尽三教九流的夜场歌手,再到一夜成名的流行歌星,戴军的生活阅历丰富至近乎驳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拥有了最“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如果说1993年以前的戴军还是沉默的,那1993年在全国夜场“走穴”的经历就是他语言活化的开端。当时作为“表演嘉宾”,他不仅需要唱歌,还要与台下的观众热切互动,只有如此才能镇得住场子,拢得住人气。站在台上的40分钟,他最多唱四五首歌,其余的时间缝隙都要用即兴的聊天与讲笑话来填满。这样的舞台也让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在灯影明晦间捕捉台下人的真实需求。最终,当阅历变为才华,戴军的语态也得以形成。李静和戴军的语境,一个源于多年供事国家媒体的习惯,一个来自长期混迹娱乐江湖的洗染,不同的过往导致了不同的出场。于是在《超级访问》的文本中,他们一个端着一个散着,一个抿嘴一个坏笑,各说各话,各表各意,依旧是两个语境。这着实让编导和后期剪辑很为难,为难到他们不得不把李静、戴军找到机房,义正词严地说:“静姐,戴军哥,你们看看被剪掉的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