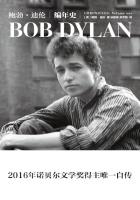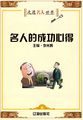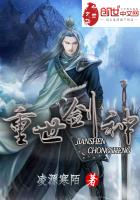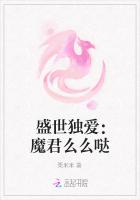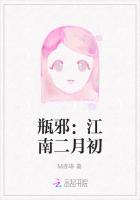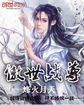祭奠之后,按预先密订的计划,两宫太后迫不及待地宣布召见恭亲王奕。关于此次召见,有三种不同的记载。
第一是《热河密札》的记载。其第七札记道:“祭后,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约一时许方出。” 这是署名“樵客”的某军机章京自热河发往北京的某军机章京“黄螺主人”的密札。因是当时当地人所记,应是可信的。“内廷”是指允许在内廷行走的御前大臣和军机大臣,这里指顾命八大臣。两宫太后召见他,他请求太后允许他同顾命八大臣一同进见。这显然是作个姿态。示意八大臣他的被召见是光明正大的,别无他意。但是,还没等八大臣表态,两宫太后却行使否决权,不准八大臣一同进见,只单独召见奕。没有办法,奕只得“独对”了。
第二是《庸庵笔记》的记载。内称:“两宫太后欲召见恭亲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数辈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见。” 这是薛福成的记载。杜翰的尖酸刻薄,端华的毫无主见,肃顺的放肆无忌,恭王的忍辱谦让,都跃然纸上。薛记和樵客所记有一些地方是相同的。但有一个根本不同点。而这一点却是被史学界同仁忽略了的。这个不同点是,薛记认为肃顺等首先放弃了一同进见的机会,而樵客却说是两宫太后不准顾命八大臣一同进见。到底谁的记载更可靠呢?我认为当事人樵客的记载是可靠的。因此,造成奕单独被召见,是两宫太后行使特权坚持的结果。这是两宫太后的一个胜利。
第三是《慈禧传信录》的记载。其中记道:“既至,顺等尚阻之,不使入见,谓岂梓宫前亦不应一哭耶?端华谓阻乖于礼,当听之入,而内大臣必于偕,于是载垣、肃顺共进。” 这个记载与前两个截然不同。他认为是奕同八大臣共同进见的。我认为这个记载是不可靠的。
两宫太后以既兴奋又忧虑的心情召见了奕。这是两宫太后对奕的第一次政治性召见。《热河密札》第十二札记道:“单起请见,谈之许久。” 《翁文恭公日记》记道:“闻恭邸于初一日到滦,奏对良久。” 到底谈了多长时间?《热河密札》第七札记道:“约一时许方出。” 即两个多小时。可以想见,谈话内容是丰富的。谈话的过程史无详载。我们只能从一些片言只语的记载中窥见其谈话的主要内容。两宫太后见到了奕,流着眼泪哭诉了顾命八大臣,尤其是为首的载垣、端华和肃顺的侮慢和跋扈,“因密商诛三奸之策” 。
这“密商诛三奸之策”应该是谈话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他们详细地密谋策划了铲除顾命八大臣的步骤和方法。
首先,密商了发难的地点。奕认为热河是顾命八大臣的势力范围,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 ,“坚请速归” 。还一再说明:“南中将帅,数疏吁回銮,外国公使行至京师,设圣驾迟留不发,和局将中变。” 两宫太后采纳了奕的建议。事实证明,这是一招高棋。只有摆脱顾命八大臣的控制,回到奕集团掌握的北京,才能达到目的。
其次,探讨了外国的态度。两宫太后担心,如果在北京动手外国是否会干涉。《祺祥故事》记道:“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 《热河密札》记道:“知昨见面,后以夷务为问。邸力保无事。” 外国的干涉是两宫太后的最大心理障碍。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熄灭,她们仍然心有余悸。但是,奕在来热河前已就这一问题同外国达成了某种默契。他向两宫太后一再说明,外国“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之回京负完全责任”。“他又劝说,只要她回到北京则任何事情他都能办到。太后完全信任他的话。”
最后,确定了拟旨的人选。要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拟定拿问肃顺集团的谕旨。关键是选好拟旨的恰当人物。这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是个大笔杆子。关于拟旨的人物,史传有二,一是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庸庵笔记》载:“并召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密拟拿问各旨,以备到京即发,而三奸不知也。” 这是薛福成最先提出的。《清鉴》的作者印鸾章即采用此说。二是醇郡王奕。李慈铭记道:“而醇郡王福晋,慈禧妹也,得时入宫,两宫密嘱之,令醇王草罪状三人诏,即携入,慈安藏之衵服中,无一人知止。” 因密拟谕旨属最高秘密,不是绝对相信的人是不能嘱办的。奕是西太后的妹夫,政治态度十分明朗,是奕一派在热河行在的总代表。为此,把拟旨重任托付给他,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也确如此。两宫太后代皇帝于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发的谕旨上即说道:“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 这足以证明圣旨是奕拟定的。
两宫太后召见毕,奕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退出。肃顺本来很藐视奕,但两宫太后单独召见这么长时间,使肃顺集团有某种不祥的预感。因此,他们在对待奕的态度上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樵客”记道:“宫灯(指肃顺)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即使是肃顺集团的军机章京也记道:“六兄(指奕)来,颇觉隆重。单起请见,谈之许久。同辈亦极尊敬之。”“敛戢”也罢,“尊敬”也罢,肩担重任的奕不改谦卑的常态,“以释三奸之忌”。
即在同一天,两宫太后按照计划行事,急切地发下谕旨:回銮京师。肃顺集团没有任阿思想准备,颇感突然。他们知道这是个重大问题,不能轻易地允诺,必须坚决阻止。肃顺威胁地说:“皇上一孺子耳,京师何等空虚,如必欲回銮,臣等不敢赞一辞。”这是在恐吓作为青年女子的两宫太后。而两宫太后早已成竹在胸,她们毫不示弱地答道:“回京后设有意外,不与汝等相干。”说完之后,命令立刻准备车驾。肃顺又固执地阻止,两宫太后则强硬地否决了他们的意见。肃顺集团只得照办。这一回合两宫太后又占了优势。
奕知道时间紧迫,来不及休息。他在关注着回京谕旨的落实情况。这件大事须由直隶总督文煜承办。文煜感到谕旨来得突兀,道路维修需一些时日,未经请示,即告密云县令,说中秋节以后再开始修路。这样无形中就要后拖半个月。“恭闻之大怒” 。两宫太后听到这一情况也极为不满,又下谕旨,“催令赶办” 。归心似箭,别有所图。
奕保持着外松内紧的状态。他利用一些时间同肃顺集团的人曲意周旋,虚与委蛇。但发动政变的消息不能不有所泄露。处于中间状态的惇亲王奕就觉察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据惇亲王奕之孙溥雪斋的回忆,有一次,肃顺宴请赴行在的奕,酒至半酣,不拘小节的喝得醉醺醺的奕,居然当着恭亲王奕的面,突然手提着肃顺的辫子大声说道:“人家要杀你哪!”奕大吃一惊,然而肃顺竟毫无警觉,却低着头戏谑地答道:“请杀,请杀!”这位奕,《清史稿》记:“屡以失礼获谴。”也许能干出这种冒失事。据说,由于他泄露了政变的秘密,慈禧对他失去信任,一直未委以重任。
肃顺集团以为大权在握,从总体上看轻了两宫及恭王,以为“彼何能为”。因此,他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他们从咸丰帝死到八月一日这半个月的时间,见面也只不过二三次,而且每次时间很短。只是八月一日见面两个小时,时间稍长些。他们认为两宫及恭王不必看重,以为“自有主宰”,即心中有数。他们没有及时地分析政情,商讨对策,而是陶醉于炙手可热的最高权力的运作上。封官许愿,加官晋爵,以便拉拢更多的同党。八月四日(9月8日),由载垣等上奏,两宫旨准,匡源兼署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焦佑瀛补授太仆寺卿。匡源、焦佑瀛又拜肃顺为老师。户左和太仆这两个官缺,本应在采用掣签法时,一同放将出去。但是肃顺等却假公济私,事先将这两缺留了下来,没有参与掣签,“不枚卜而硬定者”。这使许多旁观者心中不服。至于两宫太后在载垣上奏的当日顺利地予以旨准,正是从大局考虑,以安其心。从中不难看出,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政治斗争的艺术性。
与此相反,奕在悄悄地忙于联络党人,研究对策,部署任务,为政变积极作准备。热河行在的官员因惧怕肃顺,不敢公开地去见奕,只能秘密拜访。许多官员绞尽脑汁地为奕出谋划策。认为如果在行在“能将斧柯得回为上策”,如果办不到,就“以早回为宜”。并时刻注意地保护着奕。他们期待着恭王一旦得到胜利,他们就会被勉奖为“元佑正人”。
八月五日(9月9日),肃顺集团感到奕在此继续待下去实在碍眼,八大臣便为奕向两宫太后请示行止。两宫正好利用这一机会传旨,命六日(10日)恭王上去请安,即进行第二次召见。这一消息被军机章京“樵客”得知。他连夜拜谒奕,坐谈两个多小时。他们谈到了肃顺等人的飞扬跋扈,谈到了要隐忍“稍安”,谈到了回京后的设想,也谈到了切盼黎明的焦渴心情。“樵客”感到奕“相待优厚,可感之至”。
同时,奕与“樵客”商量明天两宫太后召见时要谈的问题。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迅速回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设想一些理由,以便作为炮弹提供给两宫太后。即“元圣(指奕)日内见面,拟了一套话说”。就是为奕“拟了一套话”,以供给两宫。“樵客”献策说,一是要进一步向两宫太后阐明迅速回銮的重要性,“劝上意主持坚定”,不要为肃顺的妖言所惑。二是要限定具体回銮的日期。原来拟定的各个日期,如九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愈早愈好。并说明提早回銮的理由,“樵客”认为最好的理由是风水说,“劝王以风水之说动之”。奕完全采纳了他的计策,即“王深然之” 。
在此期间,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也在热情积极地帮助奕。《慈禧传信录》记道:“毓瑛以月余谕旨章疏号数事由,缮一单,密授侍阉而已。”他把属于内廷最高机密的皇帝的谕旨和大臣的奏章,开了一个一览表,转给了奕,为奕决策时参考。曹毓瑛在辛酉政变中是个未引起注意的神秘人物。他在政变过程中对奕集团是立了大功的。但他到底做了些什么,现在尚不清楚,有待研究。
八月六日(9月10日),两宫太后第二次单独召见奕。奕把这几天在热河活动的情况密报给两宫,并把事先商定的计策提供给她们,使她们坚定发动政变的信心。两宫太后也关切地旨命奕明日迅即回京,布置一切,不可在此逗留过久,以免事情败露。八月六日(9月10日)的《热河密札》记载此事道:“宫灯已跪安,日内回京。” 这里的宫灯不是指肃顺,而是指奕。 跪安是说奕将要起程返京,请两宫太后训示。
八月七日(9月11日),奕不敢久留,奉命回京。据说,奕在临行前曾密令他的护卫、随从,先到热河的外八庙之一的普陀宗乘庙,即俗称布塔拉庙的后门去等他。这布塔拉庙是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雄伟壮观,值得一看。奕便向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假意说道:“我就要回北京去了,听说这里的布塔拉喇嘛庙很有名,我打算先逛一下再走。可是我的底下人们还没有来。你们有轿子,让我坐一坐。”他们听说奕要走,很高兴,就连声说道:“请爷坐,请爷坐!”奕不慌不忙地坐上他们的轿子,进了庙的前门,匆匆忙忙下了轿,也顾不得参观,直奔后门而去,带上护卫就疾驰回京了。 这个传奇性的记载是惇亲王奕之孙溥雪斋的回忆,内容显然失真。因奕奉旨返京是热河行在公开的秘密,又是八大臣代请以后两宫太后所做的决定。八大臣当然知道奕何时回京。奕用不着偷偷溜掉。但是溥雪斋的回忆所透露出的杀气腾腾的信息却是不错的。
奕警惕性很高,晓行夜宿,快马加鞭,不敢久停。“州县备尖宿处,皆不敢轻居,惧三奸之行刺也。” 他急欲赶回北京。
大约在两宫太后召见完奕的第二三天,由于两宫的催促,决定于八月十日(9月14日)备齐回銮所需的200辆车,并决定内廷主位,即后妃们先行一步,提早回京。这一决定为政变创造了有利契机。可见,奕的热河之行对两宫太后决意返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手握重兵的兵部右侍郎胜保在密切地注视着热河与北京的政治动向。奕在热河期间,他于八月二日(9月6日)从距京数百里的直隶境内的威县行营上一奏章,要求到热河叩谒梓宫。并不待旨准,与上奏章的同时,即日起行。准备于八月十日(9月14日)先到北京,然后到热河。这一举动是对八大臣不准统兵大员叩谒梓宫的公开挑战。
在行军途中,八月七日(9月11日)胜保与带兵剿捻的山东巡抚谭廷襄联衔并胜保单衔上奏折,恭请皇太后圣躬懿安。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试探举动。八大臣不能容忍任何抬高两宫太后地位与身份的做法。他们以这个请安折皇太后与皇帝同列,且缟素期内逞递黄折,有违体制为理由,把胜保、谭廷襄交部议处,以示惩戒。
但胜保毕竟是统兵大员,八大臣既要示之以威,又要示之以恩。因此,在发出交部议处的同一天,又降旨特准胜保前来热河行在,叩谒梓宫。同一天,又向另一手握重兵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发出一函,例外特恩他可以叩谒梓宫,并让他自己斟酌行止,决定去留。这一谕一函,是八大臣对带兵大员胜保和僧格林沁笼络争取的体现。
再看北京。
奕在热河的时候,北京方面的上层人物正在酝酿发动一场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攻势。当时在热河的汉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把热河方面载垣等顾命八大臣跋扈不臣的情况通过密札报告在京奕集团的朝官。大学士周祖培得信后,如获至宝,大喜过望,拿给其他人看,并煽动说肃顺等图谋不轨。周祖培的门人董元醇御史秉承他的意图,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是八月六日(9月10日)发往热河的。据说,在上奏章前。“先白之、,佥曰,当” 。奕和奕当时都在热河,董元醇当面请示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许通过密札说了这个意图。总之,奕和奕是支持董元醇上书的。
与此同时,李慈铭,这位以诗文名于时的周祖培座上客 ,亦受周祖培的指派,于八月四日(9月8日),“属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他便从历史上各代贤后临朝故事中,摘取汉朝的和熹后和顺烈后,晋朝的康献后,辽朝的睿知后和懿仁后,宋朝的章献后、光献后和宣仁后等八个太后,并简略地叙写了她们的主要事迹,撰成《临朝备考录》一书。这是为政变从历史上找合法的理论依据,进行舆论准备。同时,他又结合当前事势,主张实行垂帘,“条议上之,其稿别存” 。他把这个主张两宫垂帘听政的奏折报给了周祖培,自留了底稿。李慈铭怂恿周祖培速上奏章。但周毕竟娴于官场,老于世故,在此大变动之时,他取慎重态度,先压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