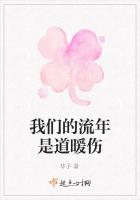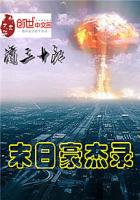儒家所推崇的唐尧、虞舜的时代,在庄子看来,只是“去性而从于心”,用老子的话来讲,就是“失德而后仁”,是失去道德之后的时代。
儒家以兴仁扬义为治世平乱之道,而在庄子看来,这样一种治世平乱之道,所突出的是对于知识的一种推崇。而对于知识的推崇,是一切社会祸乱的根源。
在庄子看来,人一旦有了知识,一旦有了是非观念,他可以干好事,也可以干坏事。而一个人干坏事的机会要比干好事的机会还要多,所以对于知识的追求、对于知识的推崇,正是社会出现混乱的根源。
庄子在《胠箧》篇讲:“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跖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物,是一个强盗,他手下有数千人。有一次跖手下的人问跖:“盗亦有道乎?”意思是,我们做强盗的有没有一定的准则呢?跖回答说,怎么能没有呢?肯定是有的。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跖回答说:
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眼看去,就知道谁有钱,谁没钱,谁家里有钱,谁家里没有钱。有这样一种能力的人,就是所谓的圣;遇事冲锋在前,这就是勇;撤退时留在最后,这就是义;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遇到突发事件,知道如何应对,这就是智;分赃物的时候,分得很公平,这就是仁。
庄子认为,在强盗内部也奉行着这样一种道德标准。所以儒家所推行的这一套仁义之道,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也可以给社会带来坏处。甚至可以说,带来的社会害处可能比好处还要大。
所以,儒家推行的仁义之道行不通,甚至不应该实行。应该实行什么?应该实行“在宥”。应当使民众自由自在,应当实行宽松的政治政策。
3. 寻求人的精神家园
庄子并不是不知道,他的这一套所谓的方针,在当时也行不通。正像儒家所讲的兴仁扬义,老子所讲的自然无为,墨家所讲的兼爱非攻一样,也不能得以实行。
为什么? 因为当时诸侯逞强,大国称霸,每一个国家都想要称王称霸,你不称王称霸,别人就要欺负你。这是每个国君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孔子那一套、老子那一套、墨子那一套、孟子那一套,包括庄子这一套,在当时都不能实行。
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包括庄子本人,不是没有对于国家治理的基本的策略,但是当时都不能为在世君王所接受。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而四处碰壁。孟子也像孔子一样,也周游列国,也到处宣传自己的思想和学说,但是他们的思想都不能为当时执政者所采用。老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也一样,也不能被采用。
因为一个当政者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生存的问题。所以当时受到重用的是法家,是法家那种富国强兵的政策。还有就是兵家的人物,也能够得到重用,因为他们可以直接解决现实的问题。
庄子对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庄子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探寻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这一方面。他更为关注的是现实的人,是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
庄子思想和前代及同代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像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那样强调社会应当怎么样;也不强调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怎么样。他更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生存;作为个人,我们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应当过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在庄子之前,无论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还是道家的老子,或者是墨家的墨子,或者是法家的韩非子,都只是从整体的意义上探讨人、说明人、把握人,而没有从个体的意义上,从个体生命的意义上,从个体价值、个体安身立命的角度,去关照人、体察人、关心人、把握人。
儒家是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派,儒家讲人,即使是讲到个人,也绝不是一个单个人,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成员。小而言之,是一个家庭成员,大而言之,是一个社会成员。他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儒家强调的是这些。强调一个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强调一个人的角色意识,这是儒家思想的特点。
在儒家那里,因为一个人是一个社会成员,在家庭是一个家庭成员,在社会是一个社会成员,所以要尽到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一个人往往成为一个符号、一种工具、某一种观念的附属品。
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个人是什么?在父亲面前就是儿子,在儿子面前就是父亲,在学生面前就是老师,在老师面前就是学生。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身份,一个人的这种身份,就限定了一个人,你只能做你这个身份所应该做的事,而不能做你这个身份所不应该做的事。你在老师面前,就要像个学生;你在儿子面前,就要像个父亲。每个人的这种身份,约束着你、限制着你。每个人就像一个演员,时刻扮演着一种社会角色,每天都在演戏,每时每刻都在演戏。
但是,一个人可以扮演各种角色,可以扮演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但却唯独不能扮演他自己。我是谁?我是什么?难道一个人就只是这样、那样一种身份吗?难道一个人就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吗?一个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是什么?自己的期望?自己的忧虑?自己的痛苦?这一切,对于儒家而言,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也许这些问题根本没有进入儒家的视野。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它所强调的不是这些,不是一个人的责任,不是一个人的社会义务,不是一个人的历史使命,而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他的精神生活,他的精神家园,以及他的精神灵魂如何安顿的问题。
我是谁?我当然是我父亲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父亲,我当然是一个老师,我也可以是一个学生,但是,离开了这一切之外,我还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我应该怎么样?我首先应当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父亲,其次才是一个儿子,才是一个老师。如果一个人连人都不是,那么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那么,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一个人应当怎么活着,抱有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而活着,庄子第一次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庄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庄子哲学的根本,形成了庄子哲学的基本倾向。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现出庄子对于整个人生、整个社会的理解、体察与把握。庄子哲学的特色,也应当从这个角度来把握。如果不能从这个角度把握庄子,那么其他一切问题,都将无从理解、无从把握。
庄子思想的意义,庄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他把一个人不是简单地只是看成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而是把他看成独立的个体,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体人的生存状态,是个体人的生活方式,是个体人安身立命的寓所。
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虽有救世之志,但任何救世之方都无由得施的时代,生灵遭受涂炭,精神飘零而无所安顿,人的生命价值究竟安在?人的精神家园究竟安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成为庄子哲学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