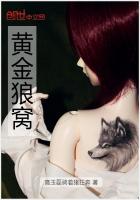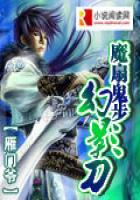Crown、Ball和圣戈班【Saint Gobain】等外资包装企业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业务,生产并供应中国市场上消费的大部分金属罐和玻璃瓶。罗氏【Roche】、DD Williamson和普拉克【Purac】等外资制药和化工企业供应大量配料,生产可口可乐在中国使用的浓缩液。一家大型全球农业企业【嘉吉】通过在中国的工厂向可口可乐供应其在国内消耗的所有高果糖玉米糖。麦肯【McCann Erickson,IPG的子公司】、奥美集团【Ogilvy & Mather】【WPP的子公司】、李奥贝纳【Leo Burnett】和阳狮集团【Publicis】的子公司实力媒体【Zenith Media】等跨国广告公司,负责可口可乐重要产品在中国的所有广告活动。外资制造企业,如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三洋【Sanyo】、Lanser、康富【IMI Cornelius】、富士【Fuji】和Maytag等,通过设在中国的工厂向可口可乐供应大部分销售和营销设备,包括玻璃门陈列柜、自动售货机和自动贩卖机等。沃尔沃【Volvo】供应可口可乐系统在中国使用的大多数高档卡车。可口可乐在中国的部分顶级分销商也是外企。麦当劳是全国最大的单家可口可乐饮料分销商。法国零售商家乐福是可口可乐包装饮料在中国最大的零售分销商,而麦德龙和沃尔玛也位居可口可乐最大的全国分销商之列。
这些外企大多数都是可口可乐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合作伙伴,在各个国家为可口可乐系统服务。它们一般拥有强大的研发、生产、品牌营销和融资能力。它们与可口可乐合作,帮助可口可乐控制产品的质量和形象,推动技术进步,降低成本,使可口可乐产品尽可能向全世界消费者普及。通过在外国市场建立生产、销售和研发业务,它们还帮助可口可乐在海外有效建立了高质量的业务。
国有企业。可口可乐在中国的价值链还吸收了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一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为可口可乐及其价值链合作伙伴指定的地方合作伙伴。太古和嘉里在中国建立装瓶业务时,都必须吸纳地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主管表示,可口可乐系统向这些地方合作伙伴“付了很多钱”,目的就是不让它们插手合资企业的管理。21世纪初,太古和嘉里的许多地方国有企业合作方之所以在经济上能够生存,就是因为把自己的合资股份卖还给了装瓶商。
第二类国有企业是积极为中国可口可乐系统进行增值活动的企业。最明显的例子包括从事装瓶业务的中粮,从事PET树脂生产的仪征,从事高档钢材供应的宝钢,从事包装设备生产的南京轻工,以及大型国有超市【例如联华、华联和农工商】等。这些国有企业一般拥有某种形式的优势,可以帮助可口可乐降低成本和风险或者增加销量。同第一类国有企业一样,它们也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受益者,但形式不同。例如中粮曾经是唯一一家政府授权的进口食品和饮料的企业。中粮1979年开始进口可口可乐,曾为太古和嘉里在中国众多装瓶企业的财务投资者。中粮的参与在中国给可口可乐带来了政治上的合法性,改革开放前期,可口可乐曾一度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中粮与可口可乐系统的历史,连同它在全国范围内的批发网络,推动了其装瓶业务在人口相对稀少的较贫困地区的发展。又如南京轻工机械集团在1985~1995年中央政府推动饮料生产设备本土化期间,培养出了碳酸软饮料包装线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当时中国的啤酒和软饮料行业都是从愿意向中国转让技术的外国制造商那里购买设备。集团许多技术和设计都是在KHS公司提供的原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类国有企业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都能够利用政策租金转变为技术进步和其他形式的可持续竞争优势。通过吸收这些国有企业进入其价值链,可口可乐可以从同样的国家产业政策中受益,能够获得较低的价格,开拓消费者渠道。
总体上来看,我国企业在可口可乐价值链的许多高附加值领域都未能赶上国外同行,包括品牌建设、金属包装、包装生产和装瓶业务领域高价值设备的生产等。1994年诺兰研究可口可乐在天津的合资企业时观察到,“在装瓶生产线制造领域,国内最好的生产商与国际行业领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些差距也带来了成本之间巨大的差别,天津公司根本没有严肃考虑过从国内机械制造厂购买新装瓶生产线的主要部件”【Nolan,1995,第27页】。到了21世纪初,情况依然如此。
其他参与者。许多企业都加入了可口可乐的价值链,努力与可口可乐系统一起在中国迅速成长。最显著的例子是两家PET供应商,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当地成千上万家小型分销商【即101合作伙伴和金钥匙伙伴】。尤其是紫江公司,2003年销售额就已突破了10亿美元。此外,港台独资企业和中间商也在可口可乐的价值链中寻找增值业务。港资企业【例如南通伞业和A-1毛绒玩具】利用市场知识和设计采购能力,在中国内地建立了制造业务,满足可口可乐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如促销奖品和市场营销设备等。位于香港的全球采购企业利丰集团【Li & Fung】,在包括中国在内的76个国家采购可口可乐需要的大??分促销奖品。台湾纺织业巨头远东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开设工厂,满足了可口可乐在中国大陆PET树脂需求的50%。其他一些台资生产企业,如铖雄【Chengxiong】和杰宏【Jiehong】等,从21世纪初开始在中国大陆向可口可乐系统供应部分低端注塑和包装设备。
价值分配
可口可乐及其装瓶商巧妙地运用了采购中的规模优势和系统集成能力来降低价值链中的成本。当一家或一组供应商变得过于强大时,可口可乐会在相同商品领域培养另一家有竞争能力的供应商来创造竞争,确保消除企业活动产生的租金和同谋关系。举个例子,当中富这家PET制造商取得巨大成功时,可口可乐又培养了紫江,与中富开展竞争。根据可口可乐主管的说法,铝罐生产商曾经串通起来人为抬高铝罐价格。可口可乐就培养了一家钢罐生产商宝翼制罐,旨在压低铝罐生产商的价格。可口可乐培养了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PET树脂生产上与远东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竞争。可口可乐也与南京轻工机械集团合作,生产较便宜的包装线设备和零部件,使KHS和克朗斯【Krones】的产品报价降低了65%之多。可口可乐与嘉里集团合作,建立了价格更低、供应更稳定的食糖替代品。可口可乐的系统集成活动不仅将价值链的价值创造最大化,还确保可口可乐系统【即可口可乐及其装瓶商】获取价值链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
利润如何在可口可乐系统内分配,是可口可乐与全世界装瓶商之间永恒的争论焦点。传统上,可口可乐品牌的实力确保可口可乐能够在业务体系所创造的价值中获得相对较大的份额,有时候甚至是绝大部分。不过,在新兴市场中,装瓶商往往对可口可乐有相当大的议价能力。装瓶商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议价能力,是因为其庞大的分销网络和丰富的客户知识。太古公司的一名主管表示:“我们把系统利润的五五分成视为我们和可口可乐之间一种比较公平的分配方案。可口可乐在品牌上进行投资,而我们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积累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消费者知识。双方的回报理应一致。”一名可口可乐主管也同样打了个比方:“可口可乐是指挥身体的大脑,而装瓶商是四肢,现在血液是同时流向大脑和四肢。”
势力平衡的变化也使可口可乐和一些装瓶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发生了改变。根据太古的说法,可口可乐希望在亚洲之外主导和控制装瓶特许经营权。可口可乐就是对“装瓶商缺乏信任和信心”,要求在装瓶商出现问题时接管特许经营权。对太古而言,它与可口可乐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交易关系转变为“基于信任和透明度的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浓缩液价格不再是争论不休的价值分配问题,而成为了一种现金流机制。可口可乐为了建立信任和透明度,甚至可以向太古“公开账簿”。另一方面,太古却拒绝了可口可乐转让具体客户信息的要求,因为这些信息是装瓶商的核心资产。太古饮料有限公司的一名主管表示:“可口可乐与太古之间的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理论上来讲,我们应当用同一套账簿,在实际意义上最终成为一家公司。”
价值链的底层:广西蔗农
可口可乐价值链通过其商品供应商及劳动密集型生产商运作,影响了中国千百万低收入劳工的生活。广西省每年生产的甘蔗占全国将近一半产量,而可口可乐系统是广西省甘蔗最大的采购商之一。它从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国有糖厂购买食糖,糖厂从当地蔗农那里购买甘蔗。在南宁糖业的例子中,当地政府划拨给制糖厂80万亩甘蔗,分布在6个县,有将近40万蔗农参与种植。如果将这一相同比例也适用于可口可乐其余食糖供应商,那可口可乐价值链就触及了我国将近200万农民的生活。
我国的制糖业传统上受政府扶持,包括进口控制、关税以及在糖价、甘蔗价方面的规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省政府向国有糖厂分配甘蔗种植地以保证甘蔗供应。实行市场化改革后,糖厂和农民之间的排他性契约关系保留下来。尽管农民们现在可以选择种植作物,但甘蔗仍然是一种受欢迎的作物,因为有政府定价的保证和国有糖厂提供的各种补贴。糖厂通过一系列措施扶持蔗农,包括提供购买化肥的资金,为新开垦的土地提供免费的化肥,推广高产甘蔗种子,供应农用设备【例如拖拉机】用于开垦新土地,还提供技术指导【例如如何最有效使用化肥】。糖厂还负责建造、维护通往甘蔗种植地的所有道路。
政府的支持使国有糖厂和农民都受益,但是程度各不相同。糖厂和农民之间价值的分配取决于政府确定的甘蔗价格。甘蔗价格为每吨180元人民币时,每位农民种植两亩甘蔗每年可获得1000~1200元人民币利润。广西省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3000元人民币,也就是每天不到1美元——低于联合国的贫困线【按2005年7月前汇率计算】。甘蔗收入通常约占农民总收入的1/3。蔗农的状况与国有糖厂工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南宁糖业,每位全职工人平均一年工资是1.6万~1.7万元人民币,是农民收入水平的5~6倍。此外,糖厂职工还享有其他福利,有医疗保险、住房补贴,还有工厂的体育和娱乐设施。
农民之间的状况也有很大差别。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时,很少有人留下来耕种政府分配给他们家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户把土地卖给邻居,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拥有大片土地。卖掉土地的人在城里或大农户的土地上做临时工。21世纪初,广西省南部一些富有的农民每户拥有的土地多达1000亩。这些农户在旺季可能要雇用30多个临时工帮忙收割甘蔗。临时工大多数都是外地的农民,负责收割、清理甘蔗、扛到称重站,每根甘蔗可以得到3分5厘的报酬。有经验的人手通常可以在收获季节每天处理1吨【或约1000根】甘蔗,每天可以赚35元。
改造本地企业
可口可乐及其国际价值链合作伙伴通过价值链互动,对许多地方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口可乐国际合作伙伴提供了先进的机械,使本土企业能够比较迅速地提升实际能力。通过购买KHS公司的包装生产线,中粮获得了现代化的高效生产能力,成为可口可乐在中国的3大装瓶商之一。通过向赫斯基【Husky】公司购买先进的PET注塑机,向西得乐公司购买PET吹塑机,使珠海中富和上海紫江等地方创业公司迅速成为可口可乐系统在中国的主要PET瓶供应商。通过向Sinco公司和Bueler公司购买PET树脂生产设备,仪征成为可口可乐系统在中国的第二大瓶级树脂供应商。许多地方供应商在成为“可口可乐供应商”后,能够迅速扩张到其他领域,因为这个身份能够得到其他商业客户的直接认可。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可口可乐公司本身在进行产业规划时,也向其地方价值链的合作伙伴转移了大量系统知识,包括技术标准和市场营销知识等。本节将具体考察几个案例,阐述可口可乐系统对地方企业的影响。
改变中国软饮料行业
可口可乐在改变我国软饮料行业方面的作用必须在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我国在软饮料生产上遵循的都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和集体所有的饮料生产厂服务各自地区,纯粹是作为制造厂经营的,几乎没有品牌和市场营销业务。碳酸软饮料是唯一的软饮料产品,玻璃瓶是唯一的包装形式,品种也不多。到了80年代,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使国内对软饮料生产的投资激增。根据诺兰【Nolan,1995】提供的数据,1981~1991年,我国软饮料厂总数从130家增长到2700家,到1993年已有多达7000家广义上的“软饮料厂”。大量饮料生产厂规模都很小,使用手工生产方式,通常造成原料和能源的大量浪费。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也经常引发令社会震惊的卫生问题。1991年卫生部的一项调查发现,当时我国只有36%的碳酸软饮料厂符合国家技术标准【Nolan,1995】。
在此背景下,作为国家饮料业现代化产业政策的一个关键策略,可口可乐被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家轻工业部决定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合作,以少数大型合资企业为中心升级中国的饮料产业。这些企业的每一家工厂都可以利用提供给专营装瓶厂的浓缩液来生产品牌产品。行业产出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工厂,有利于提高质量,完善安全规章制度,同时减少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