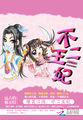一大早,蓝强和香秀告别老师和师娘,抱着自考书,在断桥分别后各自回家。蓝强把凉鞋脱下来在河里冲刷干净,在马路上随便扯了几根何首乌藤编成绳子,把鞋子拴在腰上,打着光脚板沿着河边的马路行走。
马路与河之间本来隔着一块水田加一个土片的距离。现在挨着河的田浮上一层黄泥浆,陷进里面的水葫芦还保持向前赶路的样子。今早开出的紫色小花倒端正,它全然不知昨天惊心动魄的故事。土片被河水冲刷后像刀削一般,豆苗都被拔走了,干油菜、鹅儿肠和断肠草这些杂草与泥巴混为一体。这种平常狭窄斜睨,只是在田土之间起着过渡链接作用,被人遗忘的土片看起来终于和它的名字相符,如切后的肉片儿一样光滑平整。
马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修的,只有一丈来宽,称为机耕道。机械化没有实现,曾经在上面啪啪作响的拖拉机也被淘汰,现在倒成了独轮的鸡公车和两轮摩托车的天下。四轮货车一般到断桥就不再往前开,因为这条泥马路一下雨就打滑。而这里的天气是阴雨多,晴天少,即使晴天也得多晴两天,等稀泥晒硬了才能承受重压,因此大车子受阻就成了家常便饭。这条泥马路倒因祸得福,那边比它坚硬的石子路变得坑坑洼洼,它却能够依然保持平平展展的容貌。这当然得感谢那些生命力特强的白茅草、铁线草和牛耳大黄之类的杂草,有了它们全身心的覆盖,马路好像永远葱绿年轻。
走在草上,软软的,还沾不到泥,感觉特别舒服,蓝强有点后悔脱掉鞋子。
当然他不会穿上,这条舒适的草路只有三里左右,尽头是一条名叫跳蹬子的桥。所谓桥其实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没有桥面,十六坨四四方方的石墩,间隔一步左右排成一条直线,人在上面走只能像青蛙一样跳。看见脚下流动的河水,听见哗哗的声音,从未走过的人要么觉得惊险刺激,要么不敢踏上一步。不过对于河对岸樱桃村的人来说这是老虎吃豆芽,小菜一碟。他们可以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在上面来去自如,抬着两三百斤的肥猪行动自在。鸡公车想过去也随便,在上面搭几块木板,老手就可以晃晃荡荡地奔走。要稳妥起见就得费一些时用木桩固定,上面用钉子钉一些木板,搭一个箱架。当然不是遇到修房子这样的大事谁也不会如此麻烦。
昨天这些石墩全都消失在洪水里,今天得以重出河面。蓝强不时把脚伸进水里搅几下水,一蹦一跳过了跳蹬子,就算到了村里的地界。守着河的这个队是五队,穿过五队的地界得一直爬坡上坎,路很滑,蓝强扎紧脚趾,也险些“吃坐坐肉”。
走了十来分钟,终于走到山脊上,那是七队,自己的地盘。说是山,大都只高出地面几十米,在真正的山里人眼里不过是“馒头”而已。山头大都是一圈一圈倾斜的土围着,树很少,不高的庄稼长在上面,远远看去的确像一个个不太平整的馒头,连大小形状都差不多。蓝强旁边的这座山却不是这样的山,它上面也是土,种的还是庄稼,可它的形状却像一座官帽,而且是有两根长长的翅往外延伸,帽型方方的宋朝样式,大家都叫它官帽山。它的正对面一座“馒头山”的肚皮上有一座土墙房子,过去农业社的保管室,现在就是蓝强的家。
蓝强家左面还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山,大家都叫它大山。名副其实,它又高又大,看起来就是由一块巨型石头横放在上面,上山的道路陡峭,山上有几块土,很贫瘠,大多长着野生的树子。据说上世纪大炼钢铁前大山上全是茂密的树林,晚上还能听见狐狸的声音。现在树虽然不多,也不是很大,但也使它的高度增加不少,神秘感突显很多。大山可以说是桃塆乡第一高。它的后面盘旋着的是断桥河的上游。它的前面坡地上到官帽山脚下住着的人家是六队的,村长夏清明就在那里。六队七队都靠着大山,所以外头人眼里称这两个队都叫“大山”,队里的人自然获得“大山的人”这个称呼。
“你回来啦。”蓝强八十二岁的外婆头缠灰白色洗澡帕,身穿深蓝色卡其衣服,打着光脚板,乍一看就是一个老头。她挑一担粪要去浇菜,见外孙儿回来招呼一声就打算下场坝。
“婆,路这么滑,你不要出去,小心摔着你。”蓝强赶忙跑上去拦住外婆。蓝强的外公死的早,外婆只有一个女儿。在蓝强一岁多时,外婆就搬到女儿家来了。人人都叫她李大婆,一天到黑没一刻闲下来,总是忙于煮饭找柴扯草,这不还挑粪呢。
“涨水啦,茅厕满了,不挑咋办嘛?”李大婆是个只管做事不管能不能做的人,只要想到,半夜爬起来下地也是常事。
“好啦,放下,我来。”蓝强伸手去接外婆肩上的扁担。
李大婆却挑着走开了。她边走边说:“都快成大学生了,还干这些?你外公从不干这些,连饭都要我给端拢。你呀,就不像个读书人的样子。”蓝强的外公是一个私塾先生,听说很有文化,教出的学生有好多是当大官的。可惜蓝强从没看见过,连一张画像也没有,唯一与外公有联系的就是一个残破的黑漆狮子头模样的笔筒。外婆说这笔筒是外公放毛笔的,还说很值钱。
“你怎么才回来?”蓝强妈李桂兰从屋里跑了出来。留着上海头,穿着大号男式T恤,单薄的身材似乎连一个影也没有,四十多岁的女人看不出一点女性特征。
“我去老师家啦。”蓝强一闪身跑进自己屋里。屋里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架床上罩着硬邦邦的麻布蚊帐,挂蚊帐的钩是蓝强自己用铁丝扭的。床对面是一个三层的书架,上面放满蓝强从小学到高中的课本,还有到旧书市场买来的四大名著和林语堂《飘在大海上的晾椅》之类的闲书。当然所谓的书架也是读初中时,他借邻居的锯子矬子等工具自己做的。
进深一丈五的屋子,只有一个一尺见方的窗子透一点光线进来。现在这屋是以前队里的保管室,房子很宽很高,就是没有窗子,没有亮瓦。买下时,蓝强请求父亲安窗子,可是父亲虎着脸说:“忙安窗子,你真是想好还要好!要安自己安!”是呀,这屋宽敞、向阳,的确比以前山脚下只有一间,房顶上还长草的房子好多了。可是光线对于读书人来说又多么重要,不过他再也不敢提。反正一泡尿夹不死活人,办法都是人想的。跟王表叔借石匠用的钻子锤子,打穿一尺来厚的土墙,镶上木条,一个窗子就出来了,光线就进来了。
窗子下面妈妈买回的写字台也是在他多次修正,多次“贴膏药”的照顾下,才站到今天的。写字台上放着的只有当收音机的录音机算妈妈在他身上投入的最大本钱。正中的台灯是他的发明,花线牵着的灯泡用木头架支着,灯泡上罩一块弧形的硬纸。这屋里唯一显得光鲜的就数外公那个笔筒。
躺在谷草铺的床上,如芒在背,左翻右滚他都觉得不舒服。“农民”二字像标枪一样从各个方向射来,眨眼功夫,蚊帐、墙壁,席子……好像哪里都被射中。老师讲过甲骨文、金文的“民”字,正像以锥刺眼之形,其本义原指奴隶,引申为被统治者,其中包括奴隶和平民,后来也泛指普通老百姓。今天的职业划分里只有与农有关的还用这个“民”字,像“村民”“农民”,这也许说明农民身上依然打着千百年来奴隶的烙印。低贱、普遍、被奴役、被虐待好像是农民的专利。而事工事商的则称“人”,如“工人”“商人”,甚至从军从武的兵都可以叫“人”,即“军人”,连“学生”的身份都比“农民”高贵。
蓝强想到这些越来越为中国农民愤愤不平。人们总是利用农民的朴实善良勤劳夺取他们的劳动果实,抢占他们的精神世界。他现在就要当一个顶天立地的农民,让世人知道农民并不是一个群体象征,而是一个个有生命,有血肉,有情感的人。可是连老师都不能理解,谁还会支持?父母会怎么看?从小到大同父母的关系若即若离,有时对他们的极端节约也心怀不满,可他是一个孝顺儿子,从来也不愿意惹他们生气。家虽然不温暖,但是他知道他们爱他甚过一切。在父母眼里他就应该是读书人,无论“烧胎”还是算八字,不管老师还是乡邻,都说他是读书的料,是能跃出农门的鲤鱼。十九年的含辛茹苦,十九年的望眼欲穿,揭开锅盖一看,竟是一溜烟的空气,他们绝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天大的玩笑。就像一只从小特别受优待,开小灶,不关鸡笼的母鸡,养得肥肥胖胖的,竟然下软蛋,它的结局一定比鸡笼里的瘦鸡更遭到主人的唾弃。
想到这些,他倒希望自己是野人,一个人住在山洞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闭上眼睛看到香秀,又为自己野人的想法感到好笑。如果真是一个全身长毛,高颧骨窄额头的野人站在那么一个清纯可爱,淡雅脱俗,亭亭玉立,如红樱桃般秀美,如指甲花样娇艳的姑娘面前,该是一个多么传奇动人的神话呀!
不管三七二十一,他真像野人一样跳起来,在书堆里翻出初中毕业照。一下子看出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三个的小女孩就是香秀。“又黄又瘦,眼睛还看着地面,竟然还不好意思。三年不见,真是‘女大十八变’,我都差点没认出你来了。嘻,都当老师了,还哭鼻子,看来还是个小女孩。不过,你本来就比我小一岁,我是哥哥,哈。”蓝强对着照片上香秀喋喋不休,全然忘记自己的烦恼。他不自觉地把嘴巴凑上前去,又像碰到弹簧一样缩了回来。撕下两张作业本纸,小心翼翼地把相片包在里面,重新放回书里,瞥见窗外一只麻雀飞过,他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昨天,对香秀真的应该好好解释,她是农民的女儿,应该会支持的。这样想着,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找了一把锄头,走出房间。
“你在干啥子?”蓝强的父亲,蓝丙一只穿着一条短裤,显露出古铜色的肌肤和板结成块的肌肉。他手拿一根长竹竿把一百多只生蛋鸭子赶到河里,回来看见蓝强正在房子旁边的竹林下面挖土。
“我想挖一个池子。”
“挖来做啥子?”
“喂点泥鳅。”
“你想凑大学的学费吗?你妈早准备好了。”
“不,我不读了。”
“你说什么?”
“爸,我考不上,不读了。”
听完这句话,蓝丙一将竹竿往地上重重一掷。啪的一声,竹竿碰到石头那一节破成了竹片,颤巍巍地发抖。
蓝强偷偷乜了一眼被父亲握得黄荆杆色的竹竿,感到自己的话刺伤了父亲的心。用了十年,连鸭子也能辨认的又长又直,握在手里刚好一拳的竹竿是父亲的心肝宝贝,他总是轻轻拿,轻轻放,生怕太阳晒,生怕雨水淋。虽说父亲是火炮脾气,但是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发过火,摔过东西。现在父亲亲手把它的心爱之物摔破,把他的希望愤怒地砸碎,蓝强相信电闪以后马上就是一声大炸雷落地。
他不敢抬头,静静地等待着父亲的发落。可是蓝丙一既没有制造风雨也没有响雷,闷声闷响地走了。他觉得这一声闷捶打在身上比被十万个响雷击中还难受。可是他不想解释,唯有赶快做出成效,方才是最好的语言。他计划用一个星期挖出一丈见方的池子,然后打些泥鳅放在里面。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他却想一口气挖一个金娃娃,做这个不花本钱的生意。泥一挑一挑地倒进竹林,将那些恶臭难忍的腐烂的杂草掩埋。那么多的草,蓝强想到了兔子。先向别人赊,等兔子卖了再还,岂不是有了第一桶金。
“你究竟要咋子?”李桂兰从屋子里跑出来,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蓝强。
蓝强抬头望了一眼,发现一直有病的母亲脸色铁青,嘴唇发抖,瘦削的身子好像一个空口袋,风一吹就会栽倒。不想成为那一股风,把母亲往坑里推,可他就是一个过河的卒子,死不回头。把眼泪往肚子里吞,他咬紧嘴唇,装哑巴。
“怎么,你闭着嘴巴以为我就不说啦?你这个核桃,老娘不敲你你硬是不知道!我和你老汉一天到黑像磨子一样转来转去,拿钱供你读书,哪一点对你不起?你要什么买什么,你要做啥子,从没挡过你……你读了十多年书,到头就学会喂泥鳅吗!我,我真的不该让你去读书,整了十几年,啥子没看到,就看到一个凼凼!……你还不如你哥,你哥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挣了钱不说,还学会了说话……”李桂兰数落半天,泣不成声。擦了擦眼泪,看了看埋头不作声的儿子,她把擤在手上的鼻涕往围腰上一揩,边走边甩下一句话:“牛教三到就晓得转弯,你这条犟牛硬是读书读傻了,干脆跟你哥去打工!”
母亲的每一句话像针一样刺着蓝强的心,他知道自己对不起父母,父母供他读书从没说过要他回报什么。父亲是孤儿,母亲是独女,从小吃尽各种苦头,他们真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再像他们一样过矮人一头的日子,当老牛般的农民。他们日夜盼着他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盼望着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父母的眼中只有官帽山,蓝强心中装的却是大山。他的梦想,他的追求比考大学更高更远,这能跟他们说得清吗?
“蓝老幺,你给我起来!喂泥鳅有啥子出息?石板上栽葱,扎不下根,你晓不晓得?你太公就是抠泥鳅出了名的。他左手向烘笼,右手抠泥鳅,没下田就知道哪里有泥鳅哪里没有,云贵川都跑遍了,最后有什么出息?连半块瓦片都没有。你爷爷是个盖瓦匠,帮别人盖了一辈子房子,自己照样东借西挪,连一个窝也没有。我十二岁就去打煤炭干了二十年,好不容易攒钱才买了这个房子。老幺,好袄做成破马褂,穷折腾,农村整死整活都没得干头,你不要当傻瓜呀!”蓝丙一蹲坐在阶沿上,抽着叶子烟语重心长地给儿子摆起家世,希望软化儿子的心。
他就两个儿子。老大今年二十,为人老实,读书不行,曾经跟他一起打过煤炭,出去帮过馆子,现在在首饰厂打工,搞水磨。对老大他没有啥子希望,也没花啥子心思,只希望他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老幺就是他全部的希望,老实说读大学不管是三万五万他已经给儿子凑齐。没想到这老幺一点不争气,难道就让他回家揉泥巴坨坨?蓝丙一越想越觉得没望头,搓着老脸呜呜地哭起来。
蓝强很想上前抱住父亲,给他说自己不仅要喂泥鳅,喂兔,还有喂羊,喂牛,喂鱼。他想说,自己就是要用读的书来干这些事,干出一番祖辈没干过的大事业。可他和父母从没亲密过,知道父亲脾气急躁,是不会听他解释的。只要一开口,父亲准会气得脸红筋涨,破口大骂。蓝强依然一言不发,沉闷的空气比砖石还要重,压得两爷子缓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