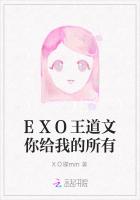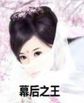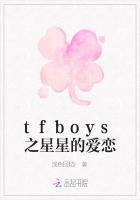有什么呢?真的没什么。《十日谈》作为故事片拍得很是一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艺术上则好一些,性的镜头也略有一些;《最后的原始部落》其实是人类学的题材,有学术性,但绝不通俗;《人体奥秘》全面地介绍了人的各种器官,并不仅限于性器官,而且画面大量使用电影(或电视)特技,冷冰冰的;《超级杀手》是国产的谈改革开放以来性病情况的片子,充满了说教的味道;《初尝禁果》呢,是生孩子和养孩子的事,专业性颇强,大约最适合妇幼保健站的干部和职工学习用。
坐在放映厅里,我暗暗发笑,并且惊叹“性”的难以置信的凝聚力,它把那么多平素可能是极少看书学习(因为工作太忙吧)的人召来,让他们自愿掏钱(五元,不算便宜──如果他们在看之前就知道是什么内容的话),并且接受正儿八经的家庭教育,我真是服了。
以上是有关统计的一些闲话。实际上统计是什么呢?我想起了一茶杯,这个杯子里有一些倒进去不久还冒着热气的白开水,现在你往里头掺些东西。掺了氰化物,不管谁喝了都会立刻死去;掺了果珍,那就有一种升空的飘动感;掺了深山里出的茶,你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掺些咖啡呢,说不定明儿就能变成某国驻某国的文化参赞了。最后,什么都没有掺,白开水还是白开水,那么喝起来,它总是淡而无味的。
淮北纪事
淮北是我的老家。这种老家的意义已经有点宽泛了:我父亲的祖籍在泗洪县梅花乡(六十年代以前也为安徽属地),母亲的祖籍是泗县山头后王沟村,我出生于蚌埠淮委医院,但却是在淮北宿县长大的。高中毕业后我插队到了灵璧县向阳公社大西生产队,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在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来来去去,总离不了淮北。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淮北是什么样的呢?在一篇创作谈里我这样说它:
所谓“淮北”,顾名思义,就是淮河以北。因为淮河及其他许多河流(包括现在已经消失的河流,例如泗水、汴水等)的冲积,淮北成了土地肥沃的平原,即淮北平原;假如它再与河南、山东、江苏的一些地方联系起来,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它又成了大平原,叫黄淮平原。这也许就是地理的最简单、也是最基本而又准确有效的组合方式。于是每一个人,就都被涵盖在这种大同小异的组合之中了。我觉得,这正是生命(和其他)发展的全部奥秘。
当然,淮北又是独到的。就像另外一个人体会他自己的地域一样,没有在淮北长期生活的经验,是不可能细微地体验或占有它的独特的。淮河是一条深奥的河,它同秦岭等连接起来,就成为我国南北地理的一条分界线了。所谓分界线,并非无力亲受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地理学为了方便而大致匡定的一条试题答案,它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那就是当我们由南而北跨越淮河时,我们马上就进入了北方——温度的差别和(因地理因素而形成的)习俚的差别,立刻就会提示我们的身体和感觉,非常明显,泾渭分明;橘生淮北为枳,就是这种差别的实践及佐证。
这是实在的大家都能有目共睹的淮北。但在我的心目中,还有一个虚构的淮北存在着:一个以实在的淮北为基本框架,以我数十年岁月积累起来的习惯、感触、亲情、友情、乡情、愿望、人文理想……为填充物的构想中的淮北。这构想中的淮北,是实在的淮北的补充和延展,我在小说中用“濉浍平原”这个自制的概念来代替它:
《人种》:濉浍平原远古的生活、生存场景。
《王》:濉浍平原有文字记录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谋略、文化史。
《焚烧的春天》:濉浍平原乡村一隅发生的爱情故事。
《幸福的王仁》:濉浍平原小城镇里的感慨人生。
《飘荡的人儿》:濉浍平原上的一段伤心传奇。
《有太阳炙烤的焦黄色天空》:濉浍平原上心灵的干燥和焦渴。
《乡村里的秀梅》:濉浍平原上歌哭着的知青生活。
……
但是现在所有关于淮北的这一切——实在的和虚构的——也都还不能满足我对淮北的周期性的渴念和暗想:我离开它似乎越来越远,时间的间隔也越来越长了。像一个断奶的孩子或者被逐出家门的弃子,我常有焦躁和暗自垂涕的时刻和愿望:淮北是我的淮北!我的淮北,谁也夺不走!夺不走!当然,谁也无法从别人的头脑里夺走本属于他的东西。一个人出生了,长大了,后来经历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又死亡了,他无法多次挑选老家、屋檐、亲邻和泥块。他的感情还能寄托在哪里呢?他还能依靠谁呢?他还能为谁而歌哭、为谁而站着生死、为谁而承誉受辱呢?于是我只能在都市冷热无定的壁垒里,每天都打点了小包,随时准备启动我的脚步,走到淮北的土地上去。
那是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的故事:
春天:春天少见的一场狂风暴雨把我驱赶到五河县桑庙乡乡西麦场边的一户农家。夜寒风冷,淮北农民都是绝对好客而朴实的。他们(一对年轻夫妻,有三个女孩,其中一个是超生)让最好的烟给我抽,又专炒一盘辣椒给我吃。晚上我睡在锅屋的麦秸里,棉被上油汗的腻味熏得我无法入睡,但后来我睡着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直到天亮。
仲春: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个人横越了灵(璧)南正在耕耙的土地,横穿了大西生产队的田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十几年前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我没有任何准备,不敢随便闯入人家,可是庄外忙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注意或认出我,我也没认出一个村里人。最终我控制不住,走进了记忆中队长的家,但那里不是队长的家,而是西学红的家,他是个有知识的人,当年我们可没少拉拢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的军事力量。
队长家搬到村外去了,那里已经盖起了成片的瓦房。
夏天:我住在向阳乡唯一的一家地铺旅社里。蚊子扑头盖脸地飞来,晚上很晚了七八个互不相识的旅客在店东家的锅屋里(用棉柴)烧火下一大锅面条,然后个个用海碗狼吞虎咽倒进去两三碗没有油只有盐的粗面条。
秋天:我再一次穿越向阳乡的土地,在新汴河的渡口上,我知道有一个人死掉了,他是地主的儿子。他娘很早就守着寡,我下乡的第一天就是他赶着牛撬在冰天雪地里把我接进庄的。他总是成为别人的笑料和欺侮的对象,到了三十多岁他还没能结婚,他娘死了,后来他自己也去死了……冬天:固镇县汽车站南墙根(太阳能照到的地方)有一个被父母丢弃的小孩,许多人围着看。小孩长得方头大脸,身上穿得干干净净,手里拿着一块蛋糕,睁着惊慌的眼睛看周围的人。有人说,是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妻丢的,刚才那两个人还站在车站对面的商店门下往这边看——是看可有人抱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抱他们的孩子?——后来孩子被车站里一个扫地的老头抱走了……这将是很长的一个故事哪!
……
这就是我的淮北的故事的一部分。
让我在淮北四月的风沙里倒下去,让我在淮北化为泥土,化为一缕轻风,化为村庄的带有猪圈牛棚腥臊的气味。
拥抱淮北,那是我三十年无时不有的愿望:
我曾徒步走遍濉河。
我曾徒步走遍沱河。
我曾徒步走遍浍河。
我曾在淮河两岸数月徘徊。
我曾无数次骑车下乡,无数次穿过淮北的村庄,无数次站定在农民中间成为他们身边的一棵杂粮。
……
“我不敢从堤岸上降下去和他同行……他开始说:‘在你末日到来之前,你便走到此地,究竟是什么机会?什么命运?那位引路的是谁?’我回答道:‘在地上的时候,我还在清明的生活之中,我迷途在一个山谷里了,那时我的年纪还没有达到鼎盛。昨天早晨,我走出山谷;在我逢着危险,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我前面,就是他引我经过这里,走向归家的路。’”(《神曲》)有它的引导,我找到了归家回淮北的路。
淮北的故事,已经成为我生活和命运的一部分了。实在的淮北和虚构的淮北,在一个人的头脑里,在一个人的书里,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那么下一部是什么?下一部是《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或者《濉水县里的龙族》?——都还是淮北佬的故事,都还是濉浍平原的话本,都还是江淮大地的传奇,都还是这方土地上开的花,养的苗,结的籽实!
——这也算是,一个淮北佬的自白?
最后两天
一觉睡醒,忽然有一种末日感。心想:今天这是什么日子,这是什么样的好日子,或者坏日子,会令一个生活过得还算开朗的人惊乍乍地惶悚起来?会令一个还算沉着的人看天会觉出天的促狭来。看地会觉出地的局迫来,看自个的“前程”会看出一片玄乎来,看社会看“人生”会看出苍苍茫茫、跌跌撞撞、大江东去、逝者如斯、前拥后搡、嘈嚣挤兑来?
原来是一年里的最后两天了!原来是一个人离天地的旨意又近了一年了!原来是一个人在人群里的玩耍又要告一段落了,(“大人”又要喊我们吃饭了!),原来是又要到了我们快要睡醒的时候了。
鹞子一样翻身下床。急什么呢?原来是急着要在这两天里,赶时间把一年里没做完的事都抓紧做完呢!
先伏在稿纸上横、竖、撇、捺了一会;然后就骑车去看早就该去却成年不见的友人。听说某中央领导人来,这事(国家大事)有点关键,一定得听听省台的新闻节目。回家时折向菜市带回来一大兜青菜(算是对妻子一年操劳的总结性补偿);去单位时见到每一位同志都充满真情地问候一声;在大街上别人碰了我,我赶忙下车发自内心地说一声“对不起”;盘点一下存粮明天大米可能会有回跌(报纸上说的)一定得瞅准时机搬回来一袋;发动全家大扫除,该扔的扔,该卖的卖,该留的自然留下;马上去给女儿请一位最好的钢琴教师,这事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孩子长大后“反叛”老爸就会师出有名,那时后悔都不再能来得及;从书架上清下来一摞书放在床头桌边,叮嘱自个儿一定要在两天之内读完,哪怕仅仅浏览一遍也算勉强过关;狗市的古玩又增加什么新品种了吗?花市的大门现在不知向哪儿开了;×××(歌星名)正在大戏院疯演明天是最后一场,怎么也得想法子弄张票进后台,找她在白衬衫上签名留念,不然这机会永不会再来(多么遗憾);还得上皖西豫皖交界的史河沿岸走一趟,那是我好几年前就许了愿的,我还得带上我自制的邮折,在那里一个世界上最小的邮政所盖一枚新年伊始当日的邮戳……坚持着一定要把一切干完!干到元旦前的几小时,偏再也干不动了。扔下手里的所有活计,不顾一切地上床喘歇着了。——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那必定会像往年一样,成为一个庄严的时刻。我怀着一种忧虑的心情躺在床上,看似水流年在我面前款款淌过。也许真的我该责备我自己年复一年的懈怠了。但我又确实已经竭尽所能尽力而为了!——无论到何年何月,这都将是我最后的回答。
新年的钟声响了!
一夕三梦
昨夜里睡得晚,但睡倒之后,却连做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是上面派我到铁路某部门任职。我到了之后,发现那部门工作太专业了。我焦虑万分,学又学不会,每天度日如年,真是活受罪。
第二个梦发生在一栋破败的高楼里。那栋楼十分高,但其被毁坏的情状又像是刚刚经受过一次战争的打击。楼里的人非常多,拥挤不堪,我好不容易从楼的高处挤到底层,突然想起一件很小、但对我很要紧的东西忘记带下来。我出一身冷汗,只好重新挤进人堆,颤颤走过折断的楼梯,心力交瘁、毫无希望地往无限高的楼上挤去。
天露微光时,我靠在床上,半醒半睡地做了第三个梦。
这次是春天了,是懵懵懂懂的春天。梦境中的一切都很逼真、具体、活灵活现:报纸上宋体绿形的植树节消息;广告中完美无缺的新娘子妩媚一笑;第一株白杏花开在干休所一家老干部的小院里;阳光照在镜子上,美发屋里挤满了粉黛;两个骑自行车来到很远的郊区的时新年轻人跳下车在田间小路上猛吻;一队好小好小的一年级小朋友拉着手、排着队、唱着歌、牵着各色气球,走过市区的街道;在田野里干活的一个中年农民上身光着膀子,下身穿着棉裤;扎小辫的丫头面前堆着一大堆野荠菜,许多油头粉面的女市民团团围住哄抢;阳台上晒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气味迥异的棉被;柳絮铺天盖地地纷飞,迷入人的眼睛;……做完三个梦,我就彻底醒来了。我歪在床头,听了一会电台的晨间节目,又看了一会昨晚看剩下的晚报,然后就自己解析了夜里的三个梦:第一种解析是我太累了,我无力解决我在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那些难题,我需要轻松的气氛和环境──就像春天──来抚平自己;第二种解析是我从投入走向了虚无,我幻想摆脱困窘,对所有的疑难都一概视而不见,只顾一头栽进某种虚设的温柔乡去;第三种解析是我正确地面对了纷繁的现实。既有曲折、磨难、灰心和无望,又有光明、美好、亮丽的明天。
像往日一样,这“紧张、曲折”的一夜也就完全过去了;我要说一声:再见,我的梦!我又要投入为自己设置的高速的运转之中去了。
盛夏的随笔
这个夏天热得比较晚,到了七月的中旬才热起来,而此时女儿的高考已经结束,进入了估分、填报志愿的阶段。对家长和考生来说,估分数、猜学校、冒风险、求稳妥等等,这都是大伤元气的事情。对女儿来说,她上一个文科的重点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上哪个学校,就颇为难了。报分数太高的学校,会有风险,报分数较低的学校,又不甘心。这几天就因为这事,我和女儿吵了一架。我未让她,她更不可能让我,她很伤心,我也十分沮丧。
吵过架的第二天,我一个人在家,天气酷热,我心里倒万分地宁静了。我先做了一些浇花上水的事情,出了一身汗水,精神上却像解了毒的一般,轻松万端起来。洗过澡以后我来书房的书柜里找以往七月的记载,看看那时候某年的七月我是在做什么、想什么。看看那时候的七月,我的心理的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其实只是一种度夏和排遣郁闷的方式。
一伸手就找来了1976年夏季的一天、7月初的一天,那时我正在淮北农村插队。那一段日子,我们在河东的岳河子(村名)附近的新汴河打防洪坝,住当然就住在岳河子。每天天刚亮就早早上工抬筐推土了,太阳出来了吃饭,吃过饭再干,中午午睡,午睡到下午有些凉快了,再一口气干到天黑。这是劳动的过程。
从记录上看,很奇怪的,那时候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情,记录得很少,倒把重点放在眼睛看到的事物上。并且用了大部分篇幅去描述房东一家人,而且还是用的一些“怪异的”思路和词句来写,真恍若隔世。是这样写的:
我们住在岳河子的一户人口不多但很有研究意义的人家里。这一家共有三口人:59岁的男主人,他的70多岁的叔叔和他的18岁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