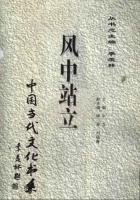法庭上,我再一次见到了俞金花和她的两个儿子,老二项君、老三项帅。据说她的大儿子项明在深圳发财了,却被母亲和两个弟弟彻底地抛弃了,被归入“穷得只剩下钱”的那类人了。我也见到了父亲、姨妈和妹妹仁小宜。我已经五年多没有看见母亲了。母亲没来,姐姐仁少宜自然也不在场。这说明母亲还活着。我还看见了我的前未婚妻宋丽芸。她和项君是证人。她比以前更丰满了,看上去更温柔了。估计那个瘦高个吴国文的厨艺早些年就可以当我的师傅。吴国文也来了,他跟汪红坐在较远的地方。他们中间的那个东张西望的孩子就是我和父亲都没认下的儿子吧,他好像叫汪东锦,随他的外婆姓。
我的身体感觉到,井裳清、姜楠这两位与我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应该就在附近。我看不见她们。我要是可以像汪红怀中的那个孩子一样东张西望,也许就可以找到她俩。我不知道,她们正在辛苦地养育着孩子。就算没有孩子,她们也没有必须来到现场的责任和义务。我只是特别想见到她们,尤其是井裳清。
俞金花满头银发,鼻翼那两条纹路,现在可以用“刀劈斧砍”去形容了。项君和项帅时不时地伸出手搀扶他们的母亲,都被老人家推开了。她直挺挺地站着,昂着头,就像女英雄面对刽子手的屠刀。经历了五年多马拉松式的上访,荡尽所有家产之后,她又举债为续。如果她不拒绝大儿子项明的钱,她可以把官司打到联合国也不会资金短缺。她为什么要对大儿子项明这样绝情呢?她一定是意识到了项智义的死与项明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她害怕历史真相会动摇她为亡夫讨回公道的决心。她大义凛然,迎难而上。吃了多少苦那不算苦,遭了多少难那不算难!杀人偿命!这是天理!今天,正是她讨回天理的日子。今天,也是了结她苦难的日子。她受苦了。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仁天木无期徒刑。”
这个声音像铁棒敲击悬空的工字钢一样,带着坚硬的金属质感和穿透力,刺得我耳鼓丝丝地发痒,在我耳廓中久久回旋,不肯遁去。
俞金花的身体瘫软了。
姨妈倒下了。
汪红在另一边呜呜地哭出了声。
我好像看见抱着俞金花身体的项君向我的方向、向姨妈站着的位置扫了一眼。宋丽芸跑回汪红那儿关照她的母亲。那个孩子大叫外婆。
法庭一时间有点儿混乱。六名法警出面维持秩序。其中两名法警把我带出法庭,送上等在偏门的一辆囚车。
一声判决,铁定如山。一切都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双方的律师都可以休假钓鱼了。
从囚车的后窗上,透过不锈钢栅栏,我看见俞金花的三儿子项帅率先冲到路面上。项帅身着武警制服,十足的彪形大汉,他瞪着一双牛眼,恨不能像大力金刚一样,抓起囚车,甩到远处的高楼墙壁上。
我的亲人们比项帅晚了好几步,他们的身影只现出了一些局部,这些局部刚够我判断出他们的身份,囚车拐弯了。
再进看守所的时候,我就开始怀念野鸡胡了,甚至在乘坐囚车离开野鸡胡的路上,这种怀念就已经发芽。洪水洗礼过的、在大山深处弯扭延展的野鸡胡川道,到处是深深浅浅的积水,许多地方的积水与清水河连在一起。它告诉人们,这川道原本就是一条宽大的河床,地里的庄稼、川道旁的房屋、圈舍、粮仓等等本来就是河床的一部分。零星的柳树披着长发,像一个一个华子良一样孤独地站在水中,一言不发。未及收割的香紫苏一株一株仰着脖子,探出三两朵花瓣。成片成片的玉米刚长出织布梭大小的棒棒和鲜亮微红的须须,正在凭借风力授粉,但多数玉米棒都沉在水中,花粉落在水面上,找不到接粉的玉米棒的须须,只好随波漂移。玉米棒没来得及领受野猪的糟践,就浸在水中,这样变质的玉米野猪是瞧不上眼的。夕阳扒开层层乌云,在大气和水中构建七色的光影,氤氲迷离,摄人心魄。
医务所靠近大路,靠近川道,就靠近清水河,也本来就是河床的一部分,它基本上完全垮塌了。本来,姜楠不在,医务所这个野鸡胡的“信息中心”“娱乐中心”就是形同虚设,现在,它连外壳也没有了。因此,野鸡胡又多了一层郁闷。我跟井裳清常常幽会的小杨树林倒没有丝毫损伤,小杨树们站在水中,依然挺拔昂扬,像一群年少不知愁滋味的孩子。
公路在川道中,是沿着一侧的山势而建的,一般要高出川道三到五米不等。山洪冲断了几处,还有两处山体滑坡埋掉了道路,并在两面山体的狭窄处拦截了川道,形成堤坝,形成了“堰塞湖”,这些都被一个中队的武警在四天之内疏通、修整完毕。这样,法院的传票才送到了野鸡胡。这样,我才乘坐囚车离开了野鸡胡。
我是被那场百年不遇的山洪冲出了野鸡胡,推到了二十一沟监狱的吧。
离开野鸡胡,押往看守所,押上法庭,再押往二十一沟监狱。这个过程中,我始终感觉身后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推我。就像当年我把项智义的后脑送上铁钩。什么力量不可抗拒呢?地震,法律,洪水。
“无期徒刑。”
与爬抓在野鸡胡死羊身上,把白色的羊变成黑色的情形类似,“无期徒刑”这四个字就像一坨一坨苍蝇一样,爬抓在我白色的大脑沟回中,改变了它们的颜色。黑色的苍蝇遇上脑浆这么好的营养,繁殖速度就像一日千里的国民经济。我的脑壳里挤满了蠕动的蛆。蛆吞食了我的脑浆,茁壮成长,它们通体洁白,晶莹透亮,它们化蛹成蝶,展开了翅膀。二十一沟监狱的第二千一百代苍蝇便有了与我这类人相近的智商、情商,它们一个个寡言少语,深思熟虑,体态矫健,动作敏捷。而我,却成了一头巨大的无头苍蝇。
来到二十一沟监狱的第一天,还在入监队,我就因为动作迟缓挨了一警棍。
警棍通常是打在胳膊肘上面的,那会造成尺骨桡骨骨裂、骨折。没有人看见警棍挥舞过来不躲闪、不伸胳膊遮挡的。
我没挡。
我看着警棍劈划开混浊的阳光,舒缓优雅地走了一个弧线。看到这样的弧线我觉得亲切,它似曾相识,经得起审美的挑剔,像个老朋友。
警棍砸在我脑壳上。
咚咚地响。
然后“嗡——嗡——”,空气紧缩,刚才被划开的空气又严丝合缝了,变成了一个大瓮的囫囵的外壳。
这大瓮有多大呢?罩得住二十一沟监狱的二十一条沟吗?
二十一沟监狱坐落在“佛足山”上。
二十一沟监狱只有六条沟,五条沟是佛足山的脚丫子缝和足内侧的大沟,这些属支线。另一条是干线沟,它贴着佛足弯扭的参差不齐的足尖,拐向远方。十月天气,大沟小沟都没水,更像是垃圾沟。那些沟就是人倒垃圾的。监狱建了几十年,垃圾倒了几十年。垃圾味儿从沟底袅袅升腾起来,汇合无处不在的焦煤烟味和煤粉颗粒,令人鼻腔发痒,双目生涩。太阳的光线在云雾中跌打,又被煤粉煤烟调戏,浑身红肿,破裂的部位还淌着黑红色的血。煤粉在阳光中反射,居然生出彩色的光斑。
“嗡——嗡——”像大瓮一样的脑壳也於满了血,憋得发胀。
“嘿嘿嘿!你傻帽呀!”
有人推了我一把。
“我一眼就认出你啦!”
我看见两扇招风大耳,一副尖嘴猴腮。
“忘啦?!我猴啊!”
像猴子。
我记得我认识二十一沟监狱的梅昊,那个知识分子。梅昊沾点儿婆婆相,年纪也快四十了,眼前的猴子不会把我当孙悟空了吧。佛足山可不是花果山,没有水帘洞。要是有瀑布般的水帘冲冲脑袋,就爽了。
稍息、立正、向前后左右转正步走、齐步走、跑步走、立定、报数、向中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
双开门,两边通铺,双层。一层十二人,两层二十四人,再乘以二等于四十八人。不出三天,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人身上的虱子就完成了它们的横向折返运动,它们南征北战,到处播种,弄得一些人彻夜难眠。彻夜难眠当然还有别种缘由,比如犯了大烟瘾呀,害了相思病啊,哼呀,嘿呀较为相似。他们都在被子下面掏啊,抓啊,鼓捣啊,看上去很像是集体手淫。臭脚丫子味儿、煤粉味儿、烂菜剩饭味儿、狐臭味儿,八味俱全。猪圈里的味道也会比这里清纯许多。“猴子”也算是大城市的人吧。他二进宫了,有经验。他对那些大呼小叫的人说:“怕什么?!狗日的,它咬你,你不会咬它——把它吃了!那也算一点肉腥嘛。改善伙食啊!”
虱子是什么味道呢?
训练间隙,群众蹲靠在墙边、扒开衣服、解开裤裆,就着晕黄的太阳捉虱子。在“猴子”的示范下,吃虱子的行动很快蔚然成风。也有不入流的,躲在人后发抖,哭泣。还有一类见政府不在就破口大骂,对相当于野鸡胡杨小帆那种角色的视而不见。掌事的也装聋作哑。“娘稀屁!虱子多得都钻屁眼儿啦!”“老子是来服刑的,不是喂虱子的!”“咱们搞一个比赛吧,看谁身上虱子多,咱们推举他做老大!四十八人的老大是什么派啊!”“这他姥姥的绝对侵犯人权!”“小姨子养的还不如看守所呐!”“这孙子从来不逮虱子,裤裆里肯定是一窝一窝的,一营一营的,一集团一集团的,肯定是冠军!”
我被群众摁在地上,四仰八叉,扯光了衣服。
哈哈哈。
比体温低得多的冷空气水一样冲刷每一片肌肤。它们在肌肤表面受到汗毛的阻碍,它们把汗毛摁下去,可是汗毛却如弹簧钢丝一样弹起来,它们摁呀,汗毛弹呀。风摆杨柳。游戏童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猴子了。我想起井裳清了。我想起野鸡胡了。我想起黑子河了。我想起未婚妻了。还有姜楠、姨妈、父亲、母亲、姐姐、妹妹。
母亲已经死了。
俞金花完成了她的终生使命。她原本当然是要求让我吃一颗黄铜闪亮的金属豆的。无期徒刑也行吧。法院说了这是“最终裁决”。无期嘛,那就是永远。罢了罢了。该回家了。回那个宝函寺村,回那个宝函寺。该去看看那个整日磕头念佛的妹子了。
宝函寺空门之中,母亲向寺庙深处的佛像磕头,姐姐立在母亲身后,庙里不时传出颂佛之音。
俞金花在空门外站了很久,似乎是适应一下这儿的空气。这里的气息已经久违了。她垂着头,深吸一口气,迈入空门。她先是在母亲的身后站着,母亲感觉到了,却没有任何反应。俞金花便挪到母亲正面,与母亲相对而跪。
母亲在宝函寺的“空门”中日日念佛已经有五年多了。也许,母亲五年如一日,就是等着这一天吧,就是等着俞金花来会面吧,就是预备着了结尘世的无边苦海吧。
她们面面相觑。
俞金花白了头发,鼻翼的八字沟纹已经堪比二十一沟监狱的沟壑了。母亲的面颊已经印上了老年斑,母亲的年龄不过五十,没有理由生出老年斑。四十七岁的女人,在香港还参加美女竞选呢。
五年多,在佛的眼中,也许还够不上“弹指一挥间”。可是,香火、烟雾粒子,已经通过七窍、通过皮肤、通过凡人无法洞悉的渠道渗透到母亲的血液中,那些色素本来是无序的、涣散的、游走的,不知哪一个瞬间,它们疲惫了,停下来歇息,沉积、凝结在母亲的脸上。所以,那些深色的色斑应该不是老年斑。母亲完全不是老年人。
母亲原本是丰乳肥臀的盈润女人,而今已是颧骨高耸,十指如柴。母亲的双膝因为天天下跪、日日磕头,已经生出了厚厚的茧子,比脚后跟的茧子还厚。在租房的炕上,母亲以膝作足,轻灵地挪移,令串门的邻居和房东叹为观止。
她们四目相对。
俞金花说:“妹子,起来吧。完啦。”
母亲看着俞金花。
俞金花说:“那好吧。我也没事了,我陪着你,天天陪着你。”
母亲咳嗽了。
俞金花伸出双手。
姐姐蹲下身去为母亲捶背。只捶了一下,姐姐听见一声喷响。
俞金花的脸上溅满了血浆。俞金花的脸在血浆的冲拍之下,回应噼噼啪啪的声响。这张脸本来有一个条件反射般地躲闪,但血浆的速度太快,它们是以颗粒为核心拖带着血浆喷射而来的,这张脸躲闪不及。以母亲虚弱的身体,从她嘴里喷出的液体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速度和力度,那有赖于时间分分秒秒的积攒和蓄势。也许母亲来到宝函寺并不是潜心向佛,而是运气、调运她身上的每一滴血液,等待此刻绝命的一喷,将她体内的血液和精气一并挥洒干净。
母亲的身体像一个空壳似的失去了支撑,翩然倒下。
姐姐后来对父亲和姨妈说:“都怨我!我要是不捶母亲的话,要是不捶的话……”姐姐把自己的小粉拳当成武林高手的铁砂掌了,仿佛可以隔山打牛,生杀予夺。
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当着群众的面哭。更不能光着身子哭。光着身子哭是婴儿的专利,盗用他人专利是违法的。
在野鸡胡被扒光了衣服丢入母猪圈的那个群众,他就是盗用婴儿的专利。他的哭喊反而助长了那几个人的兴头。当时我想,如果是我被丢进猪圈,我会认真地想一想要不要站起来。我想我会站起来的。我会立马站起来。
我站起来。
谁说的?
谁身上虱子多,谁就是老大!
我在裆下抓了一把,挥舞起来。
我喊:“看呐!这还有十八个营呐!哈哈哈!”
我追着每一个人,让他们看。他们被我追得满院子乱窜,拿着我衣服的纷纷把衣服抛向空中。把衣服抛向空中是攻陷了阵地的军人和得了博士学位的人的专利。他们不是怕见我手上抓着的虱子,眼尖的已经看出我手心里可能什么也没有,至少没有十八营那么多的虱子,他们不怕虱子,他们争着把虱子塞进上下牙之间,咬一下,发出“嗞”的一声,蓄满虱子身体的人血爆溅出来,白牙都被染红了,他们用舌头舔那白牙上的红血,舔白了,再咬一只,再舔。他们怕什么呢?
他们认为我疯了。
挖煤换班回来的老犯们黑着脸,一个个露出雪白的牙齿。
我感觉,赤裸的身体,像饱涨的馒头一样,充满了幸福。我明白华子良为什么幸福了,我明白为什么陈大勇说华子良是“幸福的麦穗”了。陈大勇说过吗?陈大勇能说出这么诗情画意的语言么?反正陈大勇活在野鸡胡很幸福。
好像是政府帮我披上的衣服。我甩膀子,甩掉了衣服。政府再次挥起警棍。威胁说:“别逼我犯错误!”群众都看出来了,政府是害怕我不伸胳膊挡警棍。哈哈。
政府还是相当的礼貌呢,够江湖。在我没离开野鸡胡的时候,《监狱法》就颁布了,打骂群众是违法的。
群众打群众违不违法呢?一群人打一个人算咋回子事儿?记不清了。好像要揪出个主犯,揪出第一个下手的和下手最重的。所谓“首恶必办,协从不问”。
大号舍与我们家的旧宅很像,双开木门,里面可以用方木棍把门别上。
我从左面的下铺开始,往下拖一个,把他的胳膊反剪到背后,令他头朝下,屁股朝上,像我出生之前他们对待我奶奶水一泓那样。
“谁说的?”
没反应。